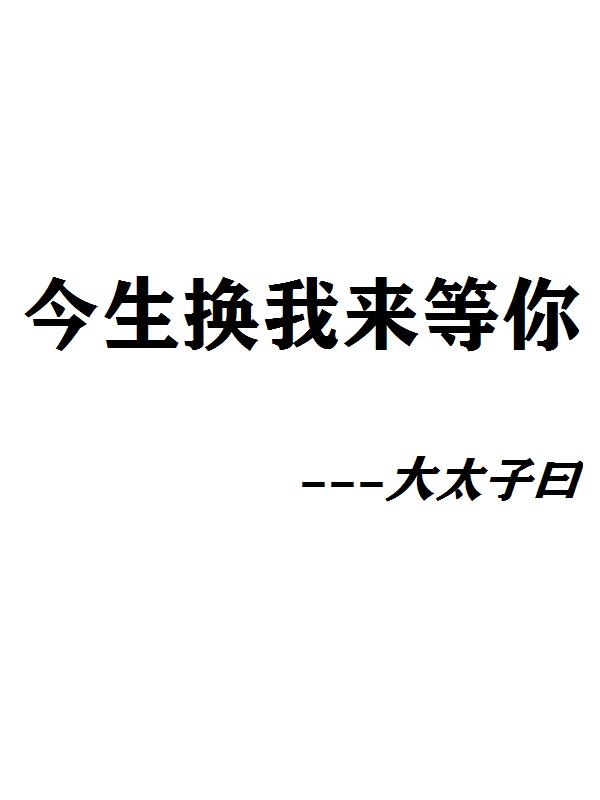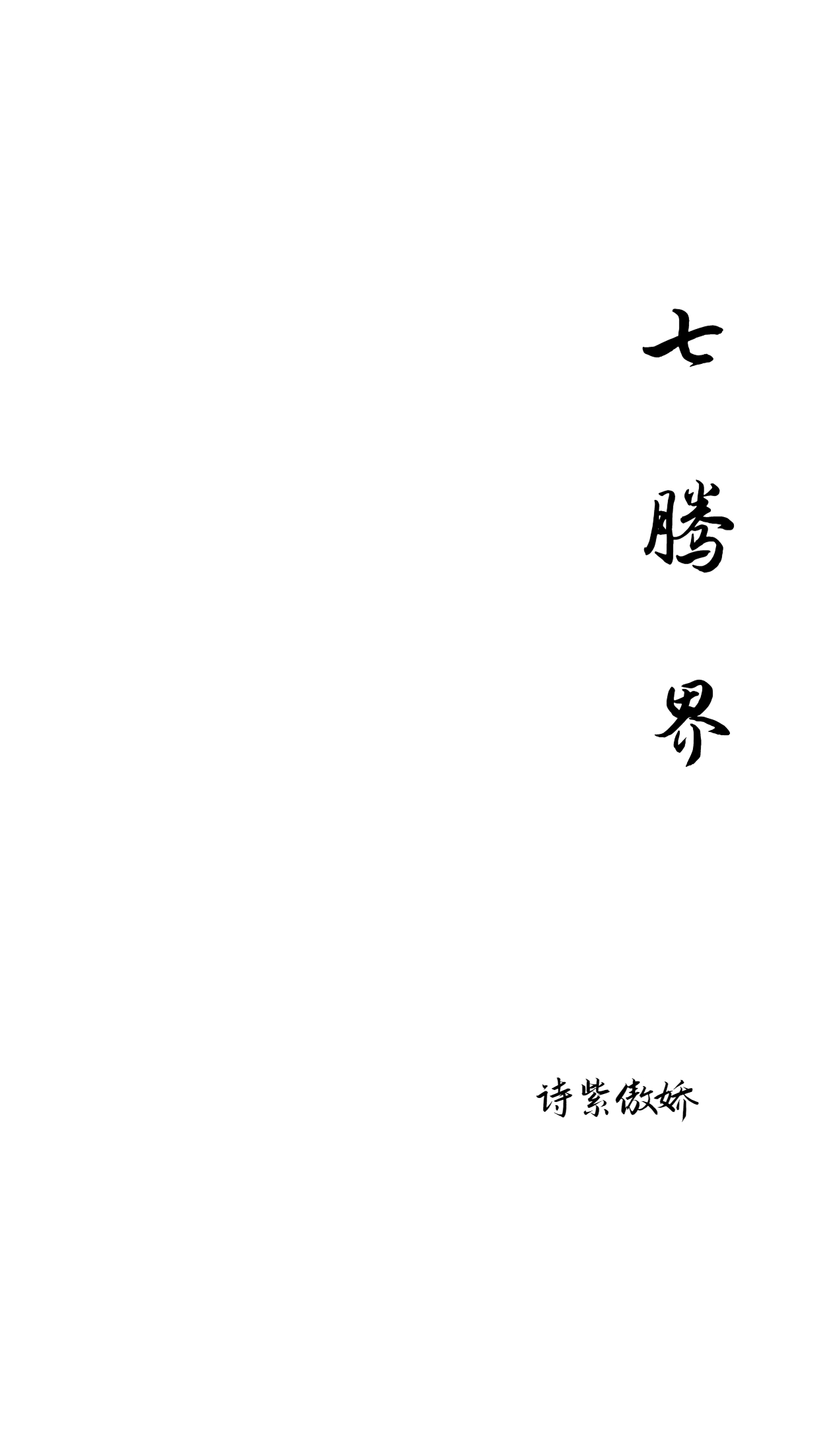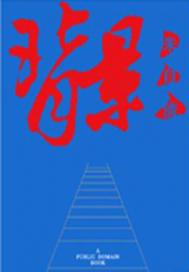在天井村住了四五天,越宁也没怎么出门,出去应酬办事说话都是戈汗一人。
戈汗却稀奇得很,因为越宁说已经想到了办法,只等那边换人,他们便可一击即中。虽说越宁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可戈汗心想,这代越坡虽是小城,却也有二百守将,越宁带的这十个人再厉害,也不可能轻易夺城吧?何况她整日在屋里坐着吃喝,也不与旁人说话,顶天了在屋里耍两剑,可这武艺虽高,难不成还能以一敌百?
这天,戈汗又见越宁在屋中琢磨剑法,实在憋不住,叫了一声公子。虽旁无人,可越宁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让他这样喊自己。
越宁停了身子,却保持着动作,侧过头看戈汗:“换人了吗?”
戈汗一怔,心说就算自己说了百阜部的人胆小,可也不会看见你们十一个人就投降吧?
为了两国停战,为了小王爷能夺回洛文部,自己不能不说了!
越宁见戈汗脸上阴晴不定,以为出了什么变故,放了手中的铜剑,上前道:“发生何事了?”
戈汗刚鼓起勇气说话,就被越宁打了岔,只能道:“倒是无事。不过……”
越宁见他欲言又止,便请他坐下,给他倒了茶,“爷爷只管说。这几日多亏有您,不然我等还无法在这天井村立足。以后还得多仰仗您呢。”
戈汗心下一顿,越宁这话说的…莫非他们真的心不止于代越坡?还要夺西凉地界不是?
越宁哪里知道戈汗的顾及,她不过是学书里的那些客套话,生搬硬套罢了。这番见戈汗脸色还不缓和,以为他还担心自己会取他性命,又道:“咱们的目的是一样的,都不希望两国交恶才有了这结盟,所以,有什么话,爷爷但说无妨,不算外人。”
戈汗留了个心眼,笑道:“我只是个小部落的老祭司,本领全无,哪里有说话的份。”这是在告诉越宁,不必指望我帮你们夺西凉,我人微言轻,毫无用处。
越宁却心里坦荡,只说:“爷爷何苦妄自菲薄。我听人说,洛文部从前可是八部之首。你放心,有我军相助,小王爷一定能重登洛文部可汗之位。”
戈汗皱起眉头,虽然之前在寨子里就是这么说的,可如今想来,怕不是引狼入室吧?就算没有这些人,他们拿回洛文部也有六成机会,这些人之举,只算锦上添花,说不定还是帮倒忙…
“唉,能不能重当可汗也不重要。只要西凉子民平安就好。”戈汗试探着越宁的口风。
越宁笑笑,“小王爷若是这么想,真是百姓之福了。我小时候读书时就常见书里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不管是好心还是歹意,争权夺位,大兴土木,苦得都是百姓。就拿这次出征来说,多少人都得为了上面的一个决定而赔上性命。”
越宁叹息一声,继续道:“不瞒爷爷说,那日攻取你们山寨,我们损失了几十余人。我是领兵之人,发号施令时不觉得,可战果摆在面前时,又后悔没有保全更多人性命的法子。”
戈汗看她一眼,见她真诚,又摸不准了,叹息一声,说:“我寨中又何尝不是…”
“我也不知说什么,到底是我们先闯寨。”越宁觉得愧疚,“可若不借道进西凉,只怕我孱国还要再败,到时死伤更多。唉,戈汗爷爷,你说,人们打仗前,要是都能坐下来谈谈,不是能免去好多战事吗?”
戈汗一怔,摇摇头,“孩子,你把问题想的太简单了。”
戈汗这“孩子”一叫出,就后悔了,这越宁虽然十七八岁的模样,可现在自己是在人家手底下当“人质”、当“俘虏”,这般称呼,岂不僭越?
索性越宁倒没有在意,他便继续道:“若不打一场,谁心里不存着个侥幸?总以为自己是吃亏的,该多占点,也有能力多占点。”
越宁撑着头,像是陷入了沉思。
戈汗忽地一想,差点把正事忘了,越宁思想如此简单,怕是真没有什么攻城大计,指望这点兵力,如何夺城啊?
这般想着,他语重心长道:“战事难免,公子还是得多想想那打胜仗的良策,既叫士兵多活,又能打胜,这才是良将的作为。”
越宁点点头,却没搭话,好似还在想事。
戈汗见她不为所动,以为是自己点的不够明白,继续道:“这代越坡,你打算如何攻啊?”
越宁一愣,心道原来戈汗爷爷是来问自己攻城计来了,想来是见自己没什么动作,怕误了事吧?
她这几日叫手下的人做事都是趁戈汗不在的时候,一来是防备他,二来也是不想叫他为难。毕竟他还是西凉人的老祭司。
越宁笑笑:“爷爷不必担心,只等着坐看好戏便可。”
戈汗也不知她是真有把握,还是背着自己作了什么,只见她油盐不进,也不再多说,左右自己又不上阵,管她罢!
且说仇徒那边,叫人打了一副拐,硬是下地走了两圈,要带阙元奎洛文部。
虞信哪里依他,说非等他伤势好全了才可。
仇徒却知道自己这伤没个百日是好不全的,根本不理虞信,叫了阙元奎就来房中坐下。
阙元奎看着仇徒苍白的脸,虽然恨他毁了自己的寨子,可也佩服他的为人,此番见他带病也要去洛文部,便说:“我都隐忍这些年,还在乎这几天?你切休息吧!”
说着,阙元奎就要走,仇徒叫他一声,他站在门前,回过头:“你这副模样,还指望做什么?”
仇徒冷冷看他一眼,“我自有办法。”
他见仇徒不死心,便又坐了回来,说:“真不是我瞧不起你,加尕布说了,你这腿没有几个月是好不了的。你真打算这样去洛文?不怕病死在路上?”
虞信听不懂他俩说啥,只见那个阙元奎似乎把自家将军惹毛了,便凶神恶煞地上前两步。
阙元奎眉头一跳,仇徒拦住虞信,“下去吧。把门带上。”
虞信见阙元奎也大伤未愈,脸色奇差,想来也做不了大动作,便说:“我就在门口。”
仇徒点点头,等他走了,又用洛文部语说:“你我都受着伤,这样去洛文部,肯定讨不到半分便宜。”
阙元奎丢了一个“这还用你说”的白眼。
仇徒只当没看见,继续说:“日前你说,当初你们洛文部分裂是你父汗不愿意争大可汗的位置,不想因为夺位而引发战乱,结果没想到他不争,底下有人叫他争,致使洛文一分为二,是也不是?”
以前仇徒一直都以为寨子里的是洛文叛党,却没想到分割洛文,占山为王是假,不忍战乱,退隐山林才是真相。想来那已经过世的洛文部可汗也是个仁义之人。可惜,他没想过,他不争,不代表别人会停止争。风雷部引领八部还不满足,短短三十年,他们的野心就打到了孱国头上。
与别国交恶,百姓苦不堪言,难道这就是善人隐忍的结果吗?
“这都是我跟你说的。又问一遍,是不信我?”阙元奎自幼聪颖,文武双全,但因为形势所迫,一直隐忍,屈于人下,如今好容易除去上头几人,却仍难摆脱这缠人的命运,如何不气?
仇徒淡漠道:“洛文现在的可汗你知道是谁吗?”
“我堂哥,钭和光。这你都不知。”阙元奎随口奚落道。他已经被仇徒拉来说过几次话了,知道他还需要自己,也不怕得罪他。
“我自然知道。你来此地时年纪尚幼,和你那堂哥应该没有过来往吧?”
“有也不记得了。你问这做什么,难道还指望他禅位给我?”阙元奎随处不忘了讥讽。
仇徒冷冷看他一眼,他倒老实了。那日仇徒的本事他也见过了,若不是被众人围住,自己只怕打不过他。想来自己也没遇见过几个对手,倒也对仇徒有几分对手间的惺惺相惜。
不过这感觉自然比不上给自己这腰间扎一刀的那个小姑娘……
可惜,听戈汗祭司的说法, 那小姑娘已经嫁给了自己面前这个男人…
“禅位给你是不可能,但直接杀了他也不行。”仇徒道。
阙元奎眉头一跳,这人把杀可汗说得如此轻描淡写,是真自信啊……
“我都没想过杀他,你倒会说。”阙元奎撇撇嘴。
“你不杀他,怎么夺位?”仇徒看着他。其实他来之前就想了许多和谈洛文部的办法,比如攻掉山寨,嫁祸其他部族,引起内乱。但这计策毕竟阴损,自从得知阙元奎身份之后,他就改变了思路,打算推他上位,快速笼络洛文部。
一旦洛文退出,那联军自然互相猜忌,不战而退了。
只是,如何才能推阙元奎上位呢?
阙元奎翻了个白眼,“你看我寨子里练兵吗?”
仇徒一怔,“何意?”
“我当你无所不知呢。你想想,如果我打算以杀夺位,我怎么不练兵啊?我那几百人,我不给他们做做兵器?”
仇徒忽地一顿,是啊,这山寨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如果阙元奎真打算夺位,怎么就领这一群虾兵蟹将?难道他根本没想争位,只是为了拖延自己而出的缓兵之计……
糟糕,如此,那祭司戈汗助娘子夺城不也是个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