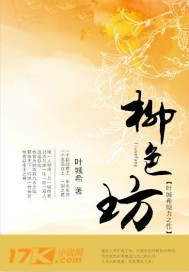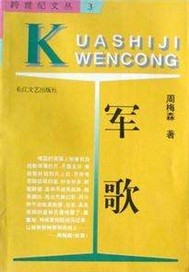仇愆皱起眉头,因为他知道这些话根本不能打动仇徒,仇徒根本不信鬼神,自然就不信什么香火供奉的功效。即或真有,他也不太可能背叛越宁。
可是站在平氏的角度来看,他觉得她娘也没有什么错,完全是为了大哥好而已,只是可能方法有点过激。既然如此,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呢?
仇愆琢磨着。
“你想到什么了?你也支持为娘,对不对?”
仇愆干笑一声,“那是当然。”忽地,他灵机一动,说:“诶不对呀娘!我可以过继一个孩子给我哥啊。”
就是这一句话——缓和了全家的关系。
从那天开始,平氏不再针对越宁,反而对她真心实意地嘘寒问暖起来,还手把手教她怎么管理内务。仇徒和平氏关系自然也好了起来。
越宁很感激仇愆为他们做的一切,她和仇徒商量着要亲自去西苑对仇愆表示表示,但府里一直忙着仇愆的婚事,一来二去的,也就耽搁到了成亲的日子。
永光二年三月初三,仇愆大婚,这一日,仇府格外的热闹,但越宁却执意要陪着小姑子人樱在婚房里坐着聊天,因为她想起自己初来的那夜,独坐空闺还不能乱动的滋味实在是愁煞人也。
人樱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心正忐忑呢,就听见越宁来找自己,忙道:“姐姐,你来啦。”她坐着虽未动弹,却也能听出她声音的激动来。
越宁上前坐下,“嗯,来陪陪你。等师弟来了我就走。”
“我正紧张呢。”人樱低下了头,只是戴着红盖头,看不到她娇羞的模样。
“没事,我刚来的时候也这样。”越宁握住她的手,她手里攥着一方红手绢,此刻被她搅得已经发皱了,足见她的紧张。
“那姐姐……”人樱欲言又止。
越宁却仿佛看透她的心思,咳了一声,压低声音说:“你是不是想问我那个。”
人樱也干咳了一声,害羞了。
“没什么,都是女儿家的,你娘和红娘肯定已经跟你叮嘱很多了。”
“可我还是怕……”人樱低语道。
“没事没事,相信我,忍一忍就好了。”越宁拍拍她的手,但似乎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她更加紧张了。
终于等仇愆来了,越宁默默退出屋去,满意地收工去找仇徒了。
第二日,是新媳妇敬早茶的时候,丹丹是外人,只让她留在客房用膳,越宁和仇徒却必须在场,所以起了个大早和仇老爷夫人一起坐在正堂里等仇愆夫妇,以免误了吉时。不过话虽如此,新婚夫妇一般敬早茶都是不守时的,毕竟新婚燕尔,头一夜往往折腾得久一些,早晨起来又少不了一番耳鬓厮磨,总是会耽搁的。
但越宁和仇徒他们刚刚坐定,就看见仇愆和杜樱婕二人在走廊里正朝这边来。越宁还在惊讶,就听见平氏感慨道:“这大家闺秀就是不一样。”
越宁暗暗清了清嗓子,坐直了身子。虽说这老夫人不刁难自己了,可到底还是有些瞧不上自己这个出身……自己必须要好好表现了呀。
“爹,娘。”仇愆和杜樱婕进来行了礼,一脸倦怠。
平氏心疼地说:“瞧瞧你们的脸色,快快敬了茶再回去补一觉吧。”说完又暗嗔儿子一眼,“你也是的,就算是头一夜,也不该这样折腾。”
仇愆和人樱脸上都露出一分尴尬,仇老爷连忙咳一声,说:“敬茶吧。”
一旁的下人连忙将茶水奉上,人樱刚刚端起一杯要递给仇老爷,就见一个下人匆匆走进来直奔老夫人,而那嬷嬷袖子里的一抹白色是如此扎眼,令她慌了神,手一抖,竟洒了些茶水。
虽然她急忙按住茶盖,但还是没能逃过平氏的眼睛。平氏是何等精明,昨夜伺候人樱的嬷嬷这时候进来已经是不正常,人樱的反应就更加坐实了这一切。就在人樱那句“爹,您喝茶”才说了个开头的时候,平氏就眯起眼睛道:“先不急。”
人樱的手抖得更厉害了,她手里的茶盖和茶杯的声响在安静的厅堂里听着令人心焦,但她却控制不了自己的手,难过地低下头咬着嘴唇。仇愆上前替她把茶交还给下人,将她扶起来——因为敬茶的时候是跪着。
仇徒和越宁这时候也意识到不对劲,彼此对视一眼,但都没能猜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为突然进来的这个嬷嬷是查白绢的,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流程,为了证明官家女子入府时是个清白之身,然后在衙门登记一番,方便以后“和离”或者其他纠纷时官府判案。但以往这种身份的嬷嬷不会入堂,何况还是在敬茶礼的时候。
仇徒和越宁都相信人樱一定是冰清玉洁的姑娘,所以更是对眼前的状况摸不着头脑。
只见那嬷嬷用身子背对众人,从袖子里取了个什么东西给老夫人看,然后老夫人的脸色就变得极为难看,立即将什么东西塞到了自己袖子里。
平氏给一旁看得分明的静初使了个眼色,静初立即会意,将下人们全都遣散出去,关上了门。屋里只剩下他们一家。
平氏冷着眉目看着仇愆和杜樱婕,一抖手将一块绢帕丢在地上,问:“你们是怎么回事!“
仇愆看看人樱,欲言又止,侧目看向一旁。
那绢帕白的晃眼,越宁不自觉地握住仇徒的手,慌张地看着人樱和仇愆。她可是听说过这女子不洁的下场,轻则被休,以后难嫁,重则——或以非人的手段处死。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人樱是不洁之女,但这块白绢如何解释?
仇徒的手被越宁捏的红白相间,但他的心思也全然在仇愆和人樱的身上,脑海里飞快地扫过几种可能,比如仇愆不举,比如人樱先天不足……但怎么都觉得勉强,索性等着仇愆夫妇的解释。
“说啊!”平氏吼道。她担心自己亲自挑选的儿媳妇是个早早与人通奸的下烂货,自己会被其他贵妇嘲笑,会令自己的儿子也抬不起头来。她在心里祈祷这一切不是真的,但她被地上的白绢刺激的心脏隐隐作痛,那痛感何其真实。
“都是人樱的错。”人樱突然跪下,眼泪已是扑簌簌地往下落。
“你果真不洁?”平氏捂住胸口。仇老爷立即拉住她,唯恐她受刺激昏厥过去。
“娘,不是的。”仇愆急忙陪人樱跪下,替她说话。但他的神情之间也充斥着懊恼,叫人难以忽视,似乎他含着什么委屈。
平氏抓紧胸前的衣服,“那是怎么样?我的傻儿子,你还要替她隐瞒吗?”
仇愆无奈又痛心地说:“我没什么好隐瞒的,娘,这事……唉,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总之人樱肯定是清白之身。”
“难道你有什么隐疾?”平氏更忧心地看向自己的儿子。
“怎么可能……”仇愆下意识反唇道,但急忙说:“哎呀,娘,您能不能不问了,这早茶还敬不敬,不敬我就和人樱先回房了。”说着他就要拉人樱起来,只是人樱不肯。
平氏一愣,“什么?那这算怎么回事?你们两个到底是谁的问题?我还能抱孙子吗?”
平氏的视线不小心扫过越宁,越宁立即紧张起来。不过,平氏此刻真的没有在针对她,只是空洞地在心里问自己,是否上辈子做了什么孽。
仇愆叹息一声,看着人樱,人樱痛哭起来,说:“都是我的错。“
“哎呀,我都说了不怪你,起来,咱们回房。”仇愆急忙要拉她,她却泣不成声,怎么也不起身。
“究竟是怎么回事?”平氏着急地直跺脚。
“爹,你能不能先把我娘带走,还有大哥师姐,你们也先走吧,行吗?别问了。本来就没什么大事,为什么非要刨根问底呢。”仇愆面露愠色。
越宁看看仇徒,仇徒冲她点点头,起了身子,“那爹,娘,我们先回去了。”
“淑娴,走吧。”仇老爷劝着平氏。
平氏却不肯走,说:“你们现在不说清楚,外人指指点点的时候,我怎么说?我说什么?啊?子恕,你让娘怎么和别人解释?这东西怎么解释?”平氏抄起白绢在仇愆眼前晃着。
仇愆一把夺过白绢,低吼道:“那我能怎么办?”
人樱身子一颤,似乎被仇愆吓到了。仇愆意识到了这一点,连忙安慰人樱说,“对不起,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只是……”他叹了口气,因为昨夜已经说了很多安慰的话了,他自己也发觉那没什么用处,不过是骗她也骗自己。毕竟他也想不到什么原因,会令她的妻子恐惧被人触碰,更想不到任何的解决之法。
平氏着急地看着他们,“你们谁能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哟喂,说句话能有多难。”
“淑娴你别急。”仇老爷紧张着平氏的身子。
“娘,这事儿让我们自己解决行吗?您先走吧!”仇愆看着仇赁,仇赁半推半拽地将平氏拉了出去,说:“他们总会给你一个交代的,下人都在,总不好叫别人看笑话吧。快走。”
待屋子里只剩他二人,仇愆说:“人樱,你已经嫁给我了,我是你的夫君,有事情咱们一起面对。如果只是因为你害怕我,我会慢慢让你认识我,接纳我;如果是因为有什么病,我陪你找大夫,治好它,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