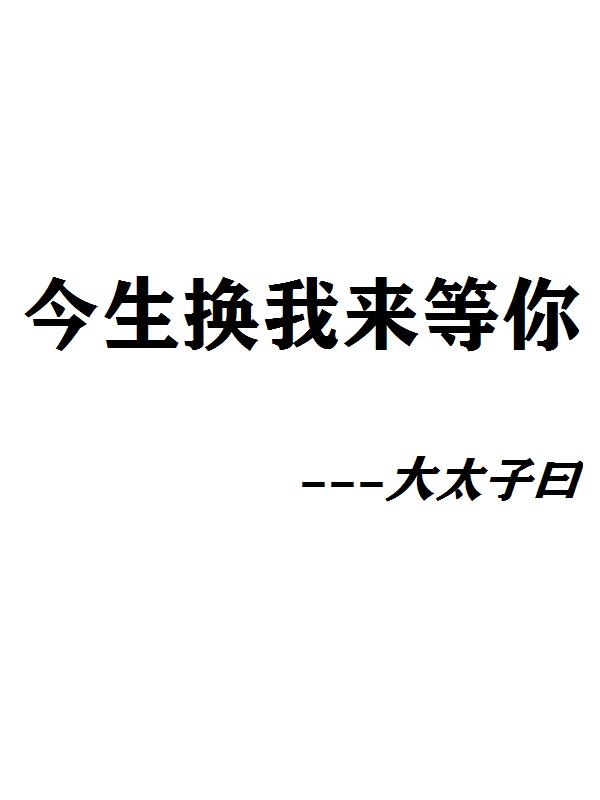这条裂隙大概有二十尺长,小六在夹缝中走了几步,骂道:“这里头好臭啊,还有老鼠。”
几人却都没有心思回他。
他兀自走着,忽然绊了一下,好在这里移动艰难,他也只是稍稍晃了晃身子。
“有东西。”小六冲上面说道。
几人相视一眼,急忙冲下面说:“是什么。”
小六皱眉道:“在我脚旁边,我蹲不下去啊。”
“是石头吗?你踩上去啊。”几人失望地骂道。
小六想了想,就要抬腿,试着踩了踩,忙收回脚,惊道:“妈呀,是软的。”
越宁立即冲到小六上面,“小六!仔细看看。”
越宁这一喊,众人都回过神来,小六眉头一跳,松开上面的手,尝试着侧腰伸手去摸,这一探不要紧,竟让他沿着这软东西,摸到一根细棍。他捡来凑近眼睛一看,这不是箭身是什么?
他心口一紧,大呼道:“好像真是将军,我发现箭骸了!”
说着,也不等上面催促,他自己就强行撑着墙壁往那软物上去看,这一看,竟然真是个人的形状,不过侧躺在缝隙深处,他一碰,竟还有几只老鼠四散,他不由心头一凉。
“怎么样了小六!”越宁急切地问。
小六不敢回话,自己晃晃尸体,绝望地唤道:“将军?将军。”
却无人应他。
“下来个人,帮我把将军弄上去!”小六声音中恨而急。
“我去。”越宁红着一双眼睛冲上前。
众人见状不敢阻拦,便要缒她下去。
小六叮嘱了尸体的位置,叫越宁从头的前面一尺的位置下来,这才擦着墙壁退回脚的位置站住身子。只是身体这会儿却因为悲愤在不住的颤抖。
几人无声的把越宁放下去,越宁一落地,也不管身上的伤口,也不知疼痛,硬生生在细缝中侧腰折下,以看清尸体的相貌。
但这里太黑了,她什么也看不清。她伸出手指触及那人的脸庞,心中已然知道,这就是她日思夜想的人。
“相公。”她颤着声音,不敢想象仇徒在这狭窄的缝隙中躺了多少个日夜,在绝望中闭上双眼……
“我来晚了。”越宁抑制不住自己激动地情绪,哭出声来。若非自己来寻,相公这天大的委屈,又有谁知?
上面几人虽然看不真切,却也泪目。这裂隙他们见识了,小六好好地身子,下去也如此艰难,将军还是带伤的,在这底下一个月……不知几多绝望。
越宁和小六费了一番功夫将尸体扶了起来,旋即二人一人举起尸体一臂,由宇文德三人将仇徒拉了出去。
再急忙将越宁和小六拉了出来。
越宁一上去,便冲到尸首前,看见仇徒紫青的、瘦的吓人的面容,沾满污血和泥的衣衫,僵硬紫黑的身体,她竟然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张口凝噎。
西凉人说,他走了,可她不信。因为仇徒亲口承诺过她会回来。亲卫们说,他走了,她也不信,因为她没见到尸体。现在见到了,尸体说,他走了,她还是不信,因为她心里眼里全是仇徒的模样,不敢相信那人已经走了。
“相公…”越宁声音沙哑,不知如何发出的声音。
亲卫们不忍地移开视线,背身拭泪。
越宁抬起衣袖,想替仇徒擦去脸上的血迹,却擦不干净,牵起他的一只手,想要暖热它,却始终冰凉凉的,不由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哭道:“都怪我,我早几日来,你是不是还会等我。”
“都怪我们,我当时就应该直接冲出关来找的!”小六一拍大腿,蹲在地上抱头懊悔。
其余几人也恨得想把自己杀了泄愤。
越宁抓着仇徒的手,紧紧地贴在脸上,身子颤个不停,说:“我竟然没有陪着你……”
亲卫们闻言,劝她,说:“夫人,这不怪你,都是我们。没保护好将……”
“夫人!你们快看!”小六忽然指向仇徒的手臂大叫。
只见那里衣袖破裂,露出紫青的手臂和一道伤痕,现下伤痕正缓缓滚着红色的血液。
越宁一惊,忙探向仇徒的鼻息,因为死人是不会流血的。
这一探,指尖上竟然晕开淡淡的温热。越宁瞳孔一缩,喜极而泣,拉起仇徒的手:“相公,相公……”
几人亦是泪中带笑,感谢上苍怜悯。
宇文德道:“夫人,这里不是久留之地,还是先把将军带到安全之地再说。”
越宁回过神来,点点头,和几人搭把手,将仇徒放在了康永的背上,在不远处寻得一处稍显隐蔽的大坑,几人这才将仇徒放了下来。
越宁看看四周,叫小六去收集那些还未化尽的雪水,用滤水囊滤过再拿来。
宇文德和康永主动提出去远处孱国的村庄借些炊具来煎药,越宁说若是有郎中,则想办法带过来,若是不愿,就用强的。
几人一怔,点点头。这战争年间,许多人都是自扫门前雪的心思。
待他们走后,越宁叫简原把阙元奎送的大氅拿来铺在地上,然后两人将仇徒担在暖和的大氅上,这才开始审视仇徒的伤势。
越宁没有学过医,但在山上曾经自己料理过简单的外伤,便张罗着简原和自己一起将仇徒的衣服裁开,因为那些衣物有的和仇徒的伤口已经粘在一起,若是强脱,可能会连皮肉都撕扯下来。
仇徒也不知道遭了多大的罪,越宁他们如此折腾,他竟一点反应也没有,若不是知道他还有气息,只怕真以为他是具尸体了。
二人将仇徒衣服褪去后,被仇徒触目惊心的伤势惊红了眼眶。
越宁颤抖着手,想要抚摸仇徒,却因他身上无一处完好之地,不敢也不忍心碰他。
“将军。”简原哽咽着。
小六拿来雪水,越宁倒了一点在手上,冷得叫她直想打哆嗦。简原立即将滤水囊拿了过来,揣进怀中。
越宁皱起眉头,“这样也不是办法。”
“可惜这里离村子太远了。”小六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看着仇徒。
越宁将自己的棉衣脱下,盖在仇徒身上,抬起头道:“小六,你去找宇文他们,想办法弄匹马回来,实在不行……”越宁顿了顿,像是在做什么重大的决断一般,凝神片刻,说:“就去龙首关偷。决不可叫人知道我们还活着。”
小六神色一变,郑重地点点头,猫着腰溜走了。
简原看看仇徒,又抬起眸子来看越宁,只见她呆呆地盯着将军,心里不由叹了口气。若是没有这场战事,将军他们本该一家三口……
“长安,你后悔吗?”简原不禁问道。
越宁眸子一怔,恍惚地看向简原,这话仿佛是他问的,又好像是自己脑中出来的。后悔吗?自己几时想过这个问题?对了,是在代越坡时就时常跃入脑海的问题。不过那时自己没受什么苦,反而还被人照顾的很好,只是心中偶觉孤独,会与昔日山中时光拿来比较,觉得那时更快乐罢了。
但若真叫自己回山上去,自己似乎又不再舍得山下的繁华与熙攘。
后悔吗?
逃出代越坡的那个雪天,她也问了自己。只是那时孩子还在,也不知道相公的安危究竟如何,总抱着些许希望,所以,也没有细想这个问题,只愿快快见他,然后把一切烦恼都诉说与他听。
后悔吗?
一个人躺在床上,腹中空空如也的时候,她又被这个问题席卷了脑海。但她太累了,身心俱损,不愿去想,怕自己会被这可怕的问题击垮。因为如果她后悔了,她就会恨,像书里那些人一样,不快乐。
她不愿恨,因为她很有可能会恨阿爹,若非他,自己不会嫁给相公,也不会出征,不会小产。也有可能会恨娘亲,若非她,自己可能已经嫁给何宸哥,在铁匠铺里终日嬉戏,还有泉君,他不会想着参军,而是每天山上山下的跑来跑去,笑着说:“阿姐,你看我天天来找你,是时候叫你相公给我打把佩剑了吧。”
这些都是她的亲人,她不能恨啊。他们也是为自己好,谁会想到后来的事呢?要恨,也该恨自己啊,好端端地,为什么要跟着出征呢?在仇府虽然不适应,可总会习惯,起码,那里安全。
唉,也不是。那杀自己的口谕无论是否是皇上所出,敢假冒圣旨的人,怎么都会是权倾朝野的存在。自己无论在哪里,总是逃不开这一劫吧。这就是做他的女人的代价吗?
那该恨他吗?
“后悔…”越宁不是回答,而是自己呢喃起这个词,仿佛不知它的含义。旋即,她笑了笑,看向仇徒,说:“相公,你说,我后悔吗。”
夜来得快,康永他们没有回来。简原将滤水囊从怀中取了出来,说:“尽力了。”
越宁接过温凉的滤水囊,虽说简原暖了一下午,可效果并不明显,但她还是说:“辛苦你了。”
简原摸摸脖子,取下自己的滤水囊,站起道:“那……我再去弄点水。”
越宁点点头,见他故意走远,也知道他是不晓得如何面对这样沉默的自己,便将目光又放到了仇徒身上。
这几个时辰他都没有动过一下。
“相公。”越宁叫了一声,声音不自觉地哽咽起来。她抬起手触及仇徒的面容,消瘦见骨,血痕和沙土将他细腻的皮肤变得粗糙,当手指拂过干裂的嘴唇时,越宁只觉得指腹好似划在砾石上。
“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