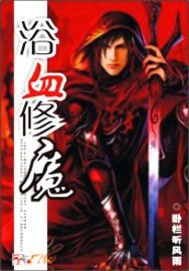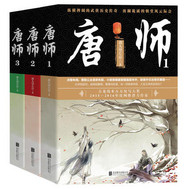如果从极高处鸟瞰,泛着黄水的龙心湖就像一个染了恶疾,却仍然竭力搏动的巨大心脏。它傲然落于两州之间,自那场地震之后,传闻底下有水怪作乱,不复当年繁华。四岸无村镇,水中不杨帆,川颖难相通。惟它浊涛千里阔,浪起时才见一泓清澈。
在龙心湖东南角的无名小河就像一脉细微血管,安静地流向那深不见底的大地伤口。在断崖边上,这道水流爆发出惊天声势,义无反顾地透地穿天,激起万斛银珠乍腾骤落,碎而不绝。这挂壁白水便有了名字:饮天瀑布。盯这瀑布久了,就会从心底生出一种焦躁,仿佛龙心湖的水不多时就会被铭罪深渊吞没得干干净净。
每到清晨,深渊上空就会升起团团迷雾,让人看不清底细,惟知前方无路,如同走到世界尽头。以双掌拢嘴,朝迷雾下方用尽全身力气大喊一声,在心里默数十来下,才听得到一声极其微弱的回响。仿佛在迷雾那头藏着另一个自己。
待雾散去,天堑显露真容,左右无际,彼岸隐隐,日照失威。心性弱者绝不敢站在崖边往下看,因那无底的黑暗似有坠魂之力。
铭罪深渊有多深,世人说不清楚。有一种说法是把世间最高的山峰拔出来倒插进去也不见得能冒出头。
此万丈沟壑常年处于湿热之中,多生蛇虫怪毒。偶有绝世强者下去探查,难见活物。光沉不下去,风涌不进来。伸手不见五指,抬脚不知方向,若踩着软塌塌的东西,也不知是动物尸体还是一坨烂泥。你的眼睛失去了作用,只敢摸着湿漉漉的岩壁前行,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毒蝎的尾钩刺穿手掌,或者被狼蛛的毒螯钳断指节。
在这里,黑暗和沉寂是永恒的旋律。如果看到两点幽光忽隐忽现,那说明瞳孔的主人在打量它的猎物;如果感到背后有一阵劲风,那是硕大的怪物在扑向你。
摸索着行走,经历长久的闷窒后,你在一幅柔和的光幕中见到了梦寐以求之人。可能是你日思夜想的亲人,对你露出最温柔和煦的笑容,向你招手。或者是一位身姿婀娜的妙龄女郎,用她卓越的歌喉给你最深情的抚慰。你忘了多久没有见人面,多久没听人声,你的思念化为哈喇子,流到衣襟上。你展开双臂拥抱那片光幕。
你忘了深渊中的一切光明乃是虚妄。那光幕化为一团鬼火,无情地将你炙烤。你的惨叫声渐弱,几只鬼影从黑暗中浮显,将你的灵魂分食。你徒留一具苍白的尸体,口目皆张。污土秽泥裹作你的冥衣,虫蚁钻入你的七窍,过往的野兽嗅到你的内脏被蛆虫啃噬一空,忍住饥饿将你遗弃。
也许你用最虔诚的祈祷和持之以恒的谨慎躲过了所有的劫难,仍免不过前进时一脚踩空,滑入某个小小的洞穴。洞壁滑似鱼肠,你无物可依,攀而不上。所有的冰冷和孤凉涌上心头,你颓然坐倒,开始与自己说话。不多时,耗尽精力的你闭上了眼睛,世上又多了一只饥饿寻食的冤鬼。
当然,你可能受上天眷顾,所有的灾劫与你绝缘。但你只是个普通人,适应不了深渊之下的环境和气候,也找不到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最多五日,你的体表就会被侵蚀得开始溃烂,痛痒和饥饿的感觉袭上心来。你伸手去挠发痒的地方,抓下一块脆弱的皮肉。你握着自己的皮肉不知所措,无处不在的饥饿感驱使你吃掉了它。于是你疯了,身体还没走到尽头,但精神的崩溃加速了你的灭亡。
如此艰苦险绝的深渊之底,任谁也想不到,竟独自生活着一个怪人。
这怪人蓬发垂肩,浑身包裹于一层干泥形成的盔甲之中,颈上挂一串铜钱,腰间用藤条别着一只葫芦。
怪人寻到一汪水潭,沿着石壁向上攀援数里,在一处石缝中静坐。这一边的陆地断脉是挨近英州的那一面,越往上越垂直,甚至倒弯。想徒手攀越这万丈峭壁,见到地面上的太阳,难于登天。
在这处石缝,以怪人的目力刚好能清楚地观察到那条灰蒙蒙的裂天长弧,再向上攀爬,屋檐般的岩层反而会遮挡所有视线。
仰头看对面极高之处,是一条白练般的瀑布。近它闻洪声震耳,远它看静水留痕。瀑布被嶙峋怪石割裂,越往下越扩散,越扩散就越稀松,黄白色的水花被摊薄成透明的颜色。经过数十里的跋涉,瀑流失去所有威势,变成一股山泉紧紧地贴伏岩壁,乖巧地流入深渊底下的水潭里。
怪人重新确认了一遍师父算出来的时日和方位,自语道:“就在这里等吧。”
五年前深渊之底发生了一场令鬼神失色的大战,一群高鼻梁蓝眼睛的白种人杀死了那头前所未见的巨大神物。怪人的师父从藏身之地现身,夺取了神物尸体上的一件东西,从此不知所踪。临行前师父交给怪人两个任务,一是守着那具庞大的尸体等他回来,二是在五年之后迎接“飞渡一线天”的贵人。
作为奖赏,师父把自己的一葫芦烧刀酒给了怪人。这一葫芦酒的承诺,让怪人在深渊之底呆了五年。
“贵人”是谁呢?怪人并不清楚。只知道师父为了寻找破千古未有之变局的贵人,来到了帝国南部,自己只是他顺道捡回来的孤儿。
从小跟着师父长大的怪人,离开师父的这五年过得如何艰辛,只有他自己知道。在深渊才生活了半个月,他的衣裳就全烂了,只好给自己抹了一身泥巴,用火烤干当作衣服。
深渊有数里宽,他时常摸着黑在两侧峭壁间来回走动,看天边的那道长弧由宽变窄,再由窄变宽。幻想自己是一只陷在岩缝里的蚂蚁,以此来打发无聊的时光。
横亘在深渊底部的神物尸体有四五里长,他一开始是不敢靠近的。从来没想过,何等生灵才会有这般体型,听师父说,只有远古神兽才会长这么大。但即使这神兽活着,直起来也还是够不上地表吧。
久而久之,这钢铁山脉般的神兽尸体成了怪人最好的陪伴。除了填饱肚子,计算时日,怪人终日躺在它冰凉的背上。它的躯体有些像放大无数倍的蜈蚣,每一寸表皮都坚硬之极,似百炼寒铁浇铸。数不清它有多少对螯足,每条足都像是一根倒下来的参天巨木。足上布满了细细的绒毛,那绒毛对于常人来说,却是致命的硬刺。
如果神兽没有倒下,从它的下方穿过去,就能看到其腹部有一道巨大的伤口,是一名使剑的白种人豁开的。那一剑让它蓝色的血液流成了河,血河淌过的地方,再也没有踏进过一只生物,所以跟这具尸体呆在一起是最安全的。
怪人不明白的是,这神兽明明有撕天裂地的力量,为什么不直接杀死那些白种人。只防守不反抗,最终落得身死道消的下场。它的头颅始终顶着那一处石壁,以致于怪人从来没见过它的面容。不过怪人对它是由衷地敬佩,最饿的时候也没想过吃它的肉。
后来,怪人过于寂寥,也是动了恻隐之心,决定给它挖一座葬身的大墓。徒手掘地,一天前进一步,一挖就是五年。每过一个月,怪人就喝一小口葫芦里的烧刀酒。到了最后的日子,墓挖好了,怪人一口喝完了剩下的酒,辛辣入喉,泪水一下子涌出来了。那是他在深渊里第一次哭泣,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悲伤,却不知自己的双手炼到了何种地步。
这五年里,怪人长出了胡子,年轻的脸庞刻满了沧桑。“师父,你可别骗我啊。”他静静地坐在石缝里等候。
天上毫无征兆地下起了暴雨,也许应该伴着雷声,但天雷也惧这深渊的威势,惶恐而不敢下。就算把整个龙心湖倾倒下来,这深渊也能一口喝下吧,怪人心想。
不时有弱小的石块被雨水冲刷滚落,或者卡在更大的石块之间,或者砸进深渊底下的土壤里。这两屏千里绝壁经过多年的雨雪洗礼,变得愈来愈坚不可摧,也许只有时间才能将其磨灭。
任雨势如洪,怪人自岿然不动,紧盯着天弧与那道瀑布的交接处。两颗黑点忽地闪将出来,其中一颗下落了一段距离就停止了,像被什么东西绊住。另外一颗稍大的黑点一直下落,偶尔磕碰在岩块上。
怪人踏出石缝,算好那颗黑点落下的位置和高度,掌指翻腾,飞快地结着手印。第八个手印成型,咒语随即脱口而出:“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语毕,怪人冲天而起,向那颗黑点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