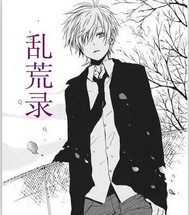他前一秒拧住我的脸腮,我猛出一拳,击在他的脸上, 用尽全力,也许骄傲的那绵堂平生第一次被人从正面突袭得对手,猝不及防打个趔趄,反应过来,闪过第二拳。下一秒我拿起鬼哥菜汤毫不客气的扣压在他的脑袋上,他一把抓住我的对手:“小子,别来两次,不好玩。”
我挑衅和害怕望着他,旁边是惊魂未定的阿香和田、和一脸惊喜的王八蛋们。我对上海的黑缺乏最起码的了解,他身后的黑衣侠立即像潮水涌来,斧子闪闪,发出让你牙酸的金属磨刀声;也根本看不出眼前他的手下把手放在怀里,是单等一声令下掏出把我射成蜂窝或打成残废。我只是大感痛快,觉得自己的自己复仇的天使,只差一柄天义之剑,便以指作剑,向前一指:“那绵堂,告诉你,我也不是好惹的。”
我隐隐感觉到,自己选择的时间、地点有点不恰当,我的心情突然变得紧张复杂,我知道,那绵堂也许只需要伸个手指头,就可能把我给废掉,可那样一样,我跟他的梁子就结大了,就相当于跟整个孤儿院敌对。但拳已经出手,骑虎难下只能再接再厉:“我这个人命贱,所以老想和富贵人换命,换了命我也不吃亏,你没听人说吗,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那绵堂挑眉不语,帅气十足的用手整理头发,整了整衣领,揉着双掌,双掌骨头咯咯响,他向后摆摆手制止住他们,身后的黑面侠向后退了退,大有自己出手的意味,英俊的脸上渐渐布满杀机......
只可惜,我刚才那番正词严义没有完全达到效果,以我对生的本能感觉到是小蚂蚁宣战了一群狼,卵蛋了!
我趁着他没有回神过来的0.1秒,我以兔子的速度冲破阿香的身边,一口气狂奔楼上,我知道那是空旷危险的楼顶,同时也是我的避难所。果然不出所料,0.3秒后,旋风般跟着我追上楼。
边追边用手势阻止黑衣徒对我围攻。
我毕竟只有16岁,打龟凤七可以,打那绵堂我不是找死吗,冲动的人呀,我正在找死当中。
我还没有来得及跑到楼顶围栏,他就在楼顶楼梯围追堵截我,抓住我犯罪的左手,拿脊背推着我往墙壁上猛撞了一下。我一口气岔在那儿,整根脊背好像生生成了几断,于是我被他一个过肩给摔在地上,一点机会都没有。
我天旋地转地看着我顶上的那少锦,
我的后脚被他粗鲁一脚勾倒在地上,我天旋地转地看着我顶上的那锦堂,我的全身重重摔倒在坚硬石头上,他骑在我身上,拳头狂风暴风般的落的我的身上,狂怒:“臭小子!”一股血从我嘴里流了出来,咸咸的,膻膻的,这个味道我太了解了。
他抬起脚,我猜想他打算把我整只手蹊断。
他那只脚一直没有踩下去,最后轻轻踢一下。
我依然没有言语,双手做向前匍匐爬行的姿态。他从狂怒的状态中冷靜下来,打到他手累了停下来,他喘着气。从我从小逃生的本能和总结来看,我机会来了,我狠狠咬他的手,用尽全力,用活命的力气。
“啊!!!”,他果然痛苦的从我身上一跃而起,被尾随而来的山鬼哥像高速炮弹发射击过来,不计成本撞击他。
不过,这种以蛋撞石的作法叫破斧沉舟,他身体素质明显比山鬼哥要强悍,用一分钟时间就摆脱和控制住他,闪电战拳脚让鬼哥找不到东南西北;随后果断让同样尾随而来打手们七八人身躯压制住山鬼哥,最愣鼠一发急掐住阿虎脖子,被那绵堂捎来一个耳光:“控制住他,不是要杀他!”,困兽犹斗的鬼哥急得向我哭腔哭调地号叫:“快跑!”。
我全身都很疼,巨疼。
但我只有一瞬的机会,要不然,我们俩可能会受屈辱,因为鬼哥的命比我们这帮穷破烂命要值钱,他们不敢把他如何。
于是,在鬼哥给我争取的时间内,我擦了擦鼻血,用尽所有的力量开始狂奔,左转,玩命地冲向高碉堡前。
这一切都让人觉得陡然回到上古洪荒时代,人们还在用石头和树棍与怪兽打拼的时代。
我,猫九九,来路不明,命运这狗东西总跟我鬼脸。
我脚停在眼前的悬崖峭壁前,后退几步,需要头向后仰才能看得见附在崖顶旁的的塔楼——我的逃生之路。
此炮楼是洋人为躲避追杀而修建,高十五米,最上面是一个小平台。早前传说有人偷溜上去从楼下一跃而死,不详之地,所以,房门早被嬷嬷用大锁锁住,目前不能走楼梯,要到达上面只能依靠从上而下玄吊的垂直浮梯,但是浮楼仅剩为数不多十格,早此年间,一场大火差点把浮梯烧个精光,所以,想要借浮梯上塔楼,首先要利用岩石悬上藤萝往上而攀登才能抓住浮梯,地面和浮梯之间想差数十米之高。
那绵堂那货紧逼跟随而至。
“跑呀,跑呀,有种了!”
“跑起来像娘们,老子要你知道男人是如何做。”
我悲愤交加的骂回去:“你妈巴羔子!你全家属乌鸦!”,一边忙着用地上的石头砸向他。
他好像是非常快活这种捉人乐趣,像猫抓老鼠样一步步的靠近,我忽然发现我的后方无路可跑,除了由下而上的高碉堡。这他妈的断头路。
“我猫九要活!要活!要活”。我大喊三声。
我深深地吸一口气,心里感到害怕,内心努力克制着内心的恐惧感。我紧紧抓住藤蔓,脚下踩着一点岩石坎,身子紧贴着峭壁,脚下踩着另一石坎,慢慢往上移动,真蠢呀,跟那绵堂一战也比这个笨方法好些,但是内心的好胜之心,容不得我往下撤。
最大的绝境不是前方不详之地,而是身后,那绵堂像狗皮膏药一样跟上,尤其腰间别着明晃晃小刀,我像待宰羊羔。
“你会摔得头破血流!”从脚下传来一个急吼,声音来自那绵堂。
“老子要叫不死猫!”我顶他一句。
对待他要敌对势力,强对强,气势不能低下,硬抗,满嘴脏话一溜出:“狗日龟儿子**,老子日你仙人板板!烧饼油条包子麻花,我看你就像一个纯种上海哈瓜儿!你靠山山倒,靠河河干,看鸡鸡死,看狗狗翻,你滚你妈三十三!”
他发狠眼神中,不忘扮演“大哥大”本色:“你有种,三天内已咬了我两次,有没有传染病,做我那兄弟,哥包你有吃有喝,叫声-”
然后,我们两只爬山虎一高一低向上蠕动。
人群聚集越来越多。
那绵堂嘴里说不上话,因为嘴里叼着刀,他只能依靠他手挥舞,大有警告别多嘴的意思。
那绵堂已到达在我脚下,阴沉沉望着我,我猜想,他是否后悔愚蠢的跟上来?是否怕了?他颤抖的轻声:“下来,你敢下来,我不打你,你这个胆小鬼!”
脚下面的世界人逼着我再一格一格往前攀爬,骨子里的逆麟也逼着我一格一格往前攀爬,我望着脚下的他们,幼稚咯咯大笑。
此时情景,我就是那个少年不识愁滋味,强说赋词偏说愁大笨蛋,其实我怕得要死,脚控制不住打抖,我想要晕厥,我想下一秒我会死,手发冷。我没有力气往上爬,也没有力气往下爬。我知道我将要掉下来了,像纸片一样飘落下去,然后会被他们像扫垃圾一样归类到垃圾桶里,最终变成树的营养或是狗粮。
万万没想到,攀登太需要体力我继续上移,一会左一会右,踩在岩石上,一会儿就感到脚酸手软,攀登过了好大一会我才平静下来,我继续往上爬。
头上面的世界是静止的,脚下面的世界是喧哗的。
“猫九九你跳呀!”
“哭啦,哭啦。”
“哈哈”,
“那哥,抓住她的脚,往下拉。”牛八为首的王八蛋们正幸灾乐祸地在下面评剧,小马六甚至于笑得岔了气,他们惊喜得很,终于有人为他们出头收拾我。
鬼哥被用绳索套起,动弹不得,嘶哑吼叫着:“那绵堂,你敢动猫九一根毛,我一命抵一命!”
我像梦游一般机械向上攀登,闪烁着无畏的情绪,大不一死,嘴里喃喃自言:“娘亲.....”我呆滞地低下头,望着近在咫尺追逐者,我以为我再也不会在任何人面前露怯和哭泣,彼时,年仅16的少年,只能用原始本能干嚎表达自己玻璃心:“来呀——”
声波阵阵荡漾。
我感到有股危险力量,吸引我放开双手,从山而降下,摆脱脚下的石头,摆脱饥饿,摆脱受控制的人生。在我心跳加快的漫长时刻里,我想象着自己已放开一切,随波飘流。
我打了个寒颤,铆足了劲,慢慢地,我专心而坚定地向前爬,一手一手地移动。
我右脚踩着岩缝里长出来的树根,还不到我的脚的宽,左脚悬在空中,但两只手紧紧地抓着藤蔓。当我身上慢慢往上移动时,身子的重量承受不了树根,猛的往下滑下几米,要不是手里拼死紧拽着藤蔓,我就明正言顺归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