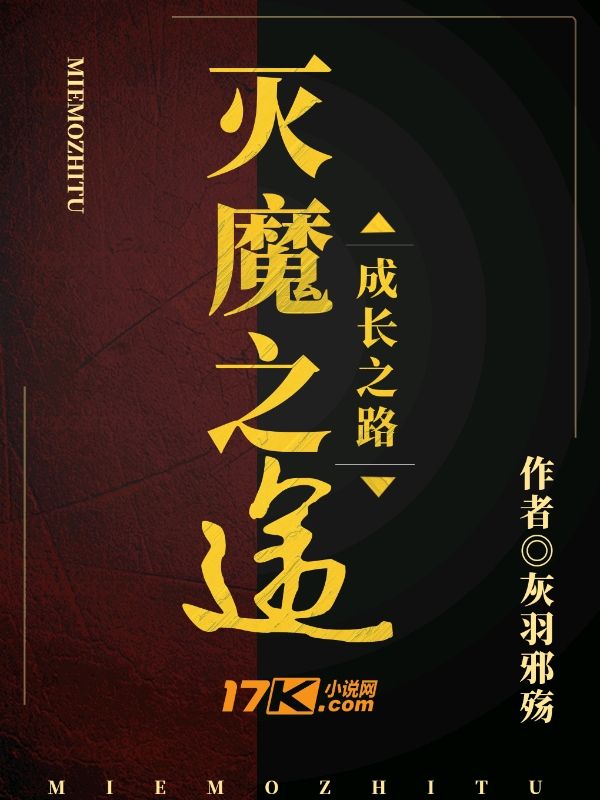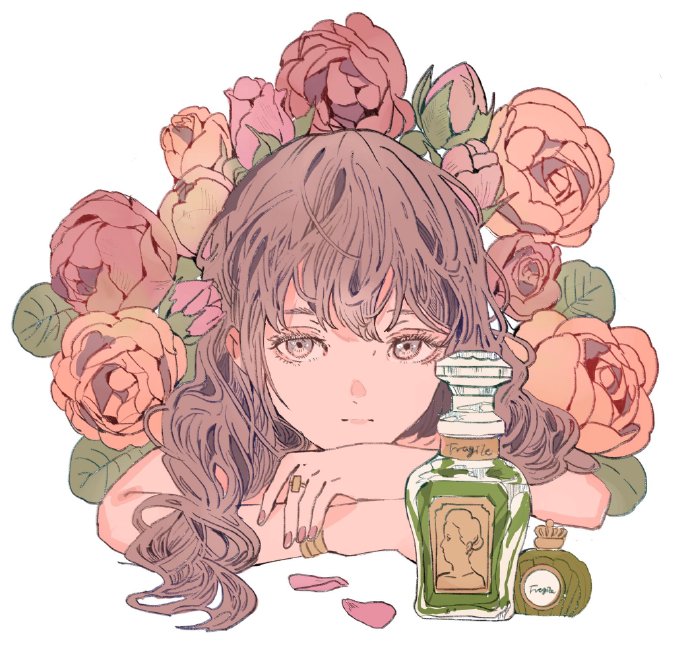据后来小马六说,当那绵堂折开的我的信时,眼睁睁地看着那绵堂面无表情,攥紧了拳头,向着墙上狠狠砸了下去,只听见一声闷响,令人头发发麻。房内瞬间一地狼藉,桌子上的台灯、电话、文件、笔墨,全都被扫在地上,就连展放康熙年间的青花瓷,也被砸在地上,摔得个粉碎。
小马六脸色惨白,额上起了一层冷汗。
当他两眼通开车来到我们家里,发现没有我的踪影,整个人阴戾各如同夜中的鹰枭。
他吼叫随从保镖,破口大骂:“什么叫还没有找到!上海滩这个地方,就算给我掘地三尺,也要把猫九九找出来!找不到人,全成仁吧。”
小马六们跟了我多年,感情深厚,他们也感受到我身处危险,此时刻更是悲从中来,捂面号啕。从军营赶到了宋达一直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听到阿五驴的哭声,狠狠掷烟头于地:“那兄,你拿主意吧。”
夜,车流如织,歌舞生平,繁华依旧。
杭州路,大新世界夜总会。
我对高高的穿衣镜看了最后一眼:我给自己涂上了蔻丹的指甲,身穿着一件身短袖紧腰攻红色的立裁洋纱旗袍,那贴身的旗袍勾勒裹着我玲珑的曲线,露出雪白的一截雪白如玉美腿和白如莲藕的玉臂,兼之身上幽香隐隐,丝丝缕缕钻入鼻腔,更是平添了无限的魅惑,妖治夺人。
我摇曳多姿一步步向大新世界夜总会走去,剪水双瞳中盈盈欲滴,整俱仿佛美玉雕成,眸底却是十分平静的神色,不见一丝喜怒。
我知道,这是我的资本,这种资本足以让男人垂涎三尺,也是我最具有攻其不备的利器,我坚定地自己安排了命运:二十载混世生涯该剧终了,混淆和精彩也许再也没有。尽管,结局还是未知数,但我无论如何了要为自己赌上这一把。
果其不然,大新世界两位笑容可掬的门童分列两旁,推开大门,以欢迎我这类交际花的到来。
大厅内载歌载歌载舞,五彩缤纷的灯光随着激情飞扬的旋律尽情挥洒。流光溢彩之下,形形色色男女贴身着,众女朗粉面含春,笑面相伴,蜂涌潮动,玫瑰香水的味道弥漫整大厅。浮中掠影中,飘扬的裙角与楚楚的衣冠沦陷脚下,恍惚一瞥,也不知道谁家的香汗花了谁家的闺女的妆容。
我在等待着。
这时,几名黑衣人正在帮张成林前面开路,两名浓妆艳抹的舞女飞奔过来迎上前,张成林来者不拒,一手搭香肩,一手捂古臀,像皇帝般左拥右抱,整个人都陷入旗袍摆下的温柔乡里。一个姑娘搂着他喂他吃果点心,一个姑娘帮他捏腿。还有一个同他打情骂俏,一直说些流氓小调调,任张成林把钞票塞进她怀里来回揩油。
谈笑间,张成林已携二女走步入舞池。在缭绕不断的的歌声中,同两名妙龄女朗纵情飞舞。
“你好呀,张大帅!”一声具有穿透性的清寒有力的声音果决地传来,那是我。
我似非似笑地摇着折扇到到张成林面前,我的闯入,有如墨池投石,黑水波波,顿起涟漪。
座上宾们的目光都在同一时间聚焦在我的身上,气场十足,龙凤之姿,风华绝纶。
张成林一脸惊奇,他环顾四周,没有发现那绵堂等人,我为何会忽然一个人敢出现在这大新世界的夜总会呢?
一脸妒忌舞女上前挡在张成林的面前,年级不过十八九岁,长得甚至是骄弱,阴阳怪气道:“哎,张大帅,又一个肉票送上门来了,怕有得你折腾的了。”
我一声娇喝:“让开。”
她显然受不了这种气。
我一记冷笑,抬手便是一记巴掌。这一记巴掌,用力极大,此女被我打得天旋地转的倒在地上。
此女是一手捂着脸,她是张成林收养的女子,纵然是被张成林纵捧在手心里,几时受过这样的委屈?
我抿唇一笑,闻言不过微微颔首:“你的女人何必要这样,我断不会虎口夺食的。”语毕,便巧笑倩兮地将挽了张成林的手,张成林的随从上前拦了我:“小姐,我们还是保持距离好些。”
我笑意更浓:“我猫九九又不是吃人的老虎,你何必怕成这样?”语毕,便将他的胳膊挥开,千娇百媚地款款走了过去。我抿唇一笑,端的是百媚横生,昏暗的灯光下,我裸露在外的肌肤光滑细腻,犹如上好的丝绸。
张成林在三大享里是色胆包天,纵然有毒的食品他也敢品尝之——我即这份有毒的食品。在大众面前,他更不可能掉了这份面子的,他就算是做戏也要把戏做足了,但不意味着他放松警觉,他仰头一笑:“果其不然,敢来这地,想必也下了决心了吧。”
我举起手中的酒杯,对张成林敬了过去:“我猫九九多少次死里求生、挣扎往复、冲锋陷阵都活过来的,我什么都不怕!这一杯,我猫九九敬你。”
张成林也将酒杯拿起,二话不说喝个痛快。
那洋酒的度数极高,我一杯杯喝,他也一杯杯喝,张成林面不改色地仰头而尽,我已有酸意,全身都在蒸笼里似的,热得难受,但张成林眼中却无醉意。
我站起身子,脚步却是不稳,不料自己一个不稳,我紧紧扶着张成林的胳膊,张成林大手揽在我的肩上,他立即泥雕木塑,因为我贴耳悄谈,像是打情骂俏跟他说:”别动,要不我开枪了,就我这小老弟性格不好,一敲击就爆,砰——”
他的随从立马发现情况有异,想要冲上来把我给收拾了,我知道一把手枪是万万不可能震住这一个同样喋血生涯的人,实际上我并没有多大把握能成功,但我真的要开枪,有谁能拦得下!
众目睽睽之下,我一把撕开旗袍一侧,已经露了一把那绵堂留给我的手枪,大厅内顿时安静下来,人早已如潮水般跑完。
我们僵持着,整个大厅的青帮子弟枪械和斧头对一个把手枪。
我从来也不懂,暴力引发更多的暴力,现在僵局一触即发。
此时的张成林还能做到面不改色,说:“把手枪给我扔下来——不,放在地上!”我嘿嘿乐了一下,也不入,还是拿手指头击下他的头。
“公了还是私了?就你一个人吗?小妞。”他的面孔由凶狠,紧张换成一副半似冷笑、半似看兴趣的嘴脸。
我咬金嚼铁般说:”这种事也哪有公了的?告诉我,鬼哥的尸首在哪儿 ?”
张成林双手投降刹那间,我忽然感到后脖子一阵巨疼,冰凉的刀锋立即架到我的脖子上,双手被狠狠地反扭在身后,喉咙被扼住,情势急转直下,我甚至来不及瞄准,我已经扣动了板机,我被制服了!
砰!
子弹朝天打了,一声巨响震聋了耳朵,一缕硝烟直冲我的鼻孔,手枪的反冲击力使我的身子摇摇晃晃,我的太阳穴跳得那么响,我几乎听不见别人说话。
一个我忽略的潜在高手——师爷,他悄无声息探住我的手腕,只一扭,将手榴弹拿到手中,交给下手,就这样不知声色就把我给制服了。师爷用尖利的目光盯着我的紧身上衣。
不能让他跑了,我要杀了他!潜在骨子里彪悍血性一时被激发出来,我愤怒大吼一声,想要甩制住我的两条大汉,向张成林冲去,全然不管劲上被刀划开一道长长的口子。我一副玩命令的架势,把张成林这个老江湖逼得用枪着我的头,一急之下,我估计他真想把我给一枪蹦了,好在,他还算冷静。
他的手下七八个人一把把我按在地上。
张成林蹲下身来,一把揪起我的头发,刀面平拍我有脸上,破口大骂:“侬还有种!不过,你玩不过我,老子要玩死你,信不信我会一刀剁下你的狗头,啊?”
我面肌痉挛,闭紧双目,刀俎鱼肉,任人宰割,努力想要傲然起身。
突然,当啷一声,已经触到眼皮上的锐利刀感消失了,周围静下来,我只觉得自己的喘息声一下子变得很响,我慢慢睁开眼,额上的血糊住了眼睛,视力有些模糊。
放开她!声音低沉,略有些沙哑,但很有震慑力。
那绵堂从天而降!
话到人到,直如一艘快船从骇浪中断桅破帆。那绵堂身姿矫健,动作飞跃。导致人车失控,车子就直直撞到在大厅的门柱上。
即便这样,那绵堂在众目睽睽之下摘下礼帽,浅施一躬:“张大帅,好久不见。”完全是谦逊的晚辈的口气。
师爷拦在前面,一脸肌讽:“那少爷,大驾光临,有什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