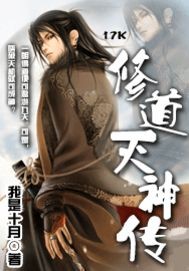列不四早已替焦晃止住了流血,却是拿起他的断手,谓然叹道:“可惜何老儿不在此处,否则便是替你续上断手,又有何难?”焦晃倒也称得上一条硬汉,兀自强忍着那钻心似地疼痛,面不改色,洒然笑道:“区区一只右手,何足道哉!多谢尊驾援手之德,在下没齿难忘!”
列不四赞道:“好汉子!可还饮得酒么?”焦晃长笑道:“有何不可?”列不四递过酒坛,道:“请!”焦晃以左手接过酒坛,仰首便“咕噜咕噜”地喝了一大口,酒水淋漓而下,意态甚是豪迈。
郭宝儿瞧得于心不忍,蹙眉娇嗔道:“都是这副光景了,还喝个不停?”焦晃放下酒坛,正色道:“宝儿小姐,大丈夫不可一日无酒,便是可志王子,虽是稚龄,却也是一日三餐,断断少不得这酒!”
燕然不禁拍手叫好,悠然神往道:“有仆忠勇如此,想来那可志王子也必是高雅之士,有机会定当拜访一番才好。”却见郭宝儿杏眼一横,不怒自威,燕然没来由地一阵心悸,讪讪地退到了一边。
柳生次郎忽然发现自己仿似陷入了一张无边无际的剑网中,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铺天盖地地便是那一道道杀机四伏的井字剑光,纵然他轻若柳絮,随风飘忽,可是那腾跃挪移的空间已是越来越小。他也是暗自心惊,倘若任由这剑网越收越紧,他如何出得自己的刀?
而谢愁飞心似老僧入定,剑如天外游龙,也不去管那柳生次郎趋退俯仰时的妖异身法,直管将手中的长剑舞得是密不通风。
层层叠叠的井字剑光无情地撕裂着虚空中的每一寸空间,柳生次郎再退再避,亦是逃不出万劫不复!须臾间,他赫然发觉,原来自己已是退无可退,只能放手一搏!
柳生次郎倏地一个回旋,黑色斗篷骤然绽开,便如黑云一般遮住了夜空。随着他一声暴喝,“魑魅魍魉,刀出不空!”,黑幕下突地炸开出一道凌厉至极的刀芒,犹如那九幽之下追魂嗜血的索命恶鬼一般,直斩谢愁飞的头颅!
燕然色变道:“不好,这厮终于还是出刀了!”欲待拔刀相助,只不过那刀芒真正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却又如何救助得及?
谢愁飞的长剑忽地嗡嗡作响,剑势倏然随之一变,大开大合,意走龙蛇,剑尖迸射出一道丈许长的如虹剑气,电石火花之间,便聚成一道斗大的井字剑光,呼啸而上,轰然架住了柳生次郎那所向披靡的一刀!
夜风中仿似凭空炸了一记惊雷,声震四野,威慑八方!谢愁飞蓦地喷出一口鲜血,脚下楼板竟已似蛛网一般,层层断裂撕开!燕然见势不妙,慌忙伸手搂过郭宝儿,足尖一点,人已似飞鸟一般,跃升到夜空中,口中急声呼道:“不四道长,这楼快垮啦,赶紧让开!”
列不四却早已横着抱起焦晃,闪身跃到一旁,兀自哇哇乱叫道:“他奶奶的,倒是可惜了老子那一坛好酒!”燕然见他身法倒也不俗,几下起落便落在了邻近一栋小楼的楼顶上,便也暗自放下了心事。
柳生次郎一刀既出,则是心无旁骛,哪料得眼前这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年轻人,剑法竟是如此地犀利,竟是硬碰硬地接住了自己这一击必杀的一刀!他只觉得眼前一黑,自己长刀上赫然传来一正一反、一拉一扯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道,登时全身真气溃散,经脉之中仿似乱作成一锅沸粥。
柳生次郎胸间热血汹涌,终于按捺不住,仰头喷出了一大口鲜血,那胸间的烦闷之意才得以稍减几分。他大骇之下,慌忙鼓足周身真元,纵身向后疾驰而去!三下两下起落后,那黑色斗篷倏地张满,宛如那恶魔双翼,挥舞之间竟似那御风飞行一般。
郭宝儿望着他的背影,恨声怨道:“臭燕然,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这大恶人走了么?”燕然笑道:“宝儿小姐有令,小子敢不听从?”他蓦然提聚真气,登时全身青光大作,直映得二人须发皆碧,手中长刀更是隐隐声似龙吟。
燕然忽然低头,在郭宝儿面颊上轻轻一吻,尔后在她的惊声尖叫中,鬼使神差地在虚空中连踏了七步,右手举刀向下一切,一道青芒便气势如虹地磅礴而出!
柳生次郎的身法固然迅似奔雷,可是这一道青芒却是疾如闪电,倏忽之间,已是凛冽斩过柳生次郎的黑色斗篷,轰然腾起了一团血雾!只听得柳生次郎凄厉地惨呼道:“一剑之仇,一刀之恨,本座永志不忘!”声音渐趋渐远,终于细不可闻,消逝在茫茫夜色之中。
忽听得轰隆隆一阵巨响,那骑鲸跨海楼终于还是不堪重负,顷刻之间便倒塌成了一地废墟。燕然见长街上登时人头攒动,混乱不堪,四周又是尘土飞扬,乌烟瘴气。他只得无奈地摇摇头,冲着列不四作了个手势,便纵身离开了这处是非之地。
燕然一气儿跑到了海滩边,可还没等他在礁石上喘口气,谢愁飞已是兔子似地蹦了过来。燕然大喜,忙抬手招呼,岂知谢愁飞理也不理,就势瘫倒在沙滩上,兀自喘息个不停。
燕然哈哈大笑,正待走上前去挖苦一番。但觉衣衫被人紧紧扯住,纳闷着转头一看,却见到郭宝儿正媚眼如丝、娇喘微微地盯着自己。燕然心底顿时“咯噔”一跳,讪讪问道:“你这般瞧着我作甚?看得人家毛骨悚然地……”
郭宝儿紧咬红唇,细如蚊呐地嗔道:“小坏蛋,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我虽是云英未嫁,却早已是许了夫家!”燕然一时也解释不清,方才为何情不自禁地吻了她的脸颊,不由得暗自懊恼不已。正没理会处,忽听到列不四破锣般地招呼声,顿时如伦仙音,慌忙应了一声,拉着郭宝儿迎上前去。
列不四见到燕然,忙凑上前,挤眉弄眼地说道:“燕小子,你来得正好。这里有桩差事,摆明了是便宜你,却不知你想不想做?”燕然一愣,满心戒备地回道:“有言在先,作奸犯科之事,千万莫要找我!”列不四怒道:“休要拿你小人之心,度老子君子之腹!正正经经的一桩买卖,哪有你说得这般不堪?”
燕然斜眼瞥着他,冷笑道:“你且说来听听。”列不四拉过焦晃,怒声喝道:“你自己来跟这浑小子说罢,老子懒得同他多说!”
焦晃抬手拱了拱拳,燕然见他右手手腕裹着一团白布,上面血迹斑斑,心下不忍,忙拱手还了一礼。只听焦晃沉声说道:“燕公子人品出众,刀法精妙,将来必成蔚然大宗!焦某有幸识得公子,实是不胜之喜,方不负了这江南一游!”燕然大是窘迫,情知这焦晃谀词如潮,言下必有所求,但听得满心欢喜,却是无话可驳,只好连连拱手,急声称道,不敢不敢。
焦晃继续说道:“焦某乃是琉球中山王殿下四大家将之一,向来自视甚高,骄横跋扈,殊不知竟是井底之蛙。今日在柳浦城惨败于扶桑浪人刀下,失去了一只手后,才算是真正明晓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道理,只可惜悔之晚矣!”
郭宝儿插口安慰道:“焦大叔何必自责?那大恶人凶狠异常,便是我在一旁远远瞧着,心里也是害怕得紧!”燕然也是温言抚慰,却见那焦晃将手一抬,知其还有话说,忙凝神倾听。
焦晃道:“宝儿小姐,你离家出走,可是去寻你远在琉球的父亲?”郭宝儿点点头,欲言又止,焦晃将手虚按,继续说道:“那你知不知道,眼下琉球时局动荡,战火一触即发。你父亲既是琉球安抚使,此刻当是殚精竭虑,极力周转在各方势力之中?”郭宝儿不由得失声“啊”了一声,急急问道:“那我父亲岂非不是危险得紧?”
焦晃点头回道:“嗯,你父亲的处境可想而知。尤其雪上加霜的是,中山王殿下日前遇刺身亡,他膝下止有二子,而可志王子正是中山王大世子!所以焦某一路披星戴月,便是护送可志王子回国奔丧,即中山王位!”
燕然不解地问道:“既然事不宜迟,那你又为何出来找寻宝儿小姐呢?”焦晃沉声回道:“公子有所不知,可志王子在金陵可是质子身份,非大夏皇帝许可,不得擅离京城半步。琉球事变后,幸得郭延玉大学士从中斡旋,皇上才允了可志王子回国之愿。而郭大学士再三嘱托,令我等千万护得安抚使郭大人与宝儿小姐的身家安全!”
燕然点点头,忽又问道:“那个扶桑刀手又是什么来历?他又为何要寻你家可志王子?”焦晃冷哼一声,森然回道:“莫不出兄弟阋墙四个大字!可志王子行踪隐秘之极,除了中山王室寥寥数人,并无他人知晓!哼,中山王位虽说难比九五之尊,觊觎之人却也大有人在!”
燕然心念一转,恍然大悟道:“莫非你想请我等护送你家可志王子顺利归国?”焦晃点头应道:“正是!燕公子刀法如神,那位谢公子剑术无双,倘若能得你二人相助,纵使前方是刀山火海,焦某又何惧之有?”
燕然挠挠头发,苦笑道:“只可惜我另有要事在身,恕难从命了。”焦晃沉声喝道:“不四道长也曾与我提过,这两者之间并不冲突。倘若你能护得可志王子周全,顺利回国即中山王位,那么焦某即便是倾尽琉球举国之力,亦要替你寻到那离魂之岛!再者,宝儿小姐的安危,莫非你就半分也不放在心上么?”
回头望望郭宝儿那一双哀婉的眼神,燕然终于怦然心动,大声回道:“好!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这就陪你走一遭琉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