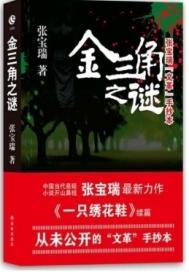柳文青神色郑重,缓缓道:“这便是柳某的恩师,昔日人称‘折梅手’的司徒守义。”
凌剑云心中一震:“这原来是司徒前辈!”
柳文青听他语声惊异,不禁问道:“你见到这画像,怎会突然如此激动?难道……”他忽然心中一跳,“你见过他?”
却见凌剑云缓缓摇了摇头:“司徒前辈据闻已不见侠踪十余年了,我没有见过他,但是……”他沉思道,“我在虬龙帮总坛的一间屋子里,却见到了一幅跟这一模一样的画像。”
凌元峰沉吟着道:“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虬龙帮主就是宗正南这厮,那么这‘折梅手’是他的师父,虬龙帮总坛有他的画像也不奇怪啊!”
凌剑云看了柳文青一眼,才道:“可是那宗……已经被逐出了师门,以他现下的行径来看,他又怎么会……还有一点,一模一样的画像,为什么要画两幅呢?”
这的确是有点奇怪,凌元峰也沉思不语了。
忽听柳文青又开口了,但语调有些奇异,竟像是在微微颤抖:“那是因为……两幅画像,是不同的人画的。”
“什么?”凌剑云不禁追问。
柳文青像是陷入了回忆中,缓缓道:“这里的一幅,是当年的丹青高手‘宫盈盈’给师父画的,当真是名家手笔,惟妙惟肖。我师妹当年也酷爱丹青,一见之下,大是羡慕,便决意要学画一幅,费时三个月,才终于画了出来。拿给师父看时,他老人家喜不自胜,称赞师妹已有了七八分宫盈盈的神韵,当即小心地收存起来。”他叹了口气,“后来师父灰心丧气,出外云游,就只带走了师妹的这幅画作。”
凌剑云闻言,沉吟半晌,忽然一惊:“这么说,那幅画应该是在司徒前辈手里才是,怎么竟然出现在虬龙帮总坛里?”
柳文青不语,脸色却沉重起来。司徒守义已然十数年不见踪影,也没有他半点消息,而本应在他手中的画作却出现在了虬龙帮总坛之中,这岂不是……
“不对不对,还有一点!”凌剑云沉思了半晌,忽然又道,“我陷在虬龙帮总坛的时候就觉得有些奇怪,那里的亭台楼阁都朴实无华,一点也不豪奢,以方才我们去过的山洞来看,宗正南不是一个简朴的人,怎会将总坛弄得那般平淡?在我看来,那儿倒是很有世外高人隐居避世的味道。”
“你是说,”凌元峰目光闪动,“那虬龙帮总坛不是宗正南建的,而只是他……霸占的?那地方原来住着的另有其人?”
柳文青闻言,沉思了半晌,沉声道:“如果那儿真如凌少侠所言,是个隐居避世之地,那么柳某的恩师的确有可能隐居在那儿……只不过,恩师是绝不可能容许他如此胡闹的……”
那“折梅手”即便不会坐视不理,但他还有没有“不容许”的资格恐怕还是个未知之数……凌剑云暗暗想道,但嘴里却也不好说出来了,想了想,忽又问道,“柳堡主,你可能猜得出司徒前辈的隐居之地在哪儿吗?或者,在他平日的字里行间有没有表现出对哪一个地方尤为喜爱?”
柳文青被他问得一怔,用心地回忆着,微皱着眉道:“恩师性喜山水,天下多少大山大泽,他老人家悉数走过,但他最喜欢哪处地方……还真难说了……”
凌剑云闻言,不禁有些失望,想了想又问:“难道司徒前辈出外远游之前就不曾交代过一句话吗?”
柳文青忽地长叹一声:“恩师被我们这些弟子气得心灰意冷,这才遽然远游……唉,恐怕连师妹都不知道他老人家行踪何处……”
凌剑云想到宗正南当年的所作所为,明白柳文青所言非虚,不禁也叹了口气。
默然半晌,凌剑云又抬头看向那司徒守义的画像,看到那肃穆的面容,端坐的身姿,忽然觉得他那看似威武的神情中却透出了一股无奈,想他一位严正的武林大侠,却教出了一个为祸江湖的弟子,诚然可悲可凉,难怪他要飘然远去了……他有些呆呆地想着,目光忽然转到画像上的一行他方才未曾注意的小字上:南归秋风雁飞回。
“南归秋风雁飞回?”凌剑云颇觉奇怪,念了两遍,喃喃道,“这是什么意思?”
柳文青听得凌剑云念了这句话,忽然眉头一皱,凝目沉思了一阵,忽然失声道:“不错,一定是雁山!”
众人都被柳文青惊动了,眼神纷纷注意起来。
凌剑云回过头,急问道:“柳堡主,你说什么?什么雁山?”
柳文青道:“我记得,当年宫盈盈给师父画像时,师父就曾经念过这句话。师父最爱的飞禽便是雁,他说过,待他厌倦江湖之时,便要终日与雁为伍,隐于尘外。”
凌剑云精神一振,道:“那就一定是了,司徒前辈一定隐居在雁山!只是……雁山,在什么地方?我从未听过‘雁山’之名。”
柳文青道:“雁山是因为南归之雁大多栖于那儿而得名,但雁山只是一个简称,那座山的全名该是‘雁宕山’。”
“什么,雁宕山?这怎么可能?”凌剑云忽然失声道。
柳文青一怔,道:“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凌剑云欲言又止,想了想,又摇了摇头道,“算了,没什么。”
柳文青也未多问,沉思着道:“若是虬龙帮总坛真的就是恩师的隐居之地,那么,我少不得也要上雁山一趟了……”
“剑云,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凌剑云正在月下庭院中独自徘徊,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语声传来。
他抬起头,瞧见果然正是凌元峰,背着手缓缓走来。
“爹,” 凌剑云嘴角一扬,“我还不想睡,所以出来走走。爹怎么也还没休息?”
凌元峰走到他身边,淡淡道:“因为我想找你说说话。”
凌剑云怔了怔:“找我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