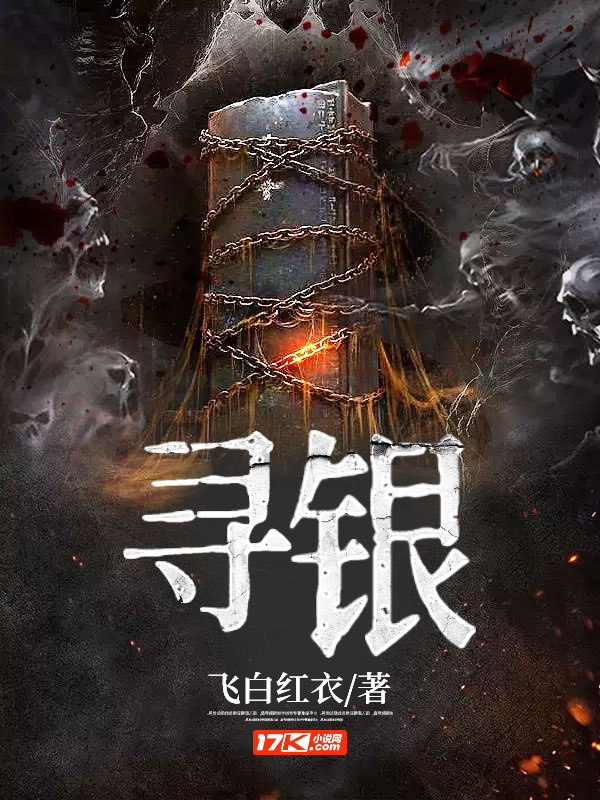我看着封面的鲜红,心里蓦地升出一丝恐惧,这是图书馆那一本,连封面的划痕都一样,而这本书在短短十几分钟内从图书馆到了我的书架上。
在图书馆看这本书时我周围并没有人,寝室的门也是锁好的,那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了。
心里蓦地生出一个念头。它,在跟着我。
我惊得说不出话,任何说服自己的说辞都编不出来,呆愣着不知在想什么。
林措:出来见个面吧。
祁热:可以,时间,地点。
林措:时间现在,地点湖心亭。
祁热:好。
我左手死死握着这本书,怕它再跑掉一般,等我到湖心亭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等了。
“你说,你可以证明给我看。怎么证明?”我缓缓开口,也许他会有办法。
“这是之前拍的照片。”他拿出手机,打开相册,递给我。
是祁热书上的那棵树,跟封面不同,这是一棵真实存在的树,在空寂的旷野,孤独矗立,连枝干的弧度都和书上丝毫不差,我盯着手机,把左手的书递给他,“你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
“我遇到麻烦了。”我抬头看他,“这本书是我在图书馆看见的,等我回到寝室的时候,它跑到了我的书架里。”
祁热脸色一变,快速地将它翻了一下,应该也是看出了那封面。
“这书和我那本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
我点点头。“是啊,看到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只是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作者的信息,封面的绘图比你的封面还要诡异一些。我排除了它出现在我书架的所有可能,无法解释。”有些无力的话,确实,很多事情是科学无法解释的,至少,目前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所以,我希望你重新考虑一下。”
“我还有考虑的余地吗?”我无奈摊手。
“貌似没有,你,已经被它选中了。”事情变得有些麻烦了,明明我只是想让她想起我,没想到卷到了另一件事里。
祁热眉头紧蹙,他的神情我有些看不透,明明我加入了,他实现了目的,为什么没有丝毫雀跃呢,反而在深思着什么,烦恼着什么。
“你怎么了,是有什么很严重的事吗?”
“没关系,我可以解决。我会保护好你的,这本书暂时放在我这里,可以吗?”
“当然可以,我不太想看见它。”我点点头,把手机还给他,“只是,我很好奇,我加入你,能做什么呢?我们平常有课,除了周末并没有很多的时间。而且我什么都不会,好像只会拖后腿吧。”
“你在就可以。”
“......”我觉得这话有一丝表白的意味,不过看着他认真的目光还是打消了自己的胡思乱想。
“跟我呆久了就免不了会有很多流言,你,”
确实这是个问题,而且并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你希望我怎么做?”我反问道,他这样提应该是有什么解决方案吧。
“我希望你默认,这样你会省很多麻烦,我也会省很多麻烦。”
我沉思了一下还是点点头。一味的解释太累了,不如就让别人误会吧,这样我和他都能清净一些。“我明白。”
“今天周五,你收拾一些东西,我们明天就出发,我带你去看看那棵树,当面看到的它跟手机里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或许你会有些什么发现。还有,”他低着头,不自然地摸摸鼻子,“我给你买了一些衣服,应该邮到了,你看看喜欢哪些挑着穿吧,就当我们工作福利。”
“衣服是你买的?可是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哪家店的衣服?”
“你室友。咳咳,没什么。”
那个周六,他带我去了宣城,那是中国文房四宝之乡、中国鳄城、江南通都大邑、江南鱼米之乡,也是他的家乡。
那棵树所在的地方很巧,就在他家附近,当然,是他一个人的家,跟祁氏一脉无关的地方。
我们只是在他家稍作休整,就去了那里,我以为要走很久的山路,特地穿了休闲装、运动鞋,结果一路除了坐飞机就是开车,只走了几步路。
那棵树就在眼前,我停住了脚步,看着它,是饱经沧桑的遗迹,亲眼看到比画上更为震撼,它的枝干极长,覆盖了周遭数十米,遮天蔽日般撑起一把巨伞,盘旋的枝干上有松鼠在啃着果子,娇憨可爱,等等,那松鼠所在的位置,我闭目细细搜寻着脑内的记忆,那里原本有一只猪首蛇身的怪物,被枝叶捆绑,掩映在密密麻麻的松针之间,神情痛苦绝望。
再睁开眼,那松鼠不见了踪影,我听得到枝叶剧烈晃动的声响以及刺耳的嘶吼,脑子一痛,感觉有什么在扎根生长,我按着头,用力捶打,希望把那声音驱赶出去。
“祁热!祁热!”我大喊着。
他走到我身边,问我,“怎么了,你看到什么了?”
“救我,我好痛。”
“哪里痛?”
“头,有好多声音,有好多针扎。”
他摸了摸我的额头,“什么都没有啊,怎么会突然痛?”不过他还是握着我的手贴上了树干,那声音和痛楚好像被引导走了一般,我舒服了很多,有些无力地坐下。
“我想回去休息一下。”我有些疲惫,眼皮重得很。
勉强爬上车之后,在颠簸之中我就睡着了。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在祁热的家里,月光直直地射进来,洒在我身上,我走到阳台,赏无边月色,听浩渺钟声,观不尽云山。
我细细想着白天里发生的事情,我确实听到了声响,头痛也是真切地,可能那里有什么跟我有关的事?我的家在距离这里千里之外的硫流,我从小根本没有离开过家乡,怎么可能跟千里之外的东西有联系。
我还想再去看看,一个人去。
我趁着夜色出了门,熟门熟路地朝那里走去,夜晚的老松比白天多了一份神秘,大片大片的月光被枝叶遮挡,只有少数光芒透过缝隙投在地上,仿佛有规律一样,构成了一幅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