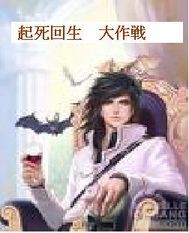“计较?计较她抢我铃铛,意图划我的脸,还想封印来杀我吗?”三个行为皆是霸道无比,不分缘由,这就是天者最宠爱的好女儿。
“可结果是她吃了亏。”
“技不如人的加害者,也是加害者。没有任何加害者和帮凶配在受害者面前站着。”
杀伐果断的天者,不会连这种道理都不懂,他的偏心自己可以不在意,他的咄咄逼人他的苛刻让自己对父亲这两个从无感变成了厌恶直到变成如今的憎恨,而憎恨的人现在就在面前。
天者揉揉眉心,有些后悔把他们放到了人世,几百年过去了,没有一个人实现他的计划,一个个还变得不可理喻,哪能不叫人头痛。“你说什么疯话?是不是人世那个腌臜地方教得太多了,让你成了这幅模样。”他怒吼道。
人世是最好的地方,有疼爱她的父母,有和善的乡邻,有平等的氛围,有多种多样的职业,她不允许有人将那里称作腌臜。
真正腌臜的地方,是他,是他那扭曲的心里。
“正是因为我从小就被人养大,我才会是这个模样。我要是被天门这些高高在上的人养大,会是你家清蓉公主那个模样吧。”
“阿铃。”天者沉声道,极力压制着怒意,听着她阴阳怪气的话。
每一次他说出自己的名字,都让人觉得无比恶心。
“怎么?天者还有事?”她的金色眼影被抹去,剩下的只有雪般苍白,目光里沁了万年冰雪,看得人嗖嗖地冒冷气。
这也是封印能力的变形,通过眼神来封印人内心的反抗和挣扎。
“你的能力是封印,我怎么从没听你提起过?”天者自然是不怕这种目光震慑,语气里隐隐带着责怪,要是早说,就不用这么麻烦,你也早就成为尊贵的公主殿下,不必折腾这么久,闹得父女离心,句句话里是火药。
“不大喜欢,所以不提。”
“你该是天门最尊贵的公主。”
“还请您别忘了答应我的事,公主这名头,我就不占了。”离开天门是必然的,阿铃的负情绪被这一父一女给毁了个彻底,实在是沉重得透不过气来,不想再同他说,沿着小径便去了芳菲苑,木门被重重地关上,一声巨响。
沉默,良久的沉默。
天者的怒意在咬牙切齿中被自行压抑下去。
“蔚连,我瞧着你们俩进展挺快。”
这种进展是他没有想到的,对如今的变化却是极为有利,感情是牵绊一个女人的最好绳结。
“过奖。”蔚连没有多说,面上也揣着几分的恭敬。
“我改变主意了,你要想尽办法把她留下,赵无极的婚事会取消,只要能留下阿铃,什么条件都不是问题。”他将手中的折扇放在蔚连的手心。
这雪中红梅折扇的重要性,知道的人并不多。
折扇可以调动主城中所有的大军,见折扇如见天者,这意思是,认了自己跟阿铃的关系。
“天者会因为一种能力就改变主意?”
“封印能力的强横你应该知道,如果顺利,她会成为下一任天门之主。”
仅仅为了一种能力,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地位和待遇,他还是觉得有些荒谬,那阿铃受过的苦算什么,流过的泪又算什么。
蔚连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他咬着唇应道,“是。”
手中的折扇刺痛了他的眼,这象征着权利的物件,轻飘飘的却又重如千斤,而它,得用阿铃的自由来换。
天者走得静谧无声。
蔚连在石桌前呆坐了一夜。
第二天便发了烧。
阿铃急急忙忙地冲进来,手心覆在他的额头处,“蔚连,我听侍从说,你在石桌上坐了一夜。”
滚烫的。
他深情地看着阿铃,带着虚弱的笑,“看你的黑眼圈,是不是昨天等了我很久。”
“没有,我才没有,回去就睡了。”她揉了揉眼睛,有些发红。
身后的如棋简直没眼看,自觉地出去了。
刚出去又进来回禀,“少将军,夫人,齐老来了,要见夫人。”
阿铃对这位老者印象极好,很是尊重的,商量道,“蔚连,我去见一见。你好好休息。”
“好。”
他瞧着自己,小嘴鼓了鼓,欲言又止。
“你还有什么事要嘱咐我吗?”她靠近了一些,满脸关切。
他指指自己的脸颊,“生病了想要安慰。”
阿铃失笑,在他唇上落下一吻,“快些休息,等好了还要陪我去铺子里呢。”
“嗯。”蔚连拿被子盖了头,挡住了面上溢出来的笑。
齐老被请到了院子里,在石凳上坐着,如棋先上了茶水和糕点。
阿铃的身份有些尴尬,不是当家主母,在正房里待客也不合适,索性在院子里喝茶聊天,权当是朋友交谈。
“铃铛小友。”齐老见着她,便笑呵呵地唤了一声。
“铃铛是随便取的,齐老叫我阿铃吧。”阿铃走到近前,礼了礼。
“阿铃阿铃,早有耳闻。”他点点头,从善如流地叫了。
“我的名声不算好。”
齐老是宫里的人,没听说过铃铛,却总是听到过阿铃的,混血公主,私生女之类的话层出不穷,总之,关于她的传闻,总是伴随着恶言和许多无端的揣测。
“百闻不如一见,我见到你,却觉得很亲切。”这姑娘气质里带着天生的不凡,总能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当日,能参加决赛多亏了齐老的推荐。”阿铃对他很是感谢,那是极大的肯定。深深地鞠了一躬。
“哎,阿铃小友,不必。”他摆摆手,枯瘦的指节上皮肉松弛,满是沟壑和褶皱。“你有实力,我有机会,选到你,令我很是惊喜。”
选到我,只是一场比赛,这话里好像有什么玄机,“我不明白。”
“看来阿铃小友不知道吗?这次比舞大会的胜者会成为祭祀舞姬,于一个月后献舞。”他遥遥看向巍峨的王宫,王宫深处那个最显然的建筑。
“没有人提过啊。”
“这是惊喜,知道的人不算多,合欢楼的掌柜也不清楚这事,只是接了宫中的指示照做。”
“......”她下意识地觉得这祭祀舞姬不是什么好活,踌躇片刻,问了问,“这个,可以弃权吗?”
“比舞大会我都看了,只有你担得起舞姬这个重任。”
“......其实我觉得千月姑娘挺好的,就是那五十两还是应该给我。”
“她的舞不够纯粹,夹杂了太多外物,美则美矣,祭祀却是不够格了。”
“齐老,我想问一问,祭祀是为了什么?”
“表示崇敬,祈求保佑。”
“保佑这天门国泰民安,是吗?”
“可以这么说。”
“既然我的事,您有听说,那也应该知道,我是一个外来者,对天门没有丝毫的归属感。”
“怎...怎么会,你在人世只会是普通人,可是在天门,你是至高无上的公主啊。”
“在今日尚未享受到的尊贵之前,我来过天门两次,活得像条狗。”她的脸上浅浅的笑,透着冰寒。
齐老对于天者的性格也知道几分,典型的无利不起早。
“那就不强求你了。”齐老叹息一声,“是天门对不住你。”
“不,对不住我的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君王,而是一个不配为父亲的男人。”
齐老有些无可奈何,只道,“若你改变了主意,尽管来找我。”
“齐老,想要我改变主意,除非是天者放我走。”
如棋将两人的谈话一五一十地报给了蔚连,床上躺着的人紧紧地闭着眼,良久,才说了一句,“你下去吧。”
“是。”
祭祀舞姬定下了千月,一时间风头无两,宫里为她赎了身,便专心地练习祭祀舞蹈。
如月则是以原先十倍的价格被卖进了花满楼,成了新的花魁。
隔天,退婚的旨意便送到了蔚家和赵家。
赵无极表现得很是平淡,让赵英明放心了几分,天者强压,无人可以违抗。
蔚连沉默着接了旨,也看不出什么起伏。
继上次蔚家赵家双双逃婚之后的大新闻变成了如今的天者仁善,不忍逼迫,便将这事做了个人情,又是一番好名声。
“蔚连,快些,阿沐姐姐已经把铺子那边收拾好了,今天可是第一天开张,我们必须得去!”
“好。”地上的男人一身白衣,睡得昏昏沉沉,含糊着应了。
“夫人,今日要什么发髻呢?”
“我也想不出,如棋你选个吧,今天很重要,好看最紧要。”
阿铃快梳洗完的时候,蔚连才醒过来,只用了几分钟就收拾妥帖,两人一道出了门。
这次坐的是马车,两匹棕马在前,由布艺车夫赶着,璇玑街宽阔稳当,一路平稳地便到了首饰铺子。
上书“流碧阁”。
“瞧瞧,我取得名字,怎么样。”阿铃等待夸奖。
“好。”
“好?”阿铃凑近了些,“就这?”
“取得好。”
“好敷衍!”她甩着袖子进了门。
流碧阁被重新修整过,却不甚华丽,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翻新了一下,胜在开阔,光照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