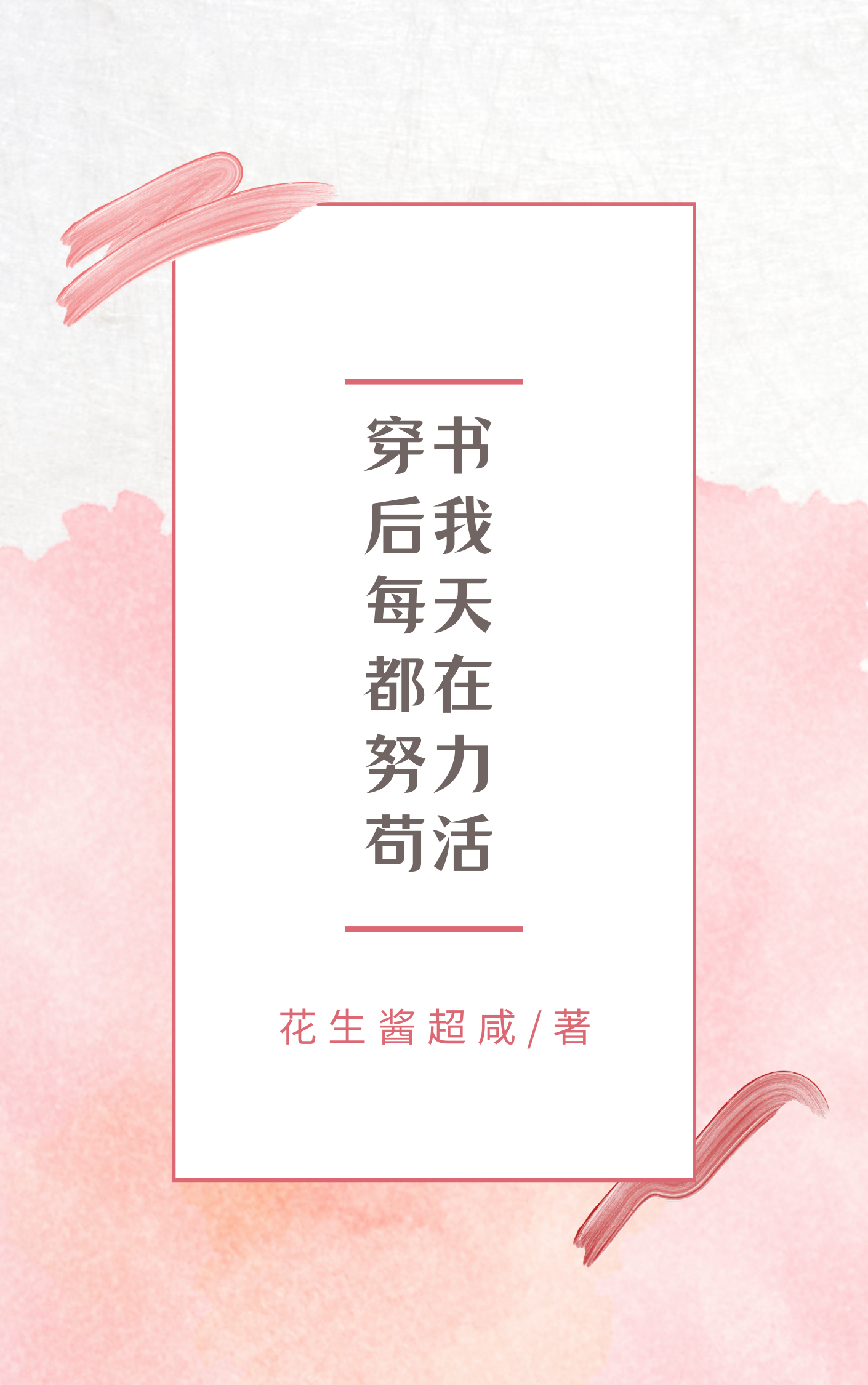我蓦的想起之前花灯会上看到的那一幕,明亮的灯笼,精致妆容的红衣新娘,这一切都同那时不谋而合,一个在漆黑中翩然诡异,一个在灼目中手握边疆。
他,就是我的边疆。
老宅是典型的徽派建筑,两层多进,各进都开有天井,周沿设有栏杆和美人靠,他直接带着我穿过前厅,到了里面那一进的阁楼内,正是他的房间,房间内的陈设是简洁的现代风格,角落原木书桌上的电脑是雷蛇灵刃,旁边还有一杯冷透的咖啡,挨着便是一张大床,洁白的枕头,深蓝的被子,突然就想起了下车时的天空,床的对面是铺满整面墙的衣柜。
“你先去洗澡吧。”他打开右侧的衣柜,找了一套男士睡衣递给我,又打开最左侧的衣柜门,指了指。“这边是浴室。”
“这,这衣服我脱不下来。”
“那,我帮你?”他笑得不正经,“可以了,现在可以了,去洗吧。”
我听话地去洗了澡换了睡衣。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地上铺好了另一床被子,桌子上多了一杯温热的牛奶。
我并不是吃不胖的体质,又懒得运动,为了保持体型晚上是不吃东西的,在学校的时候,他便每天给我送无脂牛奶看着我喝完。
“其实,”虽然我们之前牵过手接过吻,还没有更亲密的举动,但毕竟是男女朋友,我心里没有什么障碍,睡一起也没关系。
“什么?”
“没什么。”女孩子还是要矜持一点。
他洗澡很快,我还在床边发呆想事情的时候他就已经出来了,看着我的头发还是湿的,便耐心地拿吹风机帮我细细地吹干。
我们各自躺下,此刻,能听见热热轻微的呼吸声,我强迫自己闭上眼,可以看到他被挂在树上时的模样,衣衫被剪碎,整棵树都是猩红的颜色,他微动的睫毛上都有血珠滴落,他的淡蓝双眸蓦的睁大,直直地看着我,看着热热牵着我的手离开。
当时真正的画面一遍遍重现,他的不甘他的恼怒他的厌恨直直地穿过我的躯体,仿佛要将我撕碎。
他恨我?又为什么要跟我行嫁娶之礼?
不安和疑惑在我脑子里碰撞,我在无尽的疑问中徘徊,它们化身无数个绳结围绕着我一句一句地发问,一层一层地往我脖子上套,不断拉紧收缩,我只能干瘪地说着一句“我不知道”。
“咚”地一声,我坠落了,睁开眼的时候,我就趴在热热身上,把他砸得“嘶”一声痛呼。
我尴尬地往侧面一滚,正要起身先开灯,被他手臂一捞拉进怀里,用被子盖了个严严实实。
“你是故意的。”他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带着一丝得逞的笑意。
“我不是。”我一仰头,“啊”鼻子生生撞在他下巴上,痛痛痛。
我真是魔怔了,竟然开始想到悬星了。热热看我呆呆的,便关心道,“你又看到什么可怕的事了吗?”
“嗯,我看到了一些不好的事,在想着要不要阻止。”
“我不想知道别人怎么样,我只要你安然无恙。我们必须开始收集结灵了。”说话间他将我抱得更紧。
“好。”我失踪了这么久,他一定急坏了吧。“不过,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心有灵犀吧。”[我找不到你,只要他想藏,我根本找不到你。]热热的语气有些黯然。而当时的我沉醉在他怀里久违的温暖中,只当玩笑。
“那你肯定是费尽心力才找到的。我很想你,很想很想,想和你说话,和你吃东西,和你做什么都好。”
“那夜色漫漫,不如我们做一些有趣的事?”
“睡觉!”
连日来的不安在这一晚化作深沉的睡意,梦境再次开启。
于宣每天都穿着那身校服,只是没有再去城里的女子高中,偶尔做了吃的也会趁天色尚早送去山神庙,送罢即回。
生活这样无趣下去我的梦都变得暗淡无光了。
那边来人了。
隐世宗门直指此地,而此地却万卦皆乱,定位无门。连老树焚毁后的遗迹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唯有十日前,有人结亲下聘,定好日子后,拿了新人的发丝打了灵结埋于此处。
十日前。
“母亲,我要嫁他。”
“你不要嫁祁热,你要自由恋爱,我应了你,可你现在要选这样一个痨病,所有人都说他活不了了,你图什么呀。图他小时候带头欺负你?”
“母亲,我,我可以治好他。”
“就算你能治好他,也不用嫁给他呀。”
坐在一旁的父亲,默默地抽着旱烟不说话。
“求您。”
父亲终于停了动作,起身果决道,“今天这件事情我跟你母亲不可能同意的,我看祁家那孩子就很好,过几日我拉下老脸去说上一说,你嫁到祁家去。”
“父亲!你!你怎么可以这样!”于宣的语气中有种伪装的气急败坏。
下一秒,院子里就传来声如洪钟的反驳,“你的脸还不够老。”
“爷爷?!”
“宣丫头的亲事,我老爷子还是能说上话的。这门亲事,我同意了,等下张家送聘礼来,我受了。”
您那哪是说得上话,根本就您说了算。我腹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