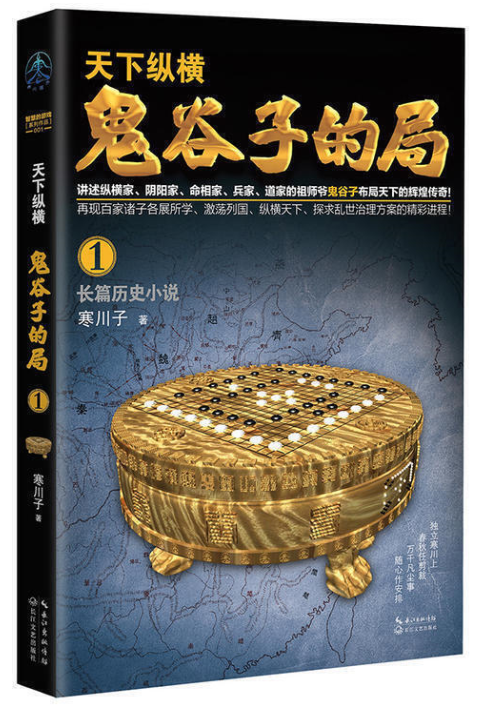“这么绝情的吗?”
“根本就没有情又哪来的绝情。”
“真是一个无情的人。”关客叹了一口气。
他在咖啡馆中又欣赏了一会儿轻柔的音乐,在七八点时便带着消化完毕的阿黑走了出去。
施枚依然凝视着窗外,看着街上匆匆的人影。直到关客的身影快要消失在门口,她才匆匆回瞥了一眼。那个男人的身影似乎在颤抖,不过还是迈过了大门。她还想再仔细确认一下,却发现已经看不到了。长大至今,她从来没有和一个人说过这么多的话,而那些话全部发自心底最深处,积压了很久很久,一朝喷发,便是突然的,剧烈的。
她把她心中的阴郁吐出大半,她的心情已经变得舒畅许多。
这一天,她一直在犹豫。
她已看出他要走了,而且很可能再也不会见面。这样的离别在她已走过的人生中已经发生了无数回,可是没有哪一回像这样的,有些温馨,有些伤感。
也许他开口说出任何请求,她都会答应。
施枚虽然一直望着窗外,但却一直等待着他的要求。
最后,他提出了他的要求,但她还是拒绝了。
也许终究只是也许,是作不得数的。
又或许,她想听的,并不是他所说的。
才离开咖啡馆,关客的双手就开始止不住得颤抖。十根手指头仿佛在弹快节奏的钢琴曲,不停晃动抽搐。他的上半身很沉,像是装满了铁汁一样沉重。他的双腿似乎无法支撑他的重量,歪歪扭扭间仿佛就要坍塌下去。
阿黑看到他的情况如此严重,就要跑回去告诉施枚。
关客阻止了他的动作,说道:“她已经够痛苦的了,何必再劳烦她呢?”
我看她很健康。阿黑用明亮的眼睛说着话。
关客扶着墙壁一拐一拐得向前走,说道:“我这点身体上的痛苦算得什么,远远比不上心灵的痛苦,因为它更加折磨人。”
阿黑想着,都成这模样了,怎么还想着装哲人呢?
一辆出租车驶过,阿黑立刻跑到路边,对着车子狂吠。
关客伸出细弱的手,向着出租车招手。
出租车司机成功得被阿黑吸引了注意力,并注意到了关客这个病人。在中年司机的搀扶下,关客终于艰难得坐上了车子的后座。
这次发作的病症是如此的突然,令人猝不及防。最近几天,脑部的瘤安静地仿佛不存在,甚至让他有一刻忘记了自己生病的事实。就在今天下午,它又回来了,让人印象深刻。
在咖啡馆里,他把颤抖的双手一直放在膝上,以免被施枚看出了什么。他的头脑中时时飘过一阵黑,最深处仿佛有一万根针在不停地刺,或浅或深。针刺一般的感觉持续了很久,但是关客没有眨一下眼睛,也没有皱一下眉头。
他对这种头痛的感觉很熟悉。既然忍过了前面几次,再多忍一次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况且美女在前,怎么好意思让她看到自己的丑态?
咖啡馆中柔和的音乐减缓了他的痛苦,施枚安详的侧脸也让人心安。他就在疼痛与柔情的双重夹击下,整整坐了一个下午。
他虽然没有看到,但还是知道施枚偶尔会不经意地向自己瞥上一眼。这种知道对方想法的感觉对他来说,并不奇妙,反而有些理所当然。他并没有深思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的脑袋早已被许多的事情塞满,再也无暇思考其他了。
他已感觉到了那一瞥间的情意,虽然很淡,但却很柔,仿佛清澈的溪水。他知道她一直在等待着他开口说话,他知道她并不想听他追债的话。
但她想听的话他并不能说。
疼痛感越来越剧烈,万千根针凝聚在一起,变成了铁锤。这让他想起了李宏身边大块头李余拿的武器。他想他的脑袋正在被那样的一把铁锤敲击着。
关客的额头上满布着汗,但还是微笑着说出要她还钱的话。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她拒绝了。
在之前安静的时间里,关客一直在想,如果他说了她想听的话,最后一人的欠款便会顺理成章地追回来,他就能写出一份完美的答卷,交上一份让红岗满意的答卷。皆大欢喜。
可是他不愿。他不愿欺骗一个这样悲伤的人。
不完美的答卷还是能交上去的,而被欺骗的人,心底的伤痕则是永久的。
他努力了那么久,已使那颗伤痕累累的心愈合了很多,为什么要在临别时,还要隐晦地再划出一道深深的伤痕?
为了不让努力白费,他选择不撒谎地离开。
……
……
幽寂的房间中,黑暗笼罩着一切。由于四十四栋楼房没有其他的住户,所以王老虎根本听不到人声。一片死寂,没有活的气息,身处这样的环境,难免令人感到压抑,沉闷。他在这样悄无声息的环境中已经呆了好几天,不待猎物到来,他就已经快要窒息而亡了。冰箱里的食物已经被他扫荡一空,厨房旁的饮水机上也只有空空的一个水桶。
他凭借想像着猎物的诱惑才没有发疯,然而如果还要在这样空寂的房间里呆上两三天的话,他可能真的要发疯。
周围的一切都是沉默的,无言的,冰冷的,感觉不到温度。也许只有他这个活人才有温度。而他的温度正在这个房间中慢慢消散。
他坐在大厅的沙发上,胡思乱想着,脑袋一顿一顿地打着盹儿。唯有安睡才能度过漫长的无聊一天。如果人还没有来,他决定明天离开。
门外的楼梯隐约传来咚咚的脚步声。
再谨慎的狮子在被无聊的环境折磨了很长时间后,也会放松警惕,何况是一只打盹的狮子。王老虎正在由浅浅的睡眠向着更深层的睡眠过度,他只隐隐约约觉得遥远的某处传来了声响,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声音意味着什么。
他的猎物已经到来,而他却茫然无知。
关客头晕眼花,摸索着布满灰尘的楼梯,一步一挪地往上爬着。他的双眼皮越来越沉重,在一眨一眨间,黑暗与现实不断地切换。过度的疼痛已使得他感觉不到疼痛,只是觉得持续不断地发麻发木。
他全身乏力,脚下使不上劲儿,因而每登上一阶台阶,就要喘上一喘。事物的任何事情都有两面,这次剧烈的症状发作反而救下了关客的一条命。他的四肢酸软,肌肉乏力,因而慢慢挪上台阶时发出的声音也很小。当然,如果他一不小心没有抓住扶梯,从台阶上滚了下去,再熟睡的老虎也会被惊醒。万幸的是,一直到第四层楼,他还是牢牢地抓着扶梯。
以往觉得登台阶不过是一件小事的关客,此刻望着那还有三层的楼梯,忍不住就要抱怨为什么楼梯那么高,每层楼梯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台阶。他一步一挪地移动,每一次移动都要花费很长时间。他有些后悔没有让司机帮自己的忙了,当时他看着司机脸上行色匆匆的样子,就没有提出扶自己上楼的要求。
阿黑走在他的身侧,关切地望着他。他一直相信他所认定的主人不会轻易地死去,就像自己一样,在布满荆棘的环境中总能找到一块平坦的土地,供自己站立。他相信病症只不过是关老大人生中的一道槛,迈过去便是坦途。
足足花费了将近一个小时,关客才爬到了自家的房门口,那个没有门牌号的地方。他苍白而虚弱地喘息着,过了很久才平静下来。他正要拿出钥匙开门,忽然感觉到小腿被咬住了。
低头看去,阿黑正扯着自己的裤腿。见关客望向他,阿黑那双明亮的眼睛回看了一眼,又充满警惕地望了木门一眼。
阿黑走在楼梯上的时候,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但是他却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由于过度关注着关老大的身体状况,所以他并没有仔细地思考。当越来越靠近房门的时候,一股浓重的汗臭味飘了过来。他灵敏的鼻子动了动,终于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
整个楼梯里的气味不对。这一栋楼里根本就没有住户,怎么会有如此浓烈的汗味?有可能是来了新的住户,但阿黑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他已发现这个气味的源头,就在家里。
关客能够读懂阿黑的心思,就像阿黑明了人类说的话一样。阿黑明确地向他传递了警惕的含义,让他不要乱动,于是关客便一动也不动的站在自家房门口,扶着墙,咬着牙,忍受着痛苦。
阿黑向上走了几层楼梯,很小心,很谨慎,尽量让自己的脚步声听起来微乎其微。这是他在以往黑暗的日子中养成的习惯,当危险来临时,就会在他的身上显现出来。
越往上走,气味越淡。
阿黑小心地走回没有门牌号的四零四房间,仔仔细细地嗅了一嗅,终于确认那一阵一阵浓烈的汗臭味便是从门里传出来的。
阿黑侧过耳朵,贴着房门听里面的动静。他听了很久,在关客的感觉中似乎有一个世纪般漫长。
然后阿黑回过头来,看着他。静悄悄地把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