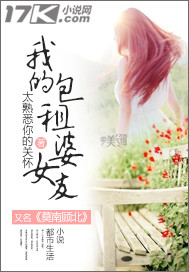赵雨涵倏然机械化地停下脚步拉下脸孔,程暮云怔住了疑惑望住她说:“怎么了?”
见她仍不作声没有给予回应,他微蹙眉头径直往音响前去,俯身关掉音响,回头轻握她的肩膀,尽力压抑烦躁的情绪,深呼一口气微笑地说:“发生什么事了,我们是两夫妻应该做到坦诚相待。”
赵雨涵幽幽抬起头,质疑又试探性地问,嘴角几乎抿成一条直线:“你身上怎么会有香水味?”
听见她的质问彷如当头一棒,该死,他竟然忽略了如此重要的细节!忘记结婚周年已经令他面有愧色,愧对雨涵,现在还胆敢身穿香水味扑鼻的西装回屋,实在错上加错,而且雨涵又是一个敏感多疑的女人,当下真不知该怎么才能平复她的心情。是应该坦白告诉她还是随便说一个善意的谎言,方可做到两全其美。
赵雨涵察觉程暮云面有难色,抓耳挠腮,便故作轻松一脸温柔地握住他的领带,轻拂他额头前一绺刘海笑盈盈地说,眼睛眨满了星星:“暮云,你不是对我说,夫妻间应该信任对方,推心置腹吗?我和你之间不应该存在谎言,我盼望百分百地信任你,所以请你不要对我有所隐瞒。”
程暮云凝望眼前笑得如沐春风的妻子,有一瞬间好似又回到二十年前第一面与她初见时,眼里尽是柔情,恍如安躺一湖波光粼粼璀璨闪耀的碧水,笑起来眼睛弯弯得像月牙般惹人怜爱,尽管在他眼前的已是一朵粉退花残憔悴的玫瑰,但每当她向他娇柔媚笑,他的心就像棉花瞬间软化,不能自已。
他抚摸她略带皱纹却净白光滑的脸颊,虔诚地说:“雨涵,你要答应我不能生气。”
“我不会生气。”
“好吧,雨涵。其实我今天确实忘记了我们的结婚周年,并且和张董还有黄董他们去和合作商谈生意,他们对我们公司的汽车很有兴趣,希望可以签成合同,谈生意自己少不了应酬,折腾下来自然是吃饭KTV夜总会直落的,所以身边少不了夜总会小姐陪唱吃喝玩乐什么的,但你要明白,这都是工作需求,一切都是为了公司。”程暮云一边解释一边留意赵雨涵的反应,小心翼翼阐述完生怕会有一字一句的错误表达触发她敏感的神经。
赵雨涵默默推开他,走到餐桌前,背对着他,声音没有语调变化地说:“张董事长,是上次你舞会的舞伴吗?”
“是的,但你不要误会,我们确实只是合作伙伴,绝对没有不轨的关系,作为我的妻子你应该了解与信任我的为人。”程暮云走上前来,紧张地说。
“所以你身上的香水味不是张董事长留下的,是那些陪酒的女人吗?”赵雨涵仍然背对着他,却异常冷静。
“对。”
“多少个女人?”她依然不依不饶地寻根问底,只是语气出奇地沉着。
“多少个?我根本没有数!这压根就不重要,那只是应酬所需叫来的女人,我是生意人,掌管那么大间公司没有可能避免这种状况,即使我对这种女人没有一点兴趣,毕竟我需要考虑客户的需求与心情,心情好了自然生意就谈成了你懂吗…”程暮云走上前紧握她的肩膀,翻转她的身子。
“呵呵。”赵雨涵突如其来的冷笑让程暮云倒吸了一口凉气,感到背脊一阵透凉,仿佛能预见一场暴风雨的来临。
“怎么?不是那个姓张的勾搭别人丈夫贱女人狐狸精的香水味,而是夜总会下三滥千人骑万人压的臭**娼妇留下的恶心臭味让你骄傲了吗?你还得瑟吗程暮云?”赵雨涵轻挑眉毛,扬起一边嘴角耻笑地盯住程暮云。
“你一把年纪还想走进花丛死在百花下?即使?你的意思就是你对那些恶心得被男人玩得下体早已腐烂不堪的不堪女人颇有兴趣对吧?我呸!你就不怕得性病不得善终?你都他妈半百岁的人还不懂为自己积点阴德吗?哈哈哈哈哈?”赵雨涵猝然情绪失控,痛楚地不停惨笑,用阴森不屑又怨恨地眼神望着程暮云,那种冰冷的眼光与刺耳地笑声深深刺伤了他,就像被一股寒冷彻骨的气体紧紧笼罩,一时之间动弹不得,瞠目结舌地只是吐出一个字:“你…”
半晌他才反应回来,冷笑地带着失望又讥讽的语气,用手轻拂额前的刘海,厌恶地说:“我真傻,怎么会认为你真的可以变回从前。我真的没有想到如此恶毒低俗的话语竟会出自自己明媒正娶的糟糠之妻口中,令我大惊失色,久久不能回神。你的嘴就像废墟里的坑渠水般滔滔不绝地恶臭,诅咒自己丈夫的话语从你口中吐出竟顺溜得如同演讲稿般出口成章。你简直是个多疑心重狭隘自私疯癫恶毒不可理喻的疯女人,让我厌烦至极!”
“你说什么,你…!!!!”赵雨涵睁大乌黑亮丽的双眼,眼珠子凸的甚至快要掉下地面,急火攻心令她血压直升,她双手紧紧搀扶餐桌,但心中的怒火熊熊不灭,暴怒的青筋一下子全凸显在她粗糙苍白的脸颊上,脸部因怒气颤颤发抖而变得狰狞,她一转身双手向餐桌上的饭菜直冲而扫,拿起周边的餐碟发狂地向外扔,扔掉水果,扔掉烛台,扔掉刀叉,扔掉所有,扔掉心血,扔掉一切的希望与期盼。
程暮云怒瞪赵雨涵,像望着一个泼妇般厌恶地看着她说:“简直就是一个泼妇!”
“我泼妇?没错!就是我这个泼妇为了我们的结婚二十周年忙出忙进,灶边炉台,而你呢?你却浑然忘我于风月场所,流连在野外莺莺燕燕怀抱里花前月下,一个张董事竟然还不能满足你,还想着像古时候皇帝般淫乱昏愦,妄想后宫三千佳丽环绕,只可惜你生错年代,也不见得你有这样福气的命!”她嘴角抿起,嘴唇紧闭,牙齿狠狠咬着嵌入唇肉,嘴边明显透出满满鄙夷而愤懑的气息,眉头紧锁,眼角轻扬,眼珠子因激动而暴突,眼球里遍布血丝,不时惨烈地大笑又转而压抑地哼哼冷笑着。
“你,你的嘴就像喝尽了全天下最毒的酒,各式各样,功能却永远如出一辙,每字每句都能够杀人于无形,比粗口脏话还要恶毒,好比用一把把锋利的刀又狠又深地插进我的胸膛,我再也不想和你多说一句话!也不愿意和你多呆一秒钟,我怎么会对你抱有期望,实话告诉你,我早就不愿意记起我们的结婚周年,这对我来说没有一点的纪念价值!你知道吗!我后悔死了!我早就后悔透了!只是基于道德伦理为了维持我固有的好男人形象才没有说出来!我真的很后悔和你结婚,留在这个家就像呆在监狱!不!是地狱!”程暮云目光如炬,如同火山爆发一下子爆发自己的满腔怒火,他认为自己已经够隐忍委屈,也熄灭了原本对赵雨涵重燃的包含了怜悯与愧疚的星星爱火,说着要转身走向大门口。
“啊!”赵雨涵大叫一声把凳子推倒,狠狠转头对程暮云怒喊:“你去哪里,回去夜总会找野女人还是那个张董事?”
“够了!我只想逃离你!我和张董事长只是普通搭档关系!你侮辱我就算了!不要再去随意诋毁无辜的人的人格!而且!我对夜总会小姐只是应酬需要!我求你消消停停吧!放我一条生路!不要再发疯了!求你做一个正常的人!”他失声大喊,手舞足蹈,手握拳头因激动而狠挥墙角却忘记疼痛,随即“趴”一声大力关门。
“暮云!!你去哪里!你给我回来!”赵雨涵拖着一拐一拐的腿因几分酒醉踉踉跄跄追出去,看见程暮云发动车子她立马跟上前,重重拍打已关上的车窗,程暮云不耐烦地摇下车窗,烦躁地问道:“你到底要干什么?”
霎时赵雨涵整个身子软下,双臂挨在窗檐上,语气也柔软地哀求着不再咄咄逼人说:“暮云,方才是我不对,是我没有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求你原谅我,不要离开,今夜是我们的结婚周年,我们好久没有好好地聊天,你不是说过我们应该有个崭新的开始吗?”
望见赵雨涵柔弱可怜苦苦哀求的模样,程暮云一瞬间动了恻隐之心,始终犹豫着没有踩下油门。
见程暮云默不作声,赵雨涵嘴角颤栗地苦笑着,委曲求全地面部每条神经都在抽动,说:“我不再计较你和张董事长还有那些野女人的事情,你们怎样我都没有关系,上床也没有关系,真的!你不要离开我就好!我不在乎你们偷情,求你不要走!”
假若她不再出声,只是泪流满面地沉默,或许程暮云真的一时心软会留下来不走,但一听到出自她口中的这些放下身段贬低人格的恶俗的话,自尊心就隐隐作痛,深深受创,他厌恶地像看着一个丑陋无比的丑女人那样望着赵雨涵,狠狠地一字一句说:“滚开!”
“我不要,我不要让你走!求你不要这么对我!你不能抛弃我”赵雨涵狠狠抓住车门的窗檐离开。
程暮云粗鲁地接下自己身上的安全带,稍微站起身来用手大力地推倒赵雨涵说:“闪开!”,随即赵雨涵倒在地上,霎时程暮云挂下车档,立马深踩油门,车子瞬间像一支离弦的箭般疾驰在马路上,如轻烟一般消失于她眼前。
程思雨这时从家里跑了出来,一直躲在楼上默默偷看不敢出声的她终于按耐不住悄悄跟着母亲与继父出来,只是她依然害怕会让赵雨涵发现自己全然目睹眼前狼狈的一幕,于是站在门口一言不发纹丝不动地注视一切,看见母亲心碎坐在地上无力地站起身来的样子,她感到痛心疾首,她恨母亲的冲动多疑与尖酸刻薄,痛心母亲的手足无措与委曲求全放下自尊的模样,也怨继父没有足够的包容体谅与关爱,但她没有能力改变一切,也没有办法去替母亲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