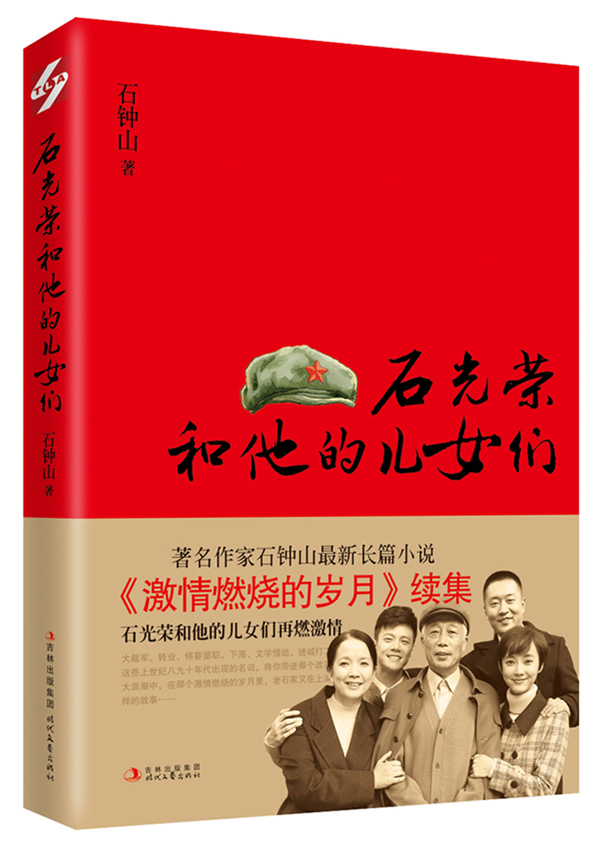用过了午膳,稍作休息,凤墨影如常前往练武堂。
练武堂在青云殿的后面,独属于女帝一人。北堂渺因是影卫,身份特殊能出入其中,外臣是没有机会进入的。
这一次,北堂渺几乎与凤墨影同一时间到了练武堂前。她朝他微微一笑,即刻屏退了跟随过来的余人,两人一前一后进入了堂中。
自从昨夜青云殿中发生那事后,北堂渺看她的眼神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似乎恢复了当初的冷漠与疏离。
凤墨影心里笑笑,也不多作理会,等他关好了殿门后,直言问道:“昨夜直至今日沐王府里可有什么异动?”
北堂渺自觉地站在离她三步之外的地方,拱手一礼,回道:“井然有序,平静得出奇。”
凤墨影眯了眯黑眸,沐王府的主人在夜里被临时请进了宫中来,直至今日不曾回府,事发突然,绝不寻常,王府里的人竟如此淡然自若?
若不是王府里的管家有极强的威势与手段如何能镇得住下面的人胡思乱想呢?再不然,就是王府里个个都是千锤百炼的精英,早已见惯了惊涛骇浪?
可这王府不可能就连扫地做饭的人都武装到底了吧?
剩下的,就只有管家有意地将这些人管束了起来。
凤墨影随即又问:“那个管家可曾派人到宫门外或者什么地方去打听沐王的消息?”
北堂渺一张冷漠脸站在那里,正儿八经地道:“没有,王府管家如常地打点着王府里面的事物,仿佛并没有觉得沐王一直进宫未返是什么要紧的事。”
凤墨影眉头挑了一挑,觉得有趣地笑了一笑,低喃道:“事若反常必为妖,这岂不是欲盖弥彰?”
按照常理,管家在这个时候不是应该遣人到宫门前找相熟的宫里人打听一下自家主子的消息,应该担忧他一夜未归的原因?或者是再要遣人去相熟的权官那儿探问一下沐王在宫里的消息?
只有两种情况下,才会对自家主人的安危不管不顾。
一种是,根本就不在乎自家主子的生死存亡,就连沐王府是否会遭难从而连累到他自身都无所谓,兴许他早已有了后路;一种是,早就料知沐王进宫后,会有人来监视沐王府的情况,就假装全然不知沐王会有危险的样子,以便不让别人对自己生疑,属于矫枉过正。
北堂渺冷不丁地打断了她的思绪道:“沐王府里那个漠回人倒是很焦急,三翻四次地向管家打听沐王的消息。那管家倒是一遍遍好言安慰他,说沐王进宫是常有的事,沐王进宫彻夜不归也是常有的事。”
他的语气看似淡然,但她怎么听着总觉得刺耳,总觉得有一股潜藏在底下的讽刺意味?
凤墨影瞠了他一眼,北堂渺却恍如不见,镇定自若得很,只是脸上的那一层薄冰一直没有掉下来过。
他这是对她昨夜赐死了斐玉晏很有意见?认为她这个人仍旧是那样的心狠手辣,心机阴沉,不值得他尊重和效忠?
凤墨影在心里叹了口气,也同样无视他的态度与表情,同样淡然不惊地道:“这漠回人究竟是什么身份?他与斐玉晏又是什么干系?”
北堂渺近似机械人般地道:“他是漠回国的三皇子秋玉琢,此番出门游历暂住在沐王府。与沐王应是旧交,两人日常琴棋书画宾客相酬,性情相投,看是挚友无疑。”
凤墨影听了此人的身份,即刻犹豫道:“此人是漠回国三皇子,又恰逢其时出现在上京?那漠回兰籽之毒,难道是与他有关?”
北堂渺对她的问题不加以评论,只是叙述道:“秋玉琢是侧妃所生,那侧妃身份低微,他也是一个不受宠的皇子。”
凤墨影疑惑道:“一个不受宠的皇子竟能够随意离开皇宫,出门四处去游历?”
北堂渺的表情没有变化,声音也没有起伏,“自从漠回国被陛下收服后,那些宫规礼制就没有真正的皇室那么严苛了。一个不受重视的皇子想要出宫去游玩,还是可以的。没有利益的阻碍,也就没有人会去谋害他,他自己不怕艰辛也就妥了。”
这人分明就是对她有意见了,每一句话都有怼的成分在。偏偏他又用着那么平淡之极的语气,让人触不着他的火药线,无从借题发挥。
凤墨影暗想,这人肯定是冷战中的高手。谁跟他认真,谁就输了。
她调整了一下心态,将他话里话外的感情全部忽略掉,只吸取了他话中那些有用的信息。
如此一过滤,蓦然就感觉这个世界清净了许多,空气也清新许多了。
凤墨影最后用吩咐地语气向他说道:“北堂,你去将此人抓来审问一下。人千万不要弄死了。”
北堂渺果然即刻对她瞠目而视,那眼神就是早料到你是这种人的意思。
凤墨影在心中呵呵一笑,又补充道:“不妨也对那管家审问一番,吓唬他一番,看能说出点什么来?”
北堂渺凝滞了好半晌,与她的眼神对峙了半息后,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应了一声:“诺!”
凤墨影淡然一笑,开始活动了一下手脚,口中说道:“北堂,昨日的招式,寡人已练过,且请你指正一二。”
北堂渺无动于衷地抬抬眉,斜眼瞥了她一眼,口中谦逊道:“臣不敢,还请陛下赐教。”
凤墨影摇了摇头,不发一言,从兵器架上抽出两柄木剑,一柄握在手里,一柄朝着他抛过去。
北堂渺右手一抬,动作轻盈利落地将木剑妥妥地接在了手里。
那动作轻而易举又潇洒轩举,让人想要鼓掌喝彩。
凤墨影目光发亮地瞧了他一眼,仍是那一张千年不变的冰山脸,偏偏身上又透着一股莲花般纯净高雅的气质,翩翩少年郎,除却君身三尺雪,天下谁人配白衣?
淩浮宫弟子中的第一人,果然风采照人。
她左手中长剑一横,已朝北堂渺发起了进攻。以他所教的招数,结合了雪灵染的指点,再经过了自己的揣摩与领悟,夹杂着一往无前的气势向他一剑刺去。假如面前的人就是刺客,那她该如何出其不意的自保?
她的招式在北堂渺眼中宛如透明一般,待那一剑几乎刺到了面前,他才右手举剑轻轻一挡。用剑面将她的剑尖抵了回去,心中却同时亦生了一丝疑惑,为何这一式剑招会如此的纯粹,完全没有了她自己剑法的半分影子?
就在他稍稍出神的瞬间,凤墨影眼眸一沉,连续三剑再刺,招式中看不出明显的变化,但这三招却连贯得如流水行云。第一招将第二招的破绽补上,第二招又将第三招的破绽补上,一时不及细想,他手中的剑便似有意识般一一化解了开来,最后一招时竟下意识地用上了内力。
“噗”地一下,他的招式夹杂着内力将凤墨影连人带剑荡了开去,她后退几近飞去,一个站立不稳便坐倒在了地上。
凤墨影怔了一怔,刚才那股由对方木剑中传过来的宛如电流般的气息,便是内力?威力竟然如此的大,让她猝不及防间便栽在了地上,这还要怎么打?
她头疼了,那些刺客的内力,又该拿什么去抵挡呢?
北堂渺亦是怔了片晌,才反应过来。他看向凤墨影,想不明白为何她不用内力抵御。
她刚才运用他仅教的几式剑法很是高明,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过这三招可以如此连用击敌。正因为威力极强,他的内力才自然而然地运到木剑上去抵挡对方的杀招,只是想不明白她为何不用内力抵挡?
而是任由自己这样狼狈地在他的面前摔坐在了地上?
他一时无措,又是不解,只缓缓的拱手请罪道:“北堂一时鲁莽,还请陛下恕罪。”
凤墨影神色复杂地摆了摆手,仿若无事地说道:“也并不是你的错,是寡人自从受伤以来,内力运气总是不顺畅,在对敌之时不免有些阻碍。”
她一面说着,一面用右手在地上一撑,站了起身来。
这一下屁股上疼得很,她却不能表现出来。这是多尴尬而又没面子的一件事?她在心里呲了呲牙,暗自的不爽。
凤墨影的眼色阴郁,冷冷地瞪了北堂渺一秒钟,瞬间恢复如常。也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反正是在她的身上讨回了一些前几日受罚杖刑的利息了。再这样陪练下去,对她是百分百的不利啊!
她将手中的木剑耍了耍,看似随口问道:“不知余下的剑法,北堂什么时候才能悟出来?”
一提到剑法,北堂渺登是神色一正,道:“这两日尚未能静心思索,请陛下且再宽容臣几日。”
凤墨影经他一提醒,回想起他又要整顿暗卫,又要给她监视沐王府,更要随时注意宫中的动静,确实是马不停蹄,无暇进行这等脑力创造活动。她检讨了一下因自己的心急而忽略了别人的辛劳,心中微带歉疚说道:“是寡人太心急了,北堂你且回去好好休憩一番才说。”
对于她此刻的和颜悦色与语气中透露出来的歉意,北堂渺不觉有些意外,与他记忆中的那个女帝有些不能重合。他的目光极快地在她的面上一掠而过,但见神色真诚,并不似伪装。
北堂渺眉梢微皱,想到她因气息不畅而无法运用内力,若遇到刺客极有可能无法自保。自己也不能无时不刻地守在她身边护佑,踌躇了片刻,试探地问道:“陛下照着那本医书修复经脉时,是否遇到了什么障碍?”
凤墨影目光微微一亮,想不到他会主动来关心自己的内力问题。这个问题一直不能解决,就无法对抗来于这个时代的野蛮力量袭击。但这个问题若非要找谁来解决,她又不得不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