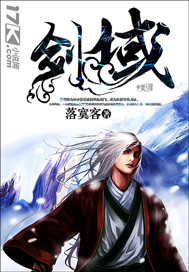虞夫人的人皮丢了,是这商都最大的事情。成汤王勃然大怒,怒视黄貂寺、张伯谦,厉声道:“黄貂寺、张伯谦,把吕清闲、竹剑客抓回来!”黄貂寺、张伯谦面面相觑,黄貂寺道:“吕清闲已被苏小迎抓住,现在大牢中。竹剑客打退宫庭侍卫逃了出去,属下已令人封锁城门,全城搜捕。竹剑客受了重伤,出不了城,不久可以擒下!”
成汤王厉声道:“好个吕清闲,好个竹剑客……很好,很好……”黄貂寺望了望成汤王,欲言又止。成汤王道:“你想说什么?”黄貂寺道:“属下以为……此中另有隐情……”
成汤王眉头一皱,他望着远处窗台火光之处,渐渐冷静下来,转念一想,又否决了竹剑客和秀才盗窃人皮的的想法,无他,竹剑客和秀才要这人皮也没什么用。
何况那秀才诡计多端,却都是堂堂正正的阳谋,应该不会做出用人皮威胁成汤王的事情,那么这其中,就是有人已经将算盘打在了成汤王的身上,而虞夫人就是这盘棋的棋眼。
成汤王没有虐待吕清闲,却也不曾放了他们,这是黄貂寺的主意,不论来者是何人,以不变应万变,才是上策,让这人不能察觉成汤王看破了这是一盘棋,才是关键。
商都依旧不变,但是御赐天师和一个剑客盗窃虞夫人人皮的事情却不胫而走,从那御林军中散布了出去,整个商都都知道这么一件事。
只是成汤王一直没什么动作,别人想来是在严刑拷打,或者那秀才和剑客就已经死在了大狱之中。
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之前有人写诗污蔑虞夫人魅惑成汤王,霍乱朝纲,这人当天下午就在松鹤年党前面的菜市口被千刀万剐。
现在谈起来也让人心有余悸,况且那御林军传出来的消息还有什么不可靠?那可是成汤王身边最近的人,再听那言语之中,都是一阵战栗。
别人也就知晓,这二人就算没死,只怕也差不了多少了。于是,人都好热闹,也就有人天天蹲在松鹤年堂,盯着菜市口的动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边杀头。
约么过去了半个月,也没什么动静,商都陷入诡异的安静,那驿站中的飞贼流寇却是日益少了许多,这倒是怪事。
等到了帝国中兴的日子,人们才瞧出了一些端倪,商都倒是安静了,但是兵马大元帅宣武王却是不安分了起来。
帝国中兴是在外戍边的统兵大将述职的日子,宣武王往年来的最早,今年却来的最晚,还带了十万兵马,将商都围了起来。
宣武王并没有先到皇宫,而是到了松鹤年堂,和老掌柜的讨了百十副刀伤药。松鹤年堂的刀伤药,最是出名,但是这刀伤药却不是给活人用的。
之前在菜市口杀了头的人,都要带着断头埋葬,在商都百官看来有违天和。所以请了一个专卖刀伤药的老掌柜,在菜市口边上开了一个松鹤年堂。
松鹤年堂的刀伤药就是给这些菜市口杀头的人准备的,砍刀一落,那脑袋咕噜噜掉下来,家里人捡过来,拿着松鹤年堂的刀伤药往脖子上这么一抹,大老远一看,就好像这脑袋没掉下来一样。
这宣武王是成汤王的弟弟,向来松鹤年堂的刀伤药只卖给杀头人的亲人,宣武王来买,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况且,宣武王买了足足一百零七副刀伤药。好事的人一算,心理慌了神,皇室的人足足一百四十三口,但是刨去了宣武王一脉的人,却是正好一百零七人,于是,宣武王去了松鹤年堂的事情,一时间就成了商都最大的新闻。
离开了松鹤年堂的第三天,宣武王仍旧没上殿面见成汤王,而是在那菜市口推出去了一百零七个人,用宣武王的话说,这些都是惦记着皇宫里面重宝的飞贼流寇。
驿站里面的人跑出来观瞧,可不就是那少了的贼人嘛,不多不少,一百零七人,正好在此。
宣武王一声令下,一百零七个人头咕噜噜落在地上,一百零七个官兵将那飞贼流寇的脑袋抓起来,在脖子上抹了松鹤年堂的刀伤药,不分老幼老女,一块埋了。立起一块石碑,上面却也没有一个名字,宣武王亲自砍了一个碑角,代表叛逆之人埋葬在此。
宣武王的行径分明是向成汤王示威,那一百零七个脑袋就是告诉成汤王,这飞贼流寇我杀了,皇宫里面的人我也能杀了。况且那城外十万大军围上了商都,谁能说宣武王就是没有半分私心?
到了第五日,宣武王终于是上了大殿,只是去的时辰不对,赶在了文武百官之前。按理说,在外戍边的王爷要是回到了朝堂之上,理应通报之后再去,但是宣武王却先到了殿堂之中,这其中更是耐人寻味。
等到文武百官上殿的时候,却是发现宣武王并不在此处,但是宫廷之中,却挂满了黑布灵幡,极尽哀荣,当中一幅挽联“难忘手泽,永忆天伦。继承遗志,克颂先芬。”落款是宣武王伟!
这挽联自然是写给已故先皇,但是先皇已故十八年,如今再来一幅挽联,这其中的道道,就不是文武百官明白的了。但是宣武王和成汤王之间的问题,大臣们也不敢随意插手。
宣武王站立殿前,头戴玉冠,身披黑色蛇袍,腰悬镶珠长剑。他背负双手,望着宫殿之中,微微冷笑。两旁立满了他的侍卫,均持戟佩剑。
文武百官见到这阵势,无不皱眉蹙眼,远远让开。有文官低声道:“大殿之内不得佩带兵器,宣武王这是想干嘛?”一个武官冷笑道:“还不明显吗?”
张伯谦上得殿来,见到这个阵势,眉头紧皱。旁边闪电剑苏小迎低声道:“宣武王左边那个高高瘦瘦的是白云山剑客冷星月,右边那个黑衣男子肩头奇高,想必是扛鼎派屠剑臣。”
侍卫林雨生道:“扛鼎派?这是什么门派?”苏小迎道:“你可记得百余年前力扛九鼎的那位使枪大高手?”林雨生道:“你说的是当年以肉体之躯扛鼎砸死四爪金龙的楚氏?”
苏小迎望着那黑衣男子,低声道:“不错!楚氏当年扛鼎屠龙,举一根霸王枪挑死仙人。因此后辈有楚人创扛鼎派,只是到得此时扛鼎派已不不如前。”林雨生冷笑道:“力气稍大,一届莽夫。”
宣武王旁边那黑衣男子忽地抬起头来,双眼射向林雨生。林雨生被他这么一瞧,只觉如被刀剑所迫,浑身冷汗涔涔而下,急忙低头不语。所幸黑衣男子瞧了一眼便低下了头。
苏小迎沉声道:“宣武王后边又有三数人,太阳穴深凹,绝对不是易与之辈。”此时宫中高手顾清风、顾清流等人皆互瞧了一眼,点了点头。
张伯谦大步走到宣武王身前,行礼毕,大声道:“王爷来到大殿,何故带着这么多的侍卫?丧幡?所为何意?”宣武王缓缓瞧了张伯谦一眼,道:“所来除叛!”张伯谦沉声道:“除叛?王爷来到大殿前除的什么叛?”
宣武王道:“成汤无道,弑父篡位!宠娇惜媚,荼毒百姓。我来除商都之叛!”说到最后一句,猛一挥袖,声音洪亮,双目灼灼,群顾众臣。只骇得文武百官无不变色失声,均窃窃私语起来。
张伯谦厉声道:“胡说八道!宣武王你胆敢再说一遍?”
宣武王伸手往下虚压,文武百官的声音渐渐小了。宣武王冷冷注视着张伯谦,道:“数十年前,父皇病危,宫中是何人侍候?”
张伯谦道:“当日大王往南方除乱,在先皇跟前侍候的人是王爷。”宣武王道:“不错!数十年前我父皇可留下圣旨点明谁来继位?”张伯谦微微变色,道;“先皇重病之时,尚未来得及拟旨……”
宣武王仰天哈哈大笑,笑声震得白旗丧幡不断震动。张伯谦道:“你笑什么?”宣武王厉声道:“好笑,好笑!当真没有拟旨吗?还是你张伯谦偷天换日、满天过海?众大臣,你们可知当日情况?”
文武百官面面相觑,噤若寒蝉。张伯谦气得浑身发抖,大声道:“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宣武王你想造反不成?”
宣武王声色俱厉地道:“大胆张伯谦!谁在胡说八道?”
此时,殿后有人高声道:“陛下驾到!”队伍排开,一众婢女侍卫拥簇着成汤王而至。文武百官忙分立一旁。
成汤王走到殿下,望了宣武王一眼,眉头一皱,道:“何意?”有文官上前禀告。成汤王道:“王爷,他所说是真?”
宣武王微微后退了半步,又挺直了胸,微笑不语。旁边有宣武王军师姜天师上前道:“大王弑父篡位,诛杀贤良。宠媚后宫,荼毒天下。我王奉上天恩怜,携兵于此,大王还不俯首认罪?”
成汤王道:“姜天师?”姜天师欠身道:“不错。”
成汤王怒道:“姜贼曾为朕臣,为何纵恶反叛,犯朕关隘,恃凶逞强,不遵国法,大逆不道!今日当朕面于此,尚不倒戈悔过,犹自胡言乱语,抗拒不理。该当何罪?”
姜天师哈哈一笑,道:“陛下居天子之尊,诸侯守拒四方,万姓供其力役,锦衣玉食,贡山航海,何莫非陛下之所有也?古人云:‘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敢与陛下抗礼?今陛下不敬上天,肆行不道,残虐百姓,杀戮大臣,惟妇言是用,淫酗沉湎,臣下化之,朋家作仇,陛下无君道久矣。陛下之恶,贯盈宇宙,天愁民怨,天下叛之。吾今奉天明命,行天之罚,陛下幸毋以臣叛君自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