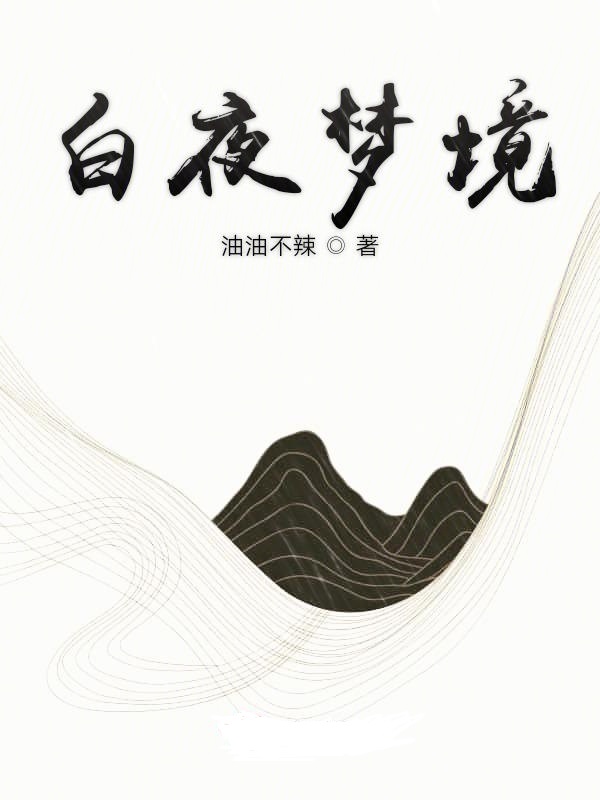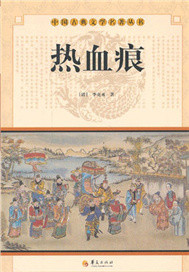王千启将冒着滚滚热气的牛肉汤给自己盛了满满一碗,先是小小嘬了一口然后才眯起来起眼睛,一脸享受的模样:“比如说,咱们需要考虑一下,既然这里的庄稼已经成熟了,那么远在固山郡的那位庄稼汉会不会赶过来收割庄稼呢?你说,他会眼睁睁看着,这两块庄稼地一块被人给糟蹋了,一块被人给捷足先登提前收割了?”
正在大口啃食牛肉的单西行抬头看了对面的王千启一眼,一脸不可思议的样子:“你是说那个曾在固山郡掀起血雨腥风的那位游方术士会回来?为了一个不过二阶的妖鬼?”
王千启微微一笑:“你是看不起妖鬼还是看不起那只墙中猛鬼?”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都一百年了,他还能想起来?”
“呵呵,别说布局一百年了,就算是一千年在有些修行者眼中也不过是弹指一瞬而已,而且他们的心思之缜密,计谋之深远,江湖之高、庙堂之远!没有什么是那些家伙不能够算计的!”他说着指了指墙中厉鬼,又指了指远处灵官庙的方向:“这些事情对于那位游方术士来说肯定都是他某一个计谋之中很为重要的一环,属于特意在小本本上面记载下来的那一种!你知道为什么么?”
单西行口中塞满了牛肉,一边缓缓咀嚼着一边问道:“为什么?”
“先前我在灵官庙发现了一个非常隐蔽的阵法。”
“哦,你是说那个隐藏厉鬼气息的阵法么?不隐蔽啊,我也能感知到。”
王千启冷冷一笑,给了他一个白眼:“那只是那头二阶妖鬼自己布置得用来隐藏自己气息的简单阵法,是个修行小有所成的修行者都能看出来,我说的是另外一个极为隐蔽的魔道阵法,那个阵法沿着整座灵官庙的风水气运而布置,而且藏匿的极深,别说是你,如果不是我将星宿派的青眼秘术修行到极致,也难以发现其中隐藏的秘密,只会是当做灵官庙附近的风水气运被那头妖鬼给破坏了!”
他说着轻轻一敲身前的木桌,发出一声咚的声响,然后对着连忙小跑过来的酒楼小厮笑着说道:“麻烦催促一下厨房,我这位兄弟吃的比较快。”
酒楼小厮看着桌子上已经空空如也的两个盘子,连忙陪笑一生,应答下来,快速跑向了厨房后面。
然后王千启收回视线继续说道:“而且那个时候,那位游方术士应该还只是先天境,最多洞虚境界的修行者,布置下的阵法竟然差一点将我都糊弄过去了!你自己想想看,不惜耗费天材地宝,在灵官庙四周布置下来一个极其隐蔽的阵法,你说说,他会眼睁睁的看着几个后生晚辈将他的多年谋划给毁坏一空?”
单西行听完他的话后,微微点头,不置可否。
他冷哼一声:“希望他的战斗实力和他的阵法实力一样,这样我才有全力以赴的快感!”
单西行瞥了一眼坐在自己对面的游虹剑仙,一脸不屑的说道:“我可是听说了,早在十多年前,那个修习魔族秘法的游方术士已经成为了无垢境界的大修行者!现如今十年过去了,不说能不能更上层楼,至少无垢境的实力肯定是巩固结实了,就算你是攻击力卓越超绝的剑修,真的能够在那位魔道游方术士的手中讨得了好?”
游虹剑仙王千启冷笑一声,争锋相对的说道:“我弃武修剑道以来,整整五十载,还从来没有不敢出手的剑!不行你问问我那可恶师尊,当年还不是被我砍了一剑依旧还要屁颠屁颠的厚着脸皮非要收我做徒弟?一个金身境的大佬我都砍过,别说一个小小的无垢境修行者了!对了,老单,话是这么说,到时候可还是老规矩,咱俩到时候一起上,揍死他丫的!”
单西行冷哼一声,嘴角一撇反嘲道:“呦~刚才是谁说的,金身境的老神仙都敢砍上一剑,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要来求我了?”
王千启嘿嘿一笑,滋溜一声喝了一口碗里面泛着绿色小葱花的可口牛肉汤,“你这话说的,怂是肯定不怂的!我一剑下去卵都给他戳爆!可是我那便宜师傅不是不准我动用武道实力么,所以我可也吃不住他的攻击不是,再说了,说到抗揍,中三境之下,那老单你认第一,整个星火郡谁敢说第二?这不是物尽其用么,嘿嘿~~”
“得得得,饭来了,先填饱肚子再说!”
“那啥,这位小哥,早给我们来两斤酸菜炒牛肉!麻溜的啊!”
“得嘞~!王师傅两斤酸菜炒牛肉,麻溜的!!~”小二一边小跑下楼一边有样学样的对着后厨吆喝了一声。
。。。
一路上追风赶月,陈寒安没有丝毫的停留,只是在路过那处污水深坑的时候稍稍停留了片刻,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后,便继续埋头赶路,短短一刻钟多一点的时间,他便已经穿过密林荒山,来到了那处建有灵官庙的山脚下面。
他仰头看了一眼不是很高却很是险峻的这座无名荒山,轻轻吐出来两口浊气之后,一撑手中七尺长棍,整个人借力跃上一处两丈多高的巨石上面,然后脚下不停的一个纵越,再一次跃上了更高处的一颗大树树干之上,对着惊飞的乌鸦群嘿嘿一笑,继续快速向着高处的灵官庙飞跃而去。
等到陈寒安再一次跃上那处平台的时候,发现灵官庙前面的那处空地上已经没有原本铺满一地的乌鸦屎,他不多想什么,快步推开了第一扇大门。然后兴高采烈地快步走了进去:“鬼鸦姐姐,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去消灭那个厉鬼吧!”
这一次没有花费多大的劲力,陈寒安便轻轻地推开了那扇长满诡异青苔的庙门。然后伸手关上房门,再一次重复了一遍:“鬼鸦姐姐,咱们一起去吧那个厉鬼消灭了吧?就今天晚上!”
庙内一身漆黑衣服的鬼鸦依旧和往常一样,长发披肩,背对大门,跪坐在一处破旧蒲团上,尖长的喙口之中在不停地喃喃自语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