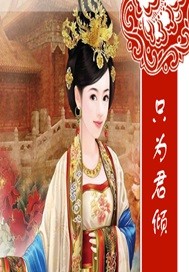再说馆娃宫那边,夷光一曲舞罢后,夫差携着她的手正要入内,一名宫人匆匆而来,神情慌张地道:“启禀大王王后,太王太后病危!”
“你说什么?”夫差大惊,急忙道:“白天大婚行礼之时,祖母不是还好端端地吗,怎么会一下子病危?”
“小人也不清楚,但这是百宁殿传来的消息,应该不会有假。”宫人话音未落,夫差已是疾步离开,夷光连忙跟上去,“臣妾懂得医术,或许能帮上忙。”
“也好。”夫差心乱如麻地点点头。
二人一路紧赶,很快便到了百宁殿,大殿灯火通明,一众太医都在,面若死灰地跪在地上。
看到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太王太后,夫差鼻子一酸,疾步上前,紧紧握住她枯瘦的手,哽咽道:“祖母,孙儿来了!”
听到夫差的声音,太王太后缓缓睁开双眼,浑浊的眼眸里是一如既往对夫差的爱惜,“哀家本想熬过今日,可惜……撑不过去了。”
“不会的,祖母一定会没事的。”夫差急切地说着,朝正握着太王太后另一只手把脉的夷光投去期翼的目光,可惜,等来的是夷光的摇头。
夫差痛声道:“怎么会这么快?明明白天还十分精神。”
夷光拿起掉在地上的瓷瓶,那里本该盛着她给太王太后制做的续命丸,可现在已经空了,“太王太后应该是一口气吃了剩下的续命丸,激发出体内残存的精气,在短时间内看起来精神十足,犹如病愈了一般,可是一旦精气耗尽,便回天乏术。”
太王太后扯出一个虚弱的微笑,“哀家的孙儿大婚,自然不能缺席。”
“祖母……”想来爱护自己二十多年的祖母就要离去,夫差忍不住落下泪来。
太王太后吃力地抚着夫差抽动的肩膀,“莫哭;生老病死,谁都逃不过,能够看到你成亲,哀家已经心满意足了。”
听到这话,夫差越发难过,哽咽道:“孙儿舍不得祖母。”
太王太后怜惜地道:“哀家以后不能再陪着你,你切要小心,不要被小人迷惑,坏了你父亲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说着,她又语重心长地道:“得饶人处且饶人,你要记住啊。”
“孙儿记住了。”夫差用力点头,眼泪不受控制的落下。
太王太后疲惫地点头,道:“哀家想与夷光单独说几句话,你们都退下吧。”
待众人退出大殿后,太王太后望向穿着王后嫁服的夷光,道:“榕儿死了是不是?”
夷光骇然一惊,她与夫差怕太王太后重病之下受不了这个打击,所以伍榕的事情一直牢牢瞒着,不许任何在太王太后面前提前,她又怎么会知道?
太王太后看出夷光心中的疑惑,虚弱地道:“那么多人进进出出,总归有一言半句的泄露。”
夷光无奈地道:“孙媳赶过去的时候,郡主已经悬梁自尽。”说着,她伏身磕头,“孙媳有负祖母托付,请祖母责罚。”
太王太后长叹一声,浑浊着目光混着痛惜与释然,“哀家不知具体情况,但哀家知道,你已经尽力了,起来吧。”待夷光在床边坐下后,她感慨道:“或许这就是榕儿的命,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夷光柔声宽慰道:“下一世,伍姑娘一定会投一个好人家,平平安安,长命百岁。”
“希望如此。”太王太后感叹了一句,又望着夷光道:“你是一个好姑娘,哀家也看得出,差儿是真心喜欢你,但你要记住,君王始终是君王,伴君如伴虎,切勿步了伍员与伍榕的后尘。”
夷光看得出,太王太后是真心把她当成孙媳,为他着想,含泪道:“多谢祖母,孙媳谨记您的教诲。”
“记住就好……”太王太后颔首,下一刻,她突然双目大睁,神情激动地伸向虚空处,喃喃道:“诸樊,诸樊……”
夷光知道这个名字,是夫差的祖父,太王太后的夫君,早在多年前便已经过世了。
太王太后的手伸到一半,颓然落下,一动不动地垂在床沿,从此再没有抬起过……
这一夜,宫人尖细报锐的报丧声传遍了整座王宫,“太王太后薨。”
太王太后过世,最伤心的莫过于夫差,亲自为太王太后守灵,出殡之日,他一路扶灵哀哭;并下令举国同悲,一年内禁止宴乐婚嫁。
夫差每每想起太王太后便哀恸难止,为免睹物思人,在伯嚭的建议下,干脆迁居馆娃宫,朝政也一并搬到了馆娃宫。
夫差这个举动,令文种大喜过望,要知道这馆娃宫是他一手修建的,里面密道重重,恰巧,夫差居住的寝宫就在一条密道,只要他潜入密道之中,就可以探听到夫差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自那以后,文种便日日经由密道来到夫差寝宫之下,窃听朝事,多日下来,真让他听到一件十分要紧的事情。
伯嚭自被夫差冷落后,一直想方设法地希望重夺圣眷,每每见到夫差都是歌功颂德,百般讨好;可惜夫差待他始终淡索索,远不及范蠡。
伯嚭嫉恨之余,想起公孙离曾透过范蠡很有可能就是子皮的事情,当即派人去越国调查,也不知他用了什么法子,竟然果真查到了范蠡底细。
伯嚭大喜,当即将此事奏禀夫差,他满以为这一次能够彻底除掉范蠡,岂料夫差并未恼怒,一来,仅凭伯嚭一面之言,不能确定范蠡就是子皮;二来,范蠡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文武双全,就算当真是子皮,夫差首先想到的,也不是除去他,而是让他真心投靠吴国。
夫差对范蠡的看重,令伯嚭越发不安,几经思索,想出了一条毒计,微笑道:“大王想知道范蠡是不是子皮,又是否真心投靠咱们吴国,臣有一法。”
夫差饶有兴趣地道:“什么法子?”
伯嚭笑着说出两个字来,“伐越!”
夫差一怔,道:“进攻越国?”
“正是。”伯嚭堆着笑容道:“若范蠡心在大王这里,那他一定会助大王彻底消灭越国;反之,他必会百般阻止。”
夫差犹豫道:“这几年伐越败齐,国力折损不少,若是再动干戈,恐怕会影响国本。”
伯嚭连忙道:“我吴国地大人多,区区折损根本不算什么;再加上这几年来大王的英明领导,如今的国力早已经强盛过往昔,乃是春秋一霸,灭掉区区一个越国,根本不在话下。”说着,他又道:“臣愿意领兵出征,为大王开疆拓土,死而后已。”
“此事关系重大,且让本王再想想。”虽然伯嚭吹得天花乱坠,夫差始终心有顾虑。
在他们君臣言语之时,文种就在密道之中,附耳窃听,听到伯嚭这个小人为了对付范蠡怂恿吴王伐越,恼怒不已,不过他怕被夫差听见,不敢说出口,只在心中暗骂。
如此又等了一会儿,确定夫差与伯嚭都离开之后,方才愤愤地怒骂了几句,随即离开了密道。
文种万万想不到,那几句怒骂已是闯下大祸。
夫差离开寝殿后,本想去看望夷光,走了几步想起忘了拿要送给夷光的东西,便又折返,岂料刚一进殿,便听到似乎有人说话,但殿中除了他之外,就只有跟在后面的王慎,他们二人都没有说话,这声音……从何而来?
夫差是一个疑心极重之人,当即命人搜查,虽然并未有结果,但自那以后,他便留起了心。
两日后,他又一次听到了细微的踱步声,这一次,他命禁卫彻查寝殿,一块砖一块砖的检查,在如此细致的搜查之下,果然发现殿中藏有密道,而入口就在他的卧榻之下。
一想到自己每日酣睡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犹如长刀时时悬于颈间,夫差不由得惊出一身汗来。
夫差惊怒之余,却没有声张此事,馆娃宫中风平浪静,犹如什么都没发生过。
翌日,文种与往常一样,经由密道来到夫差卧榻之下,人还没站稳,便被事先埋伏在这里的禁卫一举擒获,押到了夫差面前。
看到文种,夫差哪里还会不明白,文种当年之所以献上家财修建馆娃宫,就是为了今日。
他当即将文种关入地牢之中,并且派人日夜审迅,下了死令,一定要撬开文种的嘴。
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除了王慎与几个亲信,再没人知道,就连夷光也被蒙在鼓中,倒是范蠡传来消息,说文种已经失踪数日,遍寻不见人影。
这日,天气正好,夷光将葯材拿到院中晾晒,突然间,一双手自后向前环住了她的腰,将她吓了一跳,待得看清来者后,方才松了口气,嗔笑道:“大王什么变得这样顽皮?”
“吓到你了?”夫差绕到她身前,温柔地抚着她被太阳晒得有些发红的脸庞。
夷光忍着笑,故意道:“是呢,大王准备怎么赔臣妾?”
夫差故作为难地想了想,笑道:“还好本王今日带了东西来,否则还真让你难倒了。”说着,他朝捧着锦盒的王慎看了一眼,后者会意地走上前,打开锦盒,里面是两个木偶,一男一女,大约只有一个手掌高,却极其精致,眼耳口鼻,手足俱全,就连那衣裳,也是层层叠叠,绣工精巧,所有的一切都与真人一般,只是缩小了数倍。
夷光仔细打量着那两个木偶,发现五官眉眼竟是像极了她与夫差,连那衣裳也与他们大婚时所穿的一般无二,女的长袖飞扬,似在起舞,男的手里则拿着一柄剑,仿佛在伴舞。
夫差淙淙如泉水一般的声音在夷光耳边响起“这是本王让能工巧匠照着你我二人大婚那夜共舞的样子雕刻而成,你可喜欢?”
望着那一对木偶,夷光心底漫出无尽的柔软情意,含笑道:“大王如此用心,臣妾怎么会不喜欢。”
“那就好。”夫差望向夷光的眼眸中满是宠溺之色,“看看他们脚下。”
夷光依言将两个木偶倒转过来,只见男的那个脚底各刻着一个“一”字,女的一只脚底刻着“生世”,另一只脚则刻着“双人”。
“一、一、生世、双人?”夷光喃喃念着这几个看起来完全没有丝毫联系的字词,疑惑地道:“这是什么意思?”
看到夷光疑惑不解的样子,夫差咧嘴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王后素来冰雪聪明,慧质兰心,不妨再想想。“
“大王这是卖起关子来了呢。”夷光娇嗔了一句,又将目光放在那几个字词上,待得组合了几次后,终于让她猜出了其中奥秘,含了一缕恬静的笑意道:“一生一世一双人。”
“正是!”夫差握紧她的手,郑重其事地道:“这一生一世,本王谁都不要,只要你,本王的王后。”
“臣妾……本来就是大王的。”后面那几个字夷光说得轻如蚊呐,却还是被夫差听见,后者顿时心情大好,朗声大笑,倒是将夷光笑得不好意思,满面通红地别过身去,“不理您了!”
“好好好,本王不笑,不笑了。”话虽如此,夫差却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令夷光娇羞不已。
待得这番笑闹过来,夫差道:“知道为何本王的脚上,只有两个一吗?”
“臣妾不知。”
夫差正色道:“两个一,既代表你与我,也代表本王一个人并不完整,只有在遇到你时,本王的人生才会完整圆满!”
夷光感动不已,口中却故意道:“说得可真好听,看来大王平日里没少哄那些个美人贵人,练了一嘴的好情话。”
夫差以为她当真不相信自己,不禁有些着急,“本王发誓,从未对别人说过话。你若不信,可以问王慎,他整日跟在本王身边,最是清楚不过。”
夫差并不是一个擅于说情话的人,且又是一国之君,天下女子趋之若鹜,根本不需要他说情话来说。这世间,也就一个夷光能让他费心思量,处处讨好。
看到夫差认真着急的模样,夷光再也忍不住,“噗嗤”笑了出声,“臣妾与您开玩笑呢,您倒还当真了。”
夫差反应过来,又好气又好笑,屈指弹了一下她光洁的额头,笑斥道:“好你个妮子,连本王也骗,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
夷光抚一抚额头,正要说话,意外瞧见刻在木偶脚下的年月日,那几个字极小,若不细看根本发现不了,落款之日是七日前,也就是说那会儿就已经做好了。
她随口道:“既是五日前做好的,大王怎么今儿个才拿过来?”
“原本七日前就要拿来的,岂料……”话说到一半,夫差突然停了下来,夷光疑惑地道:“岂料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