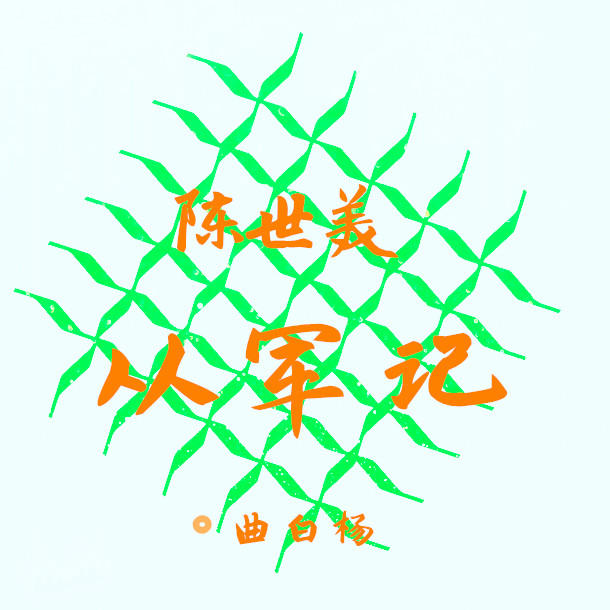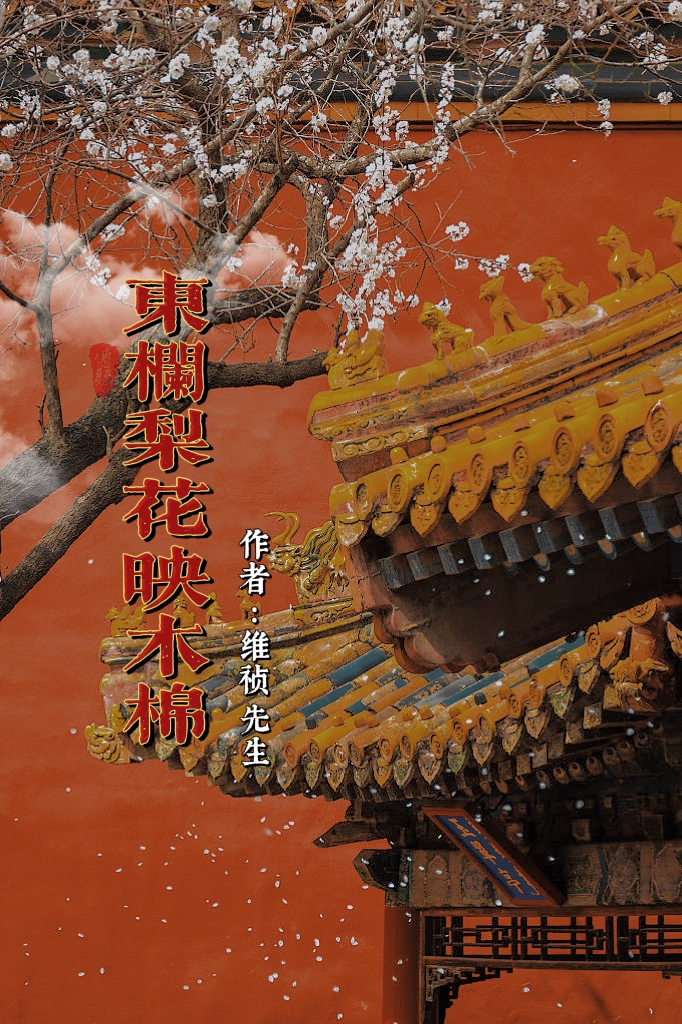范蠡谦虚地道:“公孙将军过誉了,此次能够得胜,乃是大王与全军将士的功劳,范某不敢居功。”
公孙离斜睨着一双醉眼,嗤笑道:“范将军真是会说话,难怪能够青云直上,可惜啊,伍相今日未能前来看一看他昔日的门客是如何一步步爬上来的。”
这句话一出,刚才还热闹的场面顿时冷了下来,谁都知道夫差厌恶伍子胥,偏偏公孙离还往枪口上撞,简直是在自讨死路。
百官悄悄瞅向夫差,果见后者面色阴沉,大有风雨欲来之势,那些个与公孙离不合的官员皆在心中暗笑,等着看好戏。
繁楼也在,瞧见公孙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找范蠡麻烦,眉头微微一皱,想要过去打圆场,哪知刚起身却被伯嚭拦住。
“太宰?”在繁楼惊讶的目光中,伯嚭漫不经心地道:“这是他们之间的恩怨,你跟着去凑什么热闹?坐下,陪我再饮几杯,出征在外,可是好久没饮到如此香醇的美酒了。”
“是。”繁楼不敢拂他的意,只得重新落座,有一搭没一搭的与伯嚭说着话,眼角余光不时瞥向范蠡。
那厢,面对公孙离充满火药味的话,范蠡微微一笑,不卑不亢地道:“伍相的知遇之恩,范蠡没齿难忘。”
范蠡话音未落,公孙离便又接了上来,“是吗?那为何你回京之后,没有去相府拜访?”
“今日才刚回京,匆忙之际实在来不及去相府拜访,公孙兄不也是一样吗?”
公孙离没想到他会将话题转到自己身上,一时无言以对,恼羞成怒地道:“你算什么东西,也敢与我相提并论?”
面对公孙离尖锐刻薄的言语,范蠡并不生气,微笑道:“公孙兄教训的是,范某在伍相门下不过短短一年半载,哪里及得上公孙兄在伍相手下十数载。”
百官听到范蠡的话,皆是暗自发笑,这个公孙离,一门心思想要让范蠡难堪,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要说弃主求荣,谁又及得上他呢。
这十几年来伍子胥悉心栽培,将那会儿只是一个小卒的公孙离一步步扶持至将军之位;结果伍子胥一失势,他就为了前程与富贵,转而投靠了前者的死对头,毫无气节可言,别瞧明面上一个个客客气气,背地里不知多少人在取笑他。
“你!”公孙离气得面红耳赤,全身鲜血直冲大脑,再加上酒醉,竟然挥拳向范蠡打去。
他恼极了范蠡,自是不会留情,拳头带着呼呼风声,这一下要是打实了,骨头非得断了不可。
冬云就在范蠡旁边,看到公孙离借醉欺人,迅速拿起一旁的青花瓷碗扣在公孙离砂钵大的拳头上,生生止住了去势。
公孙离一拳落空,恼怒地道:“哪里来的蛮妇,滚开!”
冬云眼底寒光闪烁,五指用力一收,那只本就因为承受了太多力量而裂纹横生的瓷碗当即破裂,无数锋利的碎瓷片在冬云的用力下,生生嵌入公孙离还来不及收回的拳头中。
“啊!”公孙离哀嚎一声,赶紧收回满是鲜血的拳头,只见上面嵌着大大小小十数枚碎瓷片,有几枚几乎整个没入皮肉之中。
冬云伤得比他一样严重,鲜血不断从掌心滴落,她却如没事人一般,直挺挺地站着,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疯妇!”公孙离接连吃亏,气得几乎要抓狂,正想教训冬云,耳中传来夫差阴寒的喝声,“住手!”
刚才的事情,令公孙离酒醒了一大半,不敢违背夫差的命令,悻悻地收回了收,但依旧心存不甘,朝夫差道:“这名女子在大王面前行凶,胆大包天,定要严惩!”
在他说话的时候,夷光已是来到冬云身边,见到她满手是血,心疼地道:“姐姐怎么这样不小心?”
冬云满不在乎地道:“我没事。”
“都伤成这样了,还说没事。”夷光嗔怪了一句,对阿诺道:“去把我葯箱拿过来。”
趁着阿诺去拿葯箱的功夫,夷光小心翼翼地将扎进冬云手掌中的碎瓷片取出,有几片扎得太深,费了好大劲才取出来。
公孙离等了半天都不见有人理他,又见别人暗自发笑,顿觉颜面无光,当即伸出另一只手往冬云抓来。
夷光面色一冷,脚步一动,挡在冬云面前,与此同时,抬手抚过发髻,那枝鎏金掐丝镶珍珠发髻已是握在手中,没等众人看清,已是刺入公孙离手腕穴道之中。
说来也奇怪,她这一下刺得并不重,顶多不过是皮肉之伤,却一下子令公孙离胳膊没了力气,软绵绵地垂了下来,任公孙离如何使颈,都动不得分毫,犹如断了一般。
公孙离骇然失色,这可比刚才冬云那一下更可怕,望向夷光的眼神充满了惊惧,“你对我做了什么?”
夷光拭去簪上的鲜血,淡然道:“没什么,不过是封了你的手三里穴道,省得你在这里行凶伤人!”
公孙离不服气地道:“是她先伤得我!”
“若不是你意图伤害范先生,冬云怎么会伤你?!”
公孙离冷哼道:“范蠡背主求荣在先,恶言中伤我在后,受我一拳已是便宜了他。”
“放肆!”夷光黛眉紧蹙,喝斥道:“范蠡何时背弃过大王,还是说……在你公孙将军眼里,伍相才是吴国的主人?!”
听到这话,公孙离冷汗顿时下来了,他一时逞痛快,却犯下了大忌,尤其还是当着夫差的面。果不其然,夫差脸色铁青欲迸,犹如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
公孙离双腿一软,跪在地上战战兢兢地道:“末将并非这个意思,大王切莫听这来历不明的越女胡言,她分明……分明是蓄意挑拨末将与大王,也不知存了什么歹毒心思。”他今日才回京,还不知道夷光即将被册立为王后的事情,一个劲的将脏水往夷光身上泼。
夫差冷冷看着他,那目光就像在看一个死人,巨大的威压与恐惧令公孙离汗如浆涌,彻底没了醉意,嘴唇哆嗦着想要说话,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公孙。”夫差突然出声,后者急忙磕头,颤声道:“末将在。”
“依你所见,这个越女该如何处置?”夫差木然问着。
公孙离一怔,旋即心中一松,看来大王也瞧出这越女居心叵测,赶紧道:“回大王的话,既然知道此女心思不善,有惑主离间之隒,便不能姑息,当与冬云一般,严惩不怠。”他思索片刻,又道:“末将以为,可以拖下去杖责三十,然后贬去采石场,任其自生自灭。
依着公孙离的心思,自然是直接杀了二人更为解恨,但他怕被夫差觉得自己过于残忍,所以“仁慈”的暂留她们一条性命。
采石场劳作繁重,一般壮实的男子都吃不消,何况是两个女子,只要进去了,不出几日就会生生累死。
“好!好!”夫差一边拍手一边道好,薄唇绽出一缕笑意,仿佛真的十分认同。
这样的笑容与言语,令公孙离心中大定,高呼“大王英明”。
“来人!”夫差唤过两名守卫,凉声道:“刚才的话你们都听清楚了,把他带下去吧。”随这话,夫差抬手一指,所指之人,正是公孙离。
面对指向自己的手指,公孙离愣了一下,赔笑道:“大王指错了呢,不是末将。”
“本王指的就是你!”夫差斜坐在王座中,以手支颐,唇边笑意依旧。
见夫差不似玩笑,公孙离心脏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强笑道:“怎么会是末将呢?”
“本王已经下旨册立夷光为王后,下月完婚,你对她不敬就是对本王不敬,你说说,该不该受罚?”
听到这话,公孙离如遭雷击,整个人僵在了那里,他……他刚才听到了什么,夷光是未来的王后?这怎么可能?
假的,一定是假的!
公孙离抬头朝众人看去,试探在他们脸上找到一丝置疑或者诧异,可他失望了,那些人脸上无一例外皆是嘲讽讥诮的笑容,也就是说……这件事是真的,而他们早就知道了,却一直不曾出言阻止,都在等着看戏,就连伯嚭……也是一样。
原来,伯嚭从来没有想过招揽他,之前在军营里的那番话,不过是为了诓骗他卖命,真是个奸诈小人!
也就是说……现在没有人会帮他。
想到这里,公孙离身子剧烈地颤抖了起来,犹如在秋风中瑟瑟发抖的枯叶,恨不得打自己一巴掌。
待得回过神来,公孙离朝夫差磕头如捣蒜,可无论他怎么哀求,夫差都置之不理。
公孙离不死心,又朝正在替冬云包扎伤口的夷光磕头哀求,“姑娘一向慈悲为怀,求姑娘帮末将向大王说说,饶末将一条性命,末将一定铭记姑娘恩德,日日上香为姑娘祷告。”
冬云鄙夷地道:“刚才不是骂得挺痛快吗,怎么一转眼又像条狗一样摇尾乞怜,真是没骨气。”
公孙离被她斥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要换了平日绝不会善罢干休,可现在指着夷光求救,只能生生咽下这口气,哀声道:“冬云姑娘说得对,我就是一条狗,二位没必要跟一条狗生气!”说着,他又朝夷光苦苦哀求,“姑娘您大慈大悲,就当……”他眼珠子飞快地转着,恬不知耻地道:“就当末将是一条狗,把末将放了吧。”
对于公孙离来说,再没什么比保住性命更重要的了,只有留着性命,他才有机会对付眼前这几个人,范蠡、夷光、冬云甚至伯嚭,他一个都不会放过!
公孙离自以为将很好的掩饰住了仇恨,殊不知皆被夷光瞧在眼中,她神色平静地道:“若你只是得罪了我,并没有什么,正如你所言,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越女,生死都无关紧要,何况是几句辱骂的话。可你不该对大王全无敬畏之心,更不该觉得吴国能有今日,全是伍子胥的功劳;看到范先生为大王征战沙场,便心怀不忿,出言讽刺,甚至还当着大王的面动手打人。”说到后面,夷光语气渐重,斥得公孙离面若死灰,“我问你,你将大王置于何地?”
公孙离急切地道:“大王在末将心中英明神武,犹如神明一般,从不敢有半点不敬不诚不畏。”
冬云冷冷吐出四个字,“口是心非!”
夫差长眉轻扬,长方形的眼睛光华流转,似笑非笑地道:“本王现在改变主意了。”
就在公孙离以为自己能够捡回一条性命的时候,冰冷濯然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公孙离对本王与王后不敬,罪不可恕,即刻推出去斩首!”
公孙离骇然,大声喊冤,见夫差不为所动,他又手脚并用地爬到夫差宝座下,急切地道:“这些年来,末将一直对大王忠心耿耿;还有艾陵之战,末将曾立下功劳,刚刚凯旋归来,大王就杀害功臣,一定会有损大王名声!”
夫差咧嘴一笑,露出森冷雪白的牙齿,他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公孙离,一字一字道:“艾陵之战,你葬送了多少将士的性命,自己心中有数;至于功劳……呵呵,那更是可笑,你自以为烧了齐军的粮草,结果呢,根本就是对方的圈套,若是范蠡及时归来,你这会儿还有命站在这里高谈阔论吗?本王还没问你的罪,你倒是恶人先告状,对范蠡横加指责,只凭这一点,你就死的不冤!”
“可是……”公孙离还想为自己辩解,夫差忽地道:“你认为本王像以往那一位君主?”
公孙离精神一振,赶紧搜肠刮肚地想了起来,倒是真让他想起一位史书中赫赫有名的君主,赶紧道:“大王自是像那齐桓公。”
“何以见得?”
“大王虚怀若谷,任用贤能,尊善者为师,事必躬亲,可不就与那齐恒公一模一样嘛。”说着,公孙离又讨好地道:“相信不出数载,大王便能像齐恒公那样,成为一代霸主。”
“看不出你还如此能说会道,不错。”夫差笑了一笑,转而道:“那你再瞧瞧,满朝文武之中,谁是本王的‘管卿’?”
夫差口中的“管卿”正是齐恒公在位时的臣子管仲,后者为相后,辅佐齐恒公推行改革,实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令齐国逐渐强盛,成为天下诸候的霸主。
“当然是……”公孙离目光飞快在百官面上扫过,最终停留在一个他痛恨的人脸上,“太宰大人。”
早在听到夫差问及比拟“管仲”之人时,伯嚭便觉得非自己莫属,此刻听到公孙离这个回答,更是暗自得意。是啊,伍子胥已经失势,满朝文武还有谁比他更似管仲。
“错了。”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夫差起身走到范蠡面前,亲切地挽起他的手,“少伯才是本王的管卿!”
此言一出,伯嚭脸色顿时涨得犹如猪肝一般,大王莫不是得了失心疯,竟将范蠡比作管仲,那他呢,他又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