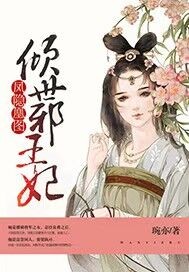那厢,范蠡有些内急,向伍子胥说了一声,来到楼下,他唤过一名宫人,在他耳边低低说一句,随后又悄悄往其手里塞了一些钱,待宫禽去后,方才去净房。
宫人走出没多远,便被人捂住嘴巴,那人将他拉到一个无人的地方方才松开,但不许他回头,“刚才那人让你去做什么?”
宫人战战兢兢地答道:“他……他让我去煮一碗醒酒汤。”
“满口胡言!”那人显然不相信他的话,喝斥道:“快说实话,否则当心你的小命。”
宫人吓得浑身发抖,哭丧着脸道:“他真的是让小人去煮醒酒汤,还给了小人几个钱。”他一边说一边哆哆嗦嗦地把那几个铜钱拿了出来。
“难道真是这样?”那人自言自语了一句,随即威胁道:“我问你话的事情不许和任何人说,否则一定取你小命;至于那醒酒汤,你就照常煎给他,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走吧!”
宫人连连点头,赶紧撒腿离去,在他走后,那人亦悄然离去,他没有发现,范蠡正站在不远处的一个阴暗角落里,面色难看到了极点。
他借故离席,确是想传递消息,但先前伍子胥锐利到近乎尖刻的目光,让他多留了个心眼,他故意放出这么一个烟幕,果然出事了,要是他刚才让宫人去传递的是夷光的消息,那自己是越国卧底的事情,就彻底暴露了,文种还有冬云他们,全部都会跟着遭难。
想到这里,范蠡一阵后怕,虽然这个危机避过了,但夷光的下落却成了一个謎。
伍子胥既然对自己起疑,那个所谓关押夷光的地方,必然也是假的,用来引自己上钩的诱饵。
范蠡恨不能立刻离去,寻找夷光下落,但他知道,自己一步也不能离开,不仅如此,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否则必将招来弥天大祸。
希望……文种他们能够找到夷光,将她平安救出。
范蠡定一定心神,回到观鱼楼上,伍子胥已经得到了消息,看向范蠡的目光中多了几分复杂。
过了一会儿,宫人送来醒酒汤,范蠡接过后递给伍子胥,关切地道:“大人喝了不少酒,快喝碗醒酒汤吧,不然酒劲上来,容易头疼难受。”
“少伯有心了。”伍子胥深深看了他一眼,接过了醒酒汤。
再说夷光,她被人打晕后从马车中带走,等她幽幽醒来时,发现自己被绑在一根柱子上,动弹不得,眼睛也被蒙住了,黑漆漆一片,什么都看不清。
“醒了?”一个陌生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夷光“盯”着声音传来的方向,“你们是伍相的人?”
罗延一怔,没想到夷光竟然一语道破他们的来历,朝一旁的公孙离瞧去,后者在纸上写了几个字――“莫回 速问”。
罗延会意,道:“我问你,你与文种还有范蠡,是何关系?”
“我逃难来到姑苏,幸得文先生收留于府中,至于范蠡,我只知他是文先生的好友,余下的并不知晓。”
罗延冷笑道:“倒是口舌伶俐,看来不用刑,你是不会招得了。”他从炭盆取出烧红的铁烙子,在夷光面前一晃,啧啧道:“这么好的皮肉若是毁了,实在有些可惜。”
夷光虽然看不见,却能感受到那种令人战栗的炙热,冷声道:“太宰大人此刻必定在四处搜寻于我,相信很快就能搜到这里,到时候,你与你身边那个人,都逃不了!”
公孙离二人皆是为之一惊,没想到夷光竟能够察觉到屋中有两个人,想必是刚才听到纸笔摩挲的声音,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女子观察力好生利害。
罗延定一定神,喝斥道:“少废话,不想受皮肉之苦的话,赶紧说实话,你与范蠡等人,可是从越国来的奸细,想要迷惑大王,祸乱吴国江山?”
夷光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道:“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你问的这些,实在是不知。”
“看来你是非要吃罚酒了!”罗延冷哼一声,又将铁烙子凑近了几分,夷光几乎能闻到头发烧焦的气味,身子微微发抖,但始终没再说话。
望着那张精致无双的脸颊,罗延实在有些不忍下手,向公孙离投去询问的目光,后者略一思索,写道――前夜繁楼之事。
罗延会意,将铁烙子放回到炭盆中,道:“前夜,繁楼怎么会在文府,可是有人通风报信?”
夷光唇角微扬,“看向”公孙离的方向,“公孙将军有什么话,直接问就是了,何必假人之口。”
罗延骇然,脱口而出,“你怎么知道是公孙将军?”
公孙离狠狠瞪了他一眼,但为时已晚,夷光微笑道:“我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还真是公孙将军。”
“你耍我?”罗延气得发怔,从开始到现在,他们明明占尽了上风,可不知怎么的,竟一直被这个女子牵着鼻子走,实在可恼!
公孙离示意他退下,又解开蒙住夷光双眼的黑布,微笑道:“姑娘真是擅于揣测人心,公孙佩服。”
夷光冷冷盯着公孙离,就是眼前这个人,为一己私欲,杀死了她的父亲,此恨此仇,她一定要亲手讨还。
公孙离被她盯得诧异,道:“姑娘为何这样看着本将军?”
夷光压下心底的恨意,嗤笑道:“久闻公孙将军骁勇善战,立下无数战功,想不到竟然做出掳人威逼之事,真是久闻不如见面。”
“让姑娘失望,公孙惭愧,不过姑娘还是先担心一下自己的处境吧,口舌再利,也抵不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公孙离抚着那张美若谪仙的脸庞,在夷光耳畔徐徐道:“只要你说出实话,我不仅保你周全,还会许你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姑娘是聪明人,当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说过,我逃难来此,余下的并不知道。”夷光的一再否认,惹怒了公孙离,目光一冷,用力捏住夷光脸颊,寒声道:“你若再不识相,休怪我不客气了!”
夷光抿唇不语,公孙离冷哼一声,取来一旁的皮鞭,狠狠抽在夷光身上,立刻出现一道血痕。
“说不说?”任公孙离怎么逼问,夷光始终是那句话,令前者气得发狂,面目狰狞地盯着满身是伤的夷光,咬牙道:“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再不说实话,就杀了你!”
面对他的话,夷光冷笑连连,她这个态度,更加触怒了公孙离,“你以为我不敢吗?”
这一次,夷光终于开口了,“你要杀我,自是易如反掌,可是我死了,将军也得赔葬!”
公孙离对她的话嗤之以鼻,“疯言疯语。”
“满朝上下,最不想我入宫的就是伍相国,这一点,你我知道,太宰大人更是清楚;你杀了我,就等于彻底得罪了他,太宰此人,最是记仇,听说十几年前的一点小仇,都记得一清二楚,何况是此等深仇。”
“伍相国位高权重,太宰大人或许无可奈何,可你……呵呵,还不至于让太宰大人束手无策。”
夷光这席话令公孙离冷汗涔涔,色厉内茬地道:“你不必在这里危言耸听,不过是一个靠阿谀奉承爬上高位的小人罢了,本将军才不会怕他。”
夷光从他眼里看到了不安与惶恐,嘴角浮起一个幽凉的冷笑,“那就祝将军好运了。”
“将军,现在怎么办?”面对罗延的询问,公孙离面色阴晴不定,正自犹豫时,门外突然传来兵器交夹的声音。
罗延也听到了,赶紧开了一丝门缝,待看清外面的情况下,他骇然道:“不好,是繁楼。”
“他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公孙离大惊失色,在确定外面是繁楼后,他与罗延赶紧蒙住脸颊,虽然大家心知肚明,但这猜测和看到还是不一样的。
几乎是在同一时刻,门被人用力踹开,冬云率先冲了进来,看到满身是伤的夷光,眉目一片冰冷,当即朝公孙离二人冲来。
此时,门外守卫已是节节败退,输――是早晚的事情。
看到这一幕,公孙离知道此处非久之地,一边与冬云缠斗,一边往门外挪去,不过在此之前,得先解决一件事。
趁着罗延拖住冬云的功夫,他朝夷光抬起手,一个黑黝黝的小箭匣出现在掌中,就在按下机关的时候,他想起夷光刚才的话,手微微一颤,原本对准夷光喉咙的短小箭矢因此失了准门,最终擦着夷光颈边掠过,钉入后面的木桩之中,几缕断发自半空中缓缓飘落。
看到这一幕,冬云出了一身冷汗,亏得是失了准头,否则……她不知要怎么向范蠡交待。
“贼子该死!”待得缓过神来看,冬云眼中腾起森森杀意,一把薄剑如灵蛇一般朝公孙离缠去,剑剑指向要害。
她剑术高明,连繁楼都吃了大亏,公孙离自然也讨不得好,几招下来,手臂上已是挨了一剑,鲜血直流。
“走!”公孙离知道此处不是久留之地,赶紧带着罗延往外退去,冬云本欲追去,被繁楼拦住,“救施姑娘要紧,而且外面人杂,万一被瞧见,容易招来祸患。”
“算他走运。”冬云恨恨瞪了一眼逃窜的公孙离等人,转身入内,将夷光将柱中解了下来,一失了倚靠,后者立刻软软倒在地上。
繁楼扶住她,关切地道:“怎么样了,要紧吗?”
“皮肉伤罢了,死不了。”说着,她感激地道:“幸好冬云姐姐及时赶来,多谢。”
“该多谢的是你自己,要不是你有先见之明,让我暗中跟随,怕是谁也找不到这里。”今朝出门时,虽然有剡季领一众兵丁护行,但夷光还是有些不放心,便让冬云悄悄跟随,如此才能发现公孙离趁着马车被堵在路口的功夫,暗中劫走了夷光。
冬云发现的时候,夷光已经在他们手里,怕他们狗急跳墙,杀了夷光,所以不敢声张,只一路尾随,确定他们关押夷光的地方后,方才去搬救兵,结果途中遇到了繁楼。
这确实是一间废弃的宅子,但并不是伯嚭的,而是一名已经过世的朝臣,就算被找到,也扯不到伍子胥头上。
夷光就着冬云的搀扶,艰难站起身,对繁楼道:“快带我去观鱼大会,否则要来不及了。”
繁楼为难地道:“可是你这伤……”
“我撑得住,快!”见夷光艰难,繁楼只得答应,解开披风覆在夷光身上,策马往观鱼大会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