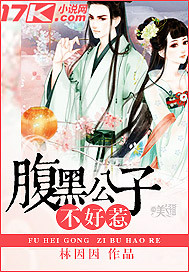阿四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天赐就像霜打的茄子,蔫了。
这大出乡亲们的意外,所有人的好奇心一下子被勾引,目光全集中天赐身上,天赐浑身刺扎似的难受。
昨晚洞房那一幕,他至今想起来百爪挠心似的难受。
当他兴高采烈、迫不及待地揭开小五头盖时,小五用手遮住脸,死活不肯挪开双手。他只当她害羞,没有强迫她,虽然他想立睹小五的真容。
媒婆作媒时,送来过小五的画像。画中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螓首蛾眉,美目顾盼!天赐一瞧之下,眼珠子就落到画像上,舍不得眨一下眼。当场魂儿就被勾去了一半,他想都没想就同意了这门亲事。
心旗摇曳中,小五柔声道:“官人,你听,有人来闹洞房了。”
天赐侧过脸竖起耳朵,小五趁其不备,一口吹灭了红烛,“嘤咛”一声,衣不解带,钻进了被窝。
新房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只听到小五呼吸急迫,吹气如兰。天赐嗓子眼冒火,血脉偾涨。说时迟,那时快,天赐一个饿狼扑食,扑向小五......
尘埃落地,小五背朝着天赐,很快睡去了。极度满足、大汗淋漓的他悄悄下了床,重新点起红烛,烛光映红了幔账,也映红了熟睡中的小五。
天赐听到小五呼吸均匀,慢慢地翻转小五的身子,他的笑容突然冻结。
烛光下,小五额角前突,双眼吞凹,目小如缝,鼻孔翘天,说不出的丑陋。天赐傻了眼:我刚才是和夜叉睡觉吗?
媒婆送来的画像还装在衣兜里,他无时不刻不揣着这幅画绢。
天赐颤颤威威取出画绢,对照床上的小五。画中人的体态、肤色和小五无疑,只是脸孔被无限美化了。
天赐一张脸比哭还难看,他叩心自问:“今后我要天天面对着这张丑脸吗?”
红烛高照,小五越发显得粗陋,天赐冲出新房,大口呕吐,连胃里的胆汁也吐出来了。
吐了半天,天赐悻悻然转回新房,看到小五睡得香甜,一种被欺骗的感觉闪电般袭击全身。
他怒火中烧,痛下决心,取了笔砚,当场修了一封休书。
“怪只怪你娘家人拿画骗我。”他扔掉笔砚,愤愤不平地步出新房。
鸡叫二遍,天赐深一脚浅一脚走进新房,休书还在,小五不见踪影。他黯然神伤,有一种莫明的负罪感。
“你们圆了房吗?”当他拿着休书找叔父时,叔父一双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
天赐声如蚊呐:“圆了。”
“啧啧啧。”叔父急得如热窝上的蚂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拜了天地,圆了房,夫妻俩就该恩恩爱爱过日子,报答天地养育之恩。你到好,拿婚姻当儿戏,洞房之夜,睡了人家姑娘,一封休书便把她休了,简直岂有此理。”
天赐争辩:“是她欺骗侄儿在先。”
“即便如此,你不该......不该先下手啊。于情于理,你得保人家姑娘清白,再休她理直气壮。”叔父气得发抖。
天赐自知理屈,一脸惶恐,张口结舌道:“哪......如何是好?叔父......帮侄儿拿主意。”
叔父忧心忡忡:“传出去只怕被左邻右舍笑死。”
他一看到天赐手上的休书,一拍大腿,“有了!”
天赐小声问:“您老有了高招。”
叔父面露喜色:“就怕小五找她俩堂兄弟撑腰。五更为叔去田渠看水,瞧见阿三阿四正在牧马。”
天赐兴奋地道:“这么说小五不知阿三阿四来到村里,自个儿回了娘家。”
叔父目现狡诈之色:“小五没拿休书,这就好办了。一不做二不休,一口咬定他们拐跑了你家娘子,把这盆脏水泼在阿三阿四身上。”
天赐心有顾虑:“阿三阿四会武功,把他俩惹毛了,只怕侄儿没好果子吃。”
叔父稳操胜券:“这个大可放心,如果阿三阿四动武,倒把这个脏栽实了。”
天赐开心之极:“如此甚好。叔父你看着办吧。”
叔父当机立断:“事不宜迟,我动员乡人先把他俩绑了再说。”
果然不出料,当村民将阿三阿四团团围住时,阿三阿四没有反抗,被村民推逐至天赐家门前,绑在马柱上。
“你做过什么,心里没数吗?” 眼下,阿四的一句话击中了天赐的软肋,天赐一时语塞。
叔父面色一青,暗叫不好。小五显然找过阿三阿四,原来她已得知兄弟俩来到了村子上。
好在休书还在天赐手中,不至于无药可救。想到这,叔父替侄儿回答:“听你话中之意,天赐媳妇下半夜跑出去和你们约会,恬不知耻地说了她和天赐的云雨之事?”
叔父先声夺人。
阿三见他撕破脸,一心想把事情已闹大,当场火冒三丈:“呸!你们占了便易还卖乖,真替小五不值。”
天赐脸一红,低下头。叔父一跺脚,天赐重新抬起头,控诉道:“媒婆不该拿画中人骗我。”
俩人针锋相对,一个说对方占了便易还卖乖,一个说媒婆拿画中人骗他,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村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到底谁占了谁的便易,到底谁吃了谁的亏?
阿三气呼呼地:“小五怎么了?比画中人差哪儿?”
天赐“哼”地一声:“那是天地之别。一个美艳不可方物,一个奇丑无比。”
“你敢说小五奇丑无比?”阿四怒吼,仿佛晴空一记霹雳,村民的耳膜震得嗡嗡作响。
打兄弟俩骂兄弟俩可以,说小五坏话就是不行。
阿四瞋目切齿,形同恶煞,天赐吓得胆颤心惊。
崔护命村长放开阿三阿四。众目睽睽下,阿三阿四跑不到哪里去。
村长派了二个村民给阿三阿四松绑。天赐叔父见村长出面,心里虽然气得不行,却不好意思动手阻止。
村长息事宁人:“这俩位兄弟,如确知天赐媳妇藏身之处,不妨告诉天赐吧。小俩口有什么瓜葛,坦诚相待,把话说开,何愁不解。”
阿三目如卧弓,恨不得一箭穿透天赐的胸膛。他气愤填膺地对村长道:“是这厮本人逼走了他娘子。”
此言一出,乡人皆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