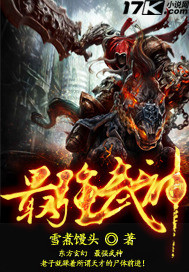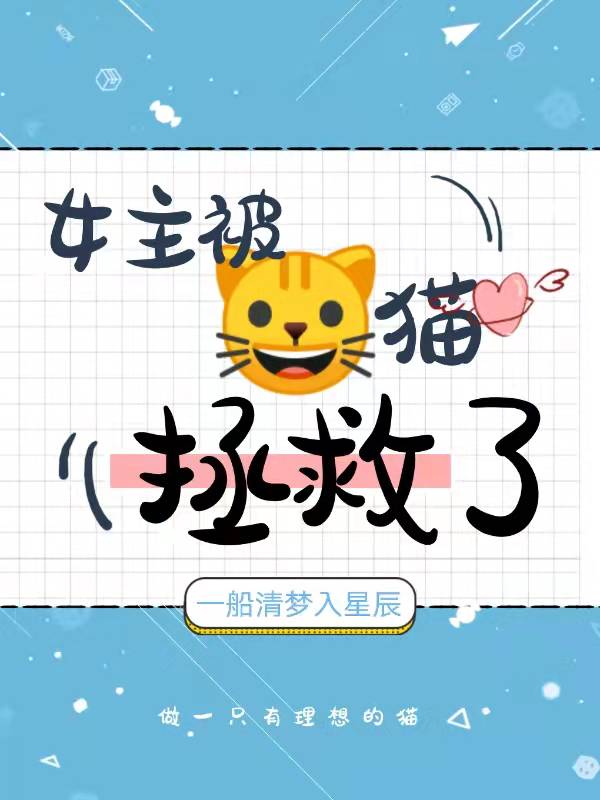“大护法有所不知:诺那佛祖金身大损,此次下界,乃是灵元转世,非隐遁入世,因此不能与大护法同行。”此时,牟尼佛祖接过话头,淡然解释道,“我已经开始为诺那佛祖起造浮屠塔,不几日即将安置他的金身。”
原来这灵元转世便如投胎重生,和世人一样要经历生老病死等种种痛苦的成长过程,然后依靠行善积德,宣化众生,才能证回金身。这实是修仙成佛最为艰难的道路,自古以来,能够以此证道者,少之又少。
玄女却未料到会有此着,不禁神色一变,怔在那里。
诺那佛祖见状,忙道:“老朽此去,少则二三十年,多则七八十载,不知归期,而大护法又有重任在身,老朽实在不敢拖累大护法啊。大护法的好意,老朽心领了。如果与大护法有缘,他日必会有相见的一天,还望大护法一路保重。”
诺那佛祖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他的意思不言自明,玄女也无可奈何,不便多说话了。
于是,玄女道:“既然佛祖心意已决,玄女也就无话好说了。请佛祖多加保重。如果红尘有缘相见,玄女定当前去护法。”
玄女说完,便向两位佛祖行礼辞别。
两位佛祖回了礼,送出大雷音寺。
玄女驾七彩祥云,朝东飞行,应劫下界去了。
******
诺那佛祖金身大损,准备借灵元前往东土修回菩提,证回金身,牟尼佛祖不便多劝,于是就在灵山玉笔锋起造一座浮屠塔,供奉诺那佛祖的金身。
不一日,浮屠塔建造竣工。
但见塔高九层,檐分六角,下建莲花台,上封葫芦顶。
并且九层六角共悬挂五十四盏琉璃灯,一盏寓示一份功德,等五十四盏琉璃灯全亮之时,便是诺那佛祖功德圆满,证回金身之日。
即日,诺那佛祖沐浴了金身,膜拜了十方诸佛,身披锦襕袈裟,结趺而坐,被众罗汉抬进浮屠塔内,封存了金身。
牟尼佛祖又唤来阿难尊者,命他奉诺那佛祖的灵元前往东土。
阿难尊者领佛旨,双手捧着诺那佛祖的灵元,一路僧衣飘飘,直出离了灵山。
行够多时,已近东土。
正行处,忽见东边一团黄光悠悠而来,阿难尊者知是有神仙打此路过,就放慢了脚程,刻意回避。
殊不料那团黄光倏然之间滚至近前,云头上现出一位道人,四十余岁,身板结实,豹子头,络腮须,背后背一根水磨钢鞭,黄光之中隐伏黑气。
“我当是何人路过此处,原来是阿难尊者,幸会幸会。在下昊天瘟部副使费结稽首了。”那道人居然认识阿难尊者。
“哦……原来是费天君!幸会,幸会……”阿难尊者合什回礼,其实他并不认识费天君,但知此神绝非善辈。
“不知尊者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啊?”费天君紧问一句。
“贫僧自来处来,到去处去。”阿难尊者有意敷衍。
“哈哈哈哈……”费天君一听此话,朗然大笑,然后道,“我听说佛家都是些无上士、天人师、调御丈夫,尊者你也是多闻第一高人,今日一见,却不料都是些插科打诨之辈!”
“天君怎么这般说话?”阿难尊者遭了挤兑,十分不悦。
“佛门由来倍受推崇,今日遇见尊者,关切一声也不失两家礼数。佛祖曾说‘出家人不打诳语’,你是佛祖身边的尊长,却拿这话来诳我,岂不是有失了佛祖的教诲?”
此话一出,阿难尊者的脸色刹时黑一阵白一阵,青一阵红一阵,毕竟他是忠厚善良的长者,并且被费天君以正理欺住,正所谓“君子欺之以正”。
因此阿难尊者满面羞愧道:“天君责备的是,请天君宥恕。此次前来,正是要送诺那佛祖的灵元去那东土历炼,修回金身。”
“哦……原来如此。”费天君明白话来,稽首道,“打扰尊者了,贫道就此告辞。”
费天君略一稽首,行过辞礼,扬长而去。
二人寥寥数语,错肩而过。
阿难尊者也并未把此事放在心上,催云脚,径奔东土而来。行够多时,业已来到了万丈红尘的东土上空。
来回观察了许久,阿难尊者发觉东南之地善气缤纷,颇是个证道的佳处,就把诺那佛祖的灵元照下界抛去,实则那下界正是东土江南之地。
但见那灵元转了几匝,闪一道金光就没入了万丈红尘之中。
阿难尊者看护了许久,见无异样,方才返回灵山交旨去了。
******
阿难尊者情急之下的一句歉语,不料竟让那费天君探知了诺那佛祖灵元转世的玄机!
细说起来,这也是东土大劫来临,气数尽变,神魔纷纷出来作乱。
但这费天君究竟又是何许人物呢?
实际上他不过是昊天瘟部里的一个行瘟充役副使,名不见经传,也不在神籍编制之中。
这充役副使说白了,就是瘟部聘来的差役,替五方行瘟正使跑腿打杂,干些苦活累活而已。
可是这费天君历劫精修,法力激增,道行早已在五部正神之上,因此久居副职,心中常有不平之气。
那日,罍山坍塌,煞灵逃逸,各部众神也都看见了,都似把持不住一般,蠢蠢欲动,是以瘟部大帝吕岳勒令众神关门闭户,各守玄关,防止为煞灵所诱,走火入魔,原来这瘟部众神出自截教门下,皆非人身,最容易遭受诱惑。
等出得关来,费天君恰巧与南方行瘟正使李奇李天君相遇,于是二神一时聊起山海大动之事,渐渐就聊到了“道心魔趣”之别,各抒己见。
最后,李天君辩不过费天君,就讥笑道:“任你道法说得精妙,终是无法享受我等正职之禄。”
费天君闻说,不悦道:“我勤修苦炼,自然会有天道酬勤之日。”
李天君不以为然,复嘲笑道:“如果你都能修得正禄,那么我等岂不是修得天师天王了?哈哈哈哈……”
嘲罢,李天君仰天大笑,拂袖而去。
费天君只当与李天君推心置腹,聊表胸襟,却未料到遭他小觑挖苦,生生气得嘴角抽搐,面色青紫。
夜间,邀请和瘟使李平小饮,叙说郁闷,就把那酴醿酒兀自饮过了头,嫌弃侍童添酒不勤,醉打了他一顿。
那侍童受了伤,抱头鼠窜,恰与李天君撞了个满怀。李天君问了原因,便来抱打不平,大骂费天君狂妄。
费天君早就愤怒,就仗着酒疯要教训李天君。和瘟使李平劝解不开,二神就大打出手。
另外三位行瘟正使闻声赶来,都怨怼费天君不过一编外副使,却如此目无尊卑,欧斗正使,便齐上阵来相助杨天君。
费天君一时酒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施展出本事,将四位正使打得鼻青脸肿,负痛哀叫,却都不是费天君的敌手。
这一闹,就惊动了瘟部大帝吕岳,就前来训斥费天君。
费天君醉意正酣,三言两语不和,又与大帝争执起来,一个不留神,竟然把大帝推翻在地,崴伤了脚,颜面扫地。
众正使大惊失色,急忙一边扶起大帝,一边大骂费天君。
就把费天君的酒给骂醒来,他顿时浑身冷汗飕飕直冒,仆地磕头认罪。
吕岳跌坐在地上,哈哈大笑,好不夸赞了费天君一番,然后叫众正使扶他而去。
费天君自以为宽恕了他,羞愧难当,深为感激。
不料此事后,费天君再不录用行走,虽不奉茶侍酒,却已与仆童无异,才知大帝衔恨于心。诸使更是疏远他,不与交集。
费天君思之极恨,暗道:我三千年的辛勤苦劳不放在眼里,一场醉酒失态却牢记在心头;有朝一日,若能扬眉,定血今日之耻。
自此,费天君把那通天的怨恨都埋在心底,云游于天地之间,准备另寻他处立身,但都事与愿违。
这日里却巧,费天君正游于西天,忽遇见阿难尊者,无意之间得知了这等玄机,起初他也并未在意,但行过数十里后,猛然醍醐灌顶,恶向胆边生来。
他暗暗道:听说佛之灵元乃是舍利子所结,吃了它可助大大功法,这诺那佛祖的灵元可是有无量之功啊!我如今漂泊无依,恰似那无归的末落子,无故却得此玄机,这岂不是天意眷顾?我何不趁这煞灵乱界之时,冒一番天险,证我殊仪?若能成功,立名三界,莫说吕岳李奇那几个贼厮,便是整个南天宫里的神仙,谁还再敢小觑于我!
费天君怨恨蒙心,魔性炽起,便就掉转身来,匆匆赶到了万丈红尘上空,却早见那灵元隐约,几成虚影,落入东南地界上去了。
他急急追赶上去,那灵元却杳杳灭灭,不知去向了。
错失了良机矣!
费天君跌足长叹,转身欲走,忽又想道:这元灵毕竟在红尘东南之地,待我慢慢寻去,就是在大海里捞针,也总有寻找到它的一日。
此念一定,费天君就飘飘然然落入了红尘之内,却正是在江南地界上,但见山川历历,市衢吵杂,已然身在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