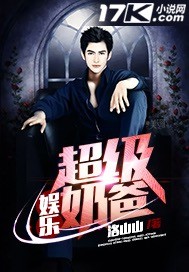付教授便不说什么了,目送儿子出门,事情发展到这样,她心里也不好受。沈知傲昨天晚上来了,他们聊了聊,说起闵洋以前那个吸毒的女朋友和婉如现在徒有其表的丈夫,两人一阵唏嘘叹息,两个漂亮优秀的孩子,怎么都没有一个美好的感情呢。
闵洋几乎是冒着违章的风险冲到婉如家的,婉如打开门,一下子扑到了他的怀里。他犹豫了一会,然后紧紧地将她抱住,从她的身上流露出一股熟悉而陌生的气味,温和的淡淡的香水味,像春天里的花朵,是赏心悦目的,轻松的。
而方锐呢,她是寒冬和酷暑里的一棵小草,总让人担心她能否经受的住挫折,她的气味是忐忑的,焦虑的。
他沉溺在婉如给予的莫名的踏实感中,好像什么事也没在她身上发生过,他们还很年轻,人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明明他们真的还很年轻,但一想到方锐,闵洋就觉得自己已经老了。
在这一刻,婉如好想问他:“闵洋,你喜欢我吗?我和尹山离婚,我们在一起好吗?”
“离婚”,“在一起”,荒诞至极的想法,她的心底里涌出一阵凄凉,似乎已经习惯闵洋是方锐的了,打破这种习惯即是不对的。
抬眼望他,他的眼圈泛红,家里没有开灯,微薄的晨曦照在地板上,犹如年少时的白月光,她用手去抚摸他的脸,说:“闵洋,我这辈子也不会有一个完完整整的爱情了。”
闵洋仿佛看到了主持黄昏电台的婉如,文艺的,伤感的,有种令他捉摸不透的神秘和吸引力。门开了,尹山酒气熏天地走进来,两人从恍惚中醒来。婉如下意识地忙松开手,闵洋也松开了,他们的样子像极了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尹山横眼瞥了一下他们,径直走向卧室,闵洋看了一眼手表,尴尬地道:“我先走了。”
“我跟你一起走。”
她重新抓住他的手,闵洋点点头,却下意识地缩回了手。房间里传来尹山的叫声:“婉如,你过来一下!”
婉如抓闵洋的手更紧了,闵洋道:“那我先走了。”
她垂下眼睑,表示默认了,虽然万般舍不得。闵洋向外走,她向房间走,大门关上的一瞬间,尹山的一个巴掌也扇了过来。
婉如瞪大眼睛咆哮道:“姓尹的,你疯啦!”
尹山一把拽紧她的头发,将她整个人往墙上撞,婉如还没反应过来,半张脸已“咕咚”一声贴上墙面又弹出,顿时火辣辣的疼痛在颧骨处蔓延开。尹山仍不愿罢休,狠狠地捏住她的脖颈甩出去,婉如摔到了地板上,顿时献血从鼻子里向外涌,尹山骂道:“贱货!偷男人偷到家里来了!我还没死呢!不要脸的东西!”
婉如倔强而绝望地瞪着他,道:“我就不要脸了!我不要脸怎么了!来啊!把我打死啊!”
“你是我的女人!你是我的!我看你再敢招惹别的男人!你再敢!”
尹山又将她扔到床上,婉如抗拒着,挣扎着,撕心裂肺的屈辱像刀一样在戳她的心,越挣扎,这个男人越疯狂.
“沈婉如,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他咆哮道,将婉如的脸扇到另一边,婉如闭上眼睛,脑袋是空的,可有好多事从眼前飘过,五颜六色的,罪恶的,疯狂的,她努力去想闵洋。
闵洋,婉如的嘴角上扬,仿佛嗅到了春天的味道,他在风里朝她微笑。
闵洋在楼下等了一会,自己都不知道在等什么,耳边回荡着婉如的那句话:我这辈子也不会有一个完完整整的爱情了,他回想着,迈不开步子。欧阳疏竹从车里走出来,叫道:“哎,陪了她一晚上?”
闵洋回望了一眼,道:“尹山回来了。”
欧阳疏竹用咬嘴唇来掩饰他的痛苦,道:“尹山已经疯了吧。”
闵洋又看了一眼欧阳疏竹,他一脸倦容,未加思索道:“你昨晚干嘛了?”
“新交了一个小女友,你说能干嘛。”
闵洋便转移话题道:“我们把婉如的生活搞得一团糟,是不是要负责任。”
“你是律师啊,从法律上来讲不需要。”
“你和婉如有什么深仇大恨啊?”
“我只是看不惯她的丈夫。”
闵洋叹口气,他们在这马后炮讨论来讨论去毫无意义,道:“我要去所里了,你呢?”
欧阳疏竹抬头望向婉如家的方向,道:“你别管我。”
“行,我走了。”闵洋拍了拍欧阳疏竹的肩,意味深长地说了句:“量力而为吧,生活不是我们遇到的案件,不会一切尽在掌控。”
欧阳疏竹哪听得进去,他另有打算。
方锐在新闻里看到了自己,她的弟弟们看到了,全市的人都看到了。二弟方成给她打了电话,问她要钱,问揽着她的那个男人是谁,每个月给她多少钱。方锐气的把电话挂了,没多久父亲方力的电话跟了进来。
方力现在知道方锐在做模特了,先是劈头盖脸骂她,从头到脚数落出一百个理由来嘲笑她,直到听到方锐结巴的喘气声才罢休,仿佛非得达到这样的目的,让她畏惧,战战兢兢,对整个家庭臣服。
方力道:“家里快吃不上饭了,你怎么不给家里钱啊?啊!”
“爸,我现在手上没钱。”
“那个男人呢?你让那个男人白睡了啊!他不给你钱啊!”
方锐握着手机的手禁不住发抖,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事都变了,父亲和弟弟们也变得更贪得无厌,他们从记恨别人吃大闸蟹变成了渴望每日能吃上大闸蟹。在方力尖锐的喋喋不休中,她颤巍着将电话摁掉,并且关了机,然而心里并不是特别舒坦,习惯性地觉得给了家里钱,换来的暂时安宁才让她踏实。
可哪里来的那么多钱呢,不劳而获的人体会不了赚钱的艰辛,会所的工作辞了,星宸的工资还未发,在餐厅赚的那些钱只够果腹,钱钱钱,除了钱,这个家还需要她吗。
她难受着,自我安慰着,但仍然决定换衣服准备去餐厅上班。
她今天没去星宸公司,曹丛河通知她避避风头,刚得到这份工作就出了这档子事,不是什么好兆头。但她的人生中有哪件事带给过她惊喜,也早已习以为常失望了,般配的闵洋和婉如,薄情的家人,艰难的处境,一帧帧画面从眼前闪过,为了生计奔波的人是没权利谈情绪的,无论情绪怎样,该做的事还得做,没有其它的选择。
头发梳到一半,想到闵洋,她突然疲惫的连举手都困难了,抹了把眼泪,快速地趿拉上鞋。
住在这里的人员复杂,有外来打工的人;有等回迁房的本地居民;也有为省吃住开销的白领图这里房租便宜,却打扮得光鲜亮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天楼道里像菜市场一样热闹。
方锐属于为数不多的第四种人,她的家离这里不远,但有家不能回,因为总是半夜归来,那些熬夜洗衣服的妇女看她的眼神充满了异样,一个单身的小姑娘总会令人浮想联翩。
方锐知趣,她不跟他们任何一类人走得近,没人知道她的故事,她的过去和现在,也没人懂她的孤独和害怕。
而这里的很多人是坦坦荡荡的,他们成为了朋友,恋人,抑或是隐秘的一种关系,在异乡通过各种方式抱团取暖。她刚住过来的时候,经常会和一对年轻的男女碰上面,他们从一扇门里手牵手走出,有时还会旁若无人地接吻,恩爱的很。
可有一天,男人回老家结婚了,再来的时候把他的妻子也带来了,他妻子的肚子已挺得老高,没过多久就生了一个女儿。他妻子是从医院一路哭回来的,因为之前所有人都说她一定会生一个儿子,男人也不安慰她,一直站在门口抽烟,倒是因他妻子到来不得不搬回隔壁住的那个女人热情地端了一碗鸡汤过去。
那天方锐毒瘾发作,正用牙齿拼命咬住防盗窗的栏杆,睁大眼睛望着那个女人忙里忙外地买鸡、杀鸡、熬鸡汤,就像对待身边一个特别重要的人似的,豆大的汗珠从她的额头滚到心里,洗刷着她自认为的肮脏和卑微。
后来那个女人没有再找过男朋友,服侍男人的妻子做完整个月子。
每次觉得快控制不住毒瘾,整个人游离在死亡边缘的时候,方锐就会想起这个女人。她是怎么做到这样若无其事的,是从哪里来的力量和韧劲。有次方锐还在楼下碰到那个女人,那女人说:“你是住在二楼的吗?有空我去找你玩。”
方锐敷衍地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主动来搭讪,或许因为方锐发现了她一个秘密,她也发现了方锐什么秘密,认为他们是同道中人。
方锐仔细看过她的眼睛,里面写满了倔强和无奈。
敲门声,方锐问道:“谁啊?”
敲门的人不回应,敲门声却没停止。
“是谁?”
“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