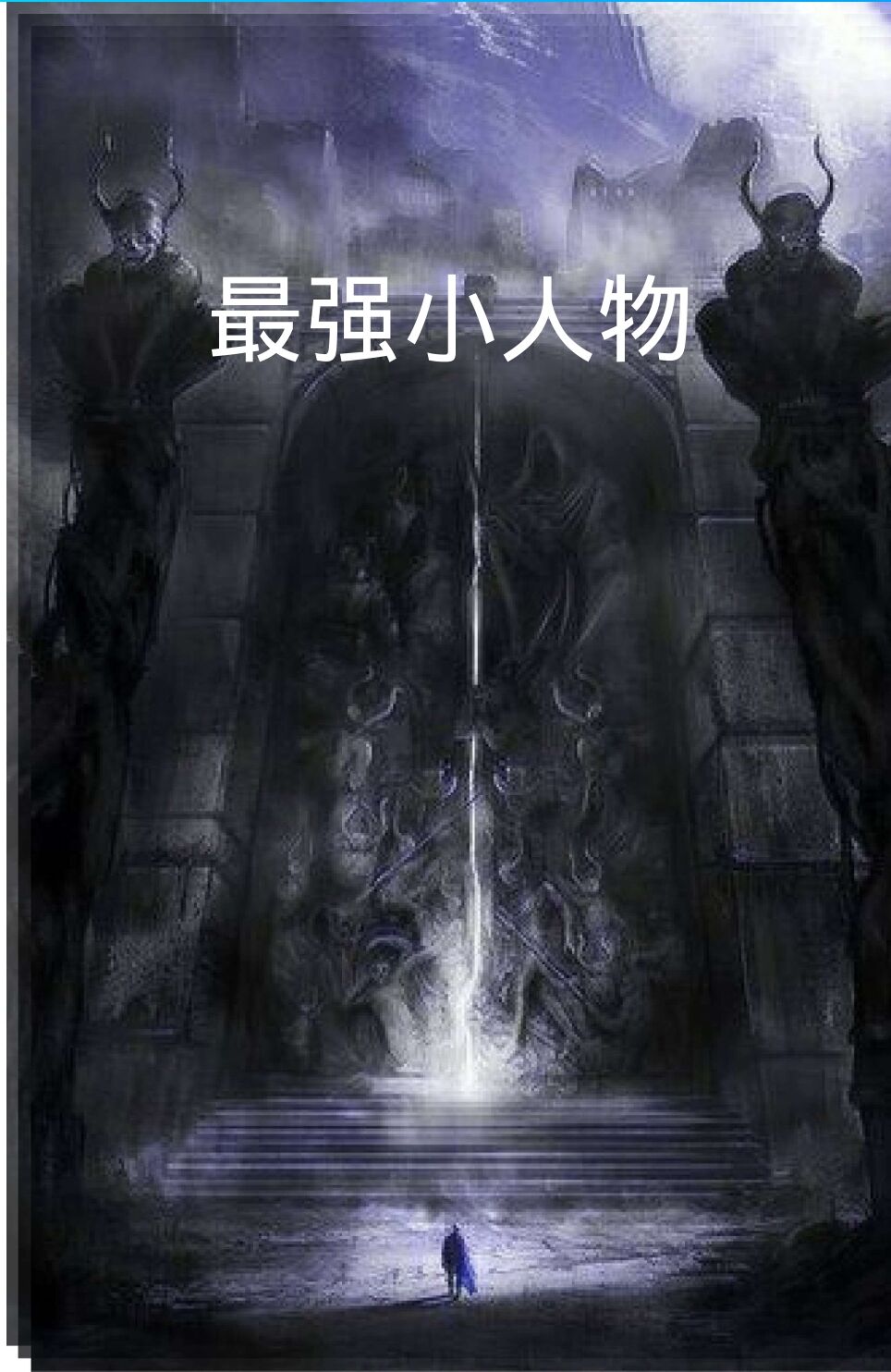刘玉升当上了刘家大院的族长后,领着族人和长工、短工早起打垄铲田,晚上还领着人榨油,没日没夜的劳作,干木工活儿更是行家里手,那时候一个木匠轻松的养活一家人,他的勤劳得到了另一个美誉——刘半夜。当时的富裕来自勤劳和善于经营,再加扩大经营了三个榨油厂、三个酒厂、两个木工厂、两个肥皂厂,在街里又开了商店,还在大商店里投股份,刘家大院,富甲一方,家人吃穿用度远远好于其他人家。每年上交的皇粮、皇油、肉、皮毛、药材、豆饼等,交的早,交的足,交的质量又好,受到官府的表彰,后来县衙授予他九品庄头的称号,还有一定的职位,要他负责西南部半个县的征收工作,他穿着官服骑着马到沙兰站、新官地、上马河、杏山、莲花等地征收皇粮、国税,还有天灾免检税务等工作,一年忙到头,他分身无术,只好将家族的族长让给了弟弟刘玉珠,和一些族人来管理工厂。刘善人的称谓实际上是三个人——刘君启、刘玉升、刘玉珠,他们都致力于扶贫帮困,救助灾民,那时候总有大量逃荒的人来到这个苦寒之地,没有物质的保障早冻死饿死在街上了。
刘家大院儿的生产管理方法,完全是家长式的,刘君启和他培养出来的刘玉升,将四百垧土地分成了几个区,由刘玉升的兄弟们各自管理一个区,那十多个工厂也由侄子们和一些工人来管理,但是有一个大掌柜,他受族长管理,下面的作坊是一个管账先生一本账,一个铺子一个钱柜子,每天晚上算账,收支每月报账,没有任何监督。造成的结果就是谁都往自己兜里揣,几年后,各家都富的沟满壕平的,钱来得容易去得就快,赌博成风,一夜之间就能倾家荡产,吃喝嫖赌成性。他们的大锅饭制度,少部分人搂足了就借机闹分家,清朝末年百日维新期间闹分家,山里的土匪骑马下山,来到刘家大院,刘善人一看,正是当年救过的鋦锅匠,当年他离开刘家大院儿后就去山里当了土匪,外号叫“杠公平”,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公平的世外桃源,抢一些为富不仁者。他听说刘家大院儿闹分家就下山来劝,刘家答应不分家了,他才走,走时“杠公平”送给刘善人五根金条。
第二次闹分家是辛亥革命期间,那一年清朝垮台了。皇粮国税不收了,刘玉升召开全族大会,他说眼下闹革命推翻了满清,不交皇粮国税了,这是咱们发财的好机会。咱们有枪有炮还能看家护院,还能防土匪,刘家大院儿又坚持了十八年,这十八年是刘家大院最富裕的时期,也是谁管事谁贪污的最严重的时期。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刘家大院在官府和地方大户家长的支持下开始分家,分得很公平,还留了十顷良田作为公祭祖先之用(每年七月十五祭祖、宴会)。光阴如梭,伪满时期民不聊生,又是抓劳工,又是抓经济犯,刘家祭祖仪式简化只是磕磕头,烧烧纸罢了。那十顷祭祖的良田也给了刘氏一位老光棍娶媳妇用了。光复以后划分成分,刘家大院里的人家基本划为了地主、富农。
注:刘家大院形成于清朝咸丰年间,解散于一九二八年,是富甲一方、家登高厚的家族,最兴旺时有良田四百多垧。玄武湖周围到哈达湾、江北从东沟村到红石砬子都是他们家的土地。然而最初却是由赤贫的农人发展而来。 现在的上官村四周还有原来院落的地基,最兴旺的时候大院内有宽阔的街道,有大四合院五座,每个四合院有正房十间,厢房十到二十间,另有仓库院、大车院、牲口院、家禽院、打场院(打谷场地)、还有榨油厂、木工厂、酒坊、粉房、糕点厂。所有这些院落被大围墙围住,高高的围墙上有四座炮楼,大门外有影壁,总体规模就是现在西上官村的面积,院内设有大食堂,长七十米,每餐可供上百人吃饭,还有小食堂,是为客人准备的,餐桌和椅子都是长条形的,碗盘全是木质的(据说不容易摔坏)。大院设有私塾,除自家子女上学外,外族的学生也可以来上学(据说收外人的学费)。院内有大车十多辆,马、骡、驴、牛、羊成群。在上马河村和三陵村建有榨油房,控制着宁安南片的食用油业,在这两个地方还有木工厂、酒坊和糕点厂,在东京城(现渤海镇)繁华地段有商店,出卖他们自家的产品和紧俏商品以及当时最时尚的服装(经理从俄罗斯、日本、沈阳、上海进货);还是宁安一些商店的股东。江北(上官村后面就是牡丹江,牡丹江北岸被称做江北)建有供乞丐、流浪汉居住的慈善房,能容纳一百多人吃住。所以庄主刘君启、刘玉升(两个族长)有刘大善人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