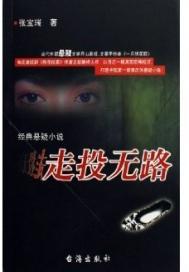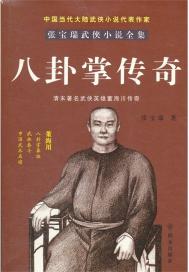说明:
这是我在自传性“记忆文学”《吾家小史》中的冥思段落,也是全书的精神归结。在这里,我完成了一种特殊的写作体验。
我爸爸,这位在“**”灾难中被整整关押了十年之久始终没有屈服的老英雄,却在“**”结束之后的二十六年,被国内一些文化传媒对我的诽谤活活气死了。诽谤的规模铺天盖地,诽谤的内容因为彻底颠倒而让他极度愤怒。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习惯性地掩护着诽谤者,使人们目睹大量志士仁人的血迹而不知道“谗夫”们的名字。但是,爸爸和我却知道今天那些“谗夫”的名字,以及他们在灾难岁月中的斑斑劣迹。爸爸当然不怕他们,但当他发现竟有那么多官方传媒站在他们一边,而法律失语,知者沉默,同行窃喜,群氓起哄,他活不下去了。
爸爸的坟墓筑在家乡的山岙里,骨灰盒暂放在上海一个殡仪馆的安灵堂里。那天,我得到了一个消息,爸爸、妈妈当年媒人余鸿文先生的骨灰盒也在同一个安灵堂,就觉得应该去祭拜一次。正是他老人家的大媒,有了我生命的起点。同时,我也可以再一次照拂一下爸爸的灵位。
那天祭拜完毕以后,我顺着安灵堂的甬道离开,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笑容,那是一个骨灰盒上一帧发黄的照片。一看名字,原来是我在学术界的忘年之交徐扶明教授。我立即后退一步,向他深深鞠了一躬。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觉得这里可能还有其他文化界人士,便放慢脚步,左右打量。这一打量不要紧,就在徐扶明教授对面,我看到了曾远风的名字。他的告发,曾使徐扶明教授入狱多年。前几年,他又是诽谤我的主力“谗夫”之一。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是进攻者,但不知什么时候,也进入到了这里。
走出安灵堂大门时我又停步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余颐贤,出现在门内的那一格。这是家乡那个著名盗墓者的名字,我没见过这个人,却知道他似乎又神秘地做过很多好事。是他吗?也许是重名?希望是他,他让我想起了家乡山间的夜夜月色。
记得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曾经说过,过程性的回忆越丰富,越会让人产生惯性下滑般的迟钝。因此,需要阻断,需要间离,让讲者和听者都陡然停步,获得思考。
我一直在等待这种停步的机会,此刻出现了。在安灵堂门口,我又回首望了一眼。除我爸爸之外,余鸿文先生、徐扶明先生、余颐贤先生,包括那位我一时还不愿意称“先生”的曾远风,都一起在这里停步。那么,我也找到了坐下来的理由。
安灵堂不远处有两把石椅,朝着一个小小的松柏林。边上,又有一个浅浅的水池,水面上浮着大片枯叶。
我在一把石椅上坐下,微闭着眼睛。一开始思绪很杂,跳荡滑动,慢慢舒了几口气,安静下来。
我的眼前,出现了这些老人,我对他们轻声说话。他们没有表情,但似乎又有表情。
我第一个想恭恭敬敬地上前交谈的,是余鸿文先生。
余鸿文先生,我应该叫您一声爷爷。我出生时,祖父早已去世,因此从小没叫过谁爷爷。从前见到您时也曾经想叫,又觉得不好意思。
现在可以叫一声了,但是我仅仅这么一想,还没有叫出口呢,就觉得自己已经蹲到了您的膝下。抬头看您,白须宽袄,太阳在您背上。
在您背后,仿佛还远远近近地站着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你们是一代人。他们走得比您早,因此看过去有点影影绰绰。
我不知道,我的长辈,当你们听说自己的一个孙儿成了“中国历来受诽谤最多的独立知识分子”时,会是什么感觉。是担忧、心疼、愤怒,还是自豪?
这个称号,是几个学者经过认真调查才得出的。我当时一听也怀疑,后来仔细一想,如果不是只算一时一地,而是算二十年的连续不断,算每一次的全国规模,确实没有人能超过。
我估计,你们之中,独独对这件事感到自豪的一定是祖母,我已经看到她炯炯的目光。其他长辈,多少都有点困惑:怎么会是这样?
对此,我愿意接受你们的盘问。
代表长辈盘问我的,应该是作为我父母媒人的您,余鸿文先生。
我似乎已经听到您的声音。
您分明在说:“讨论诽谤,不必看内容,只看它为什么发生。”
我点头。
于是您开始问了:“你和诽谤者之间,有没有权位之争?”
我回答道:“自从二十年前辞职后,我没有任何官职,也不是什么代表、委员,又早就退出一切官方协会,因此没有丝毫权位可言。他们能争什么?”
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利益之争?”
我回答道:“我几百万言的研究著作,十几万公里的考察计划,从开始到完成,从未申请过一分钱的政府资助。他们能争什么?”
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学术之争?”
我回答:“我的研究课题从来不与别人相撞,我的考察路线从来不与别人交错,我的表述方式从来不与别人近似。他们能争什么?”
您继续问:“你与他们,有没有意气之争?”
我回答:“你们看见了,那么多人连续伤害我二十几年。有几个人已经把伤害我当作一项稳定的谋生职业,我却从来没有回击一句,也从来没有点过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
您停止提问,静静地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了您的声音:“你的每一项回答,大家都可以见证。看来你是一个最不应该受到诽谤的人,却受到了最多的诽谤。造成这种颠倒一定有一个特殊原因,例如,刚才我想,是不是你太招人嫉妒?”
我回答道:“嫉妒太普通,不是特殊原因。中国文化界可以被嫉妒的人很多,但他们都没有招来那么长时间的诽谤。”
您说:“听口气,你自己好像已经有答案了。”
我说:“我自己也曾经百思不解,后来,一番回忆使我找到了钥匙。”
“什么回忆?”您问。
我说:“回忆起了我还没有辞职的二十多年前。那时候,我招人嫉妒的理由比后来多得多。我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最年轻的高校校长、最年轻的厅级官员,而且还执掌上海市那么多人的职称评选。我当时的行事风格,更是雷厉风行、敢作敢为。但是,整整六年,我不仅没有受到丝毫诽谤,而且也没有听到过一句非议。连后来诽谤我最起劲的那几个人,当时也全部对我甜言蜜语、赞颂不止。”
“我已经猜到你的答案了,”您说,“你遭到长期诽谤的最重要原因,是比较彻底地离开了一种体制。”
我说:“体制是一种力学结构,就像一个城堡。身在其中,即使互相嫉妒,却也互相牵制,获得平衡和安全。不知哪一天,有一个人悄悄地打开城门出去了,城门在他身后关闭,而他骑在马背上的种种行为又经常出现在城里人的视线之内。他的自由,他的独立,他的醒目,无意之中都变成了对城内生态的嘲谑。结果可想而知,他必然成为射箭的目标。由于城门已关,射箭者没有后顾之忧。”
“这样的城堡,可能不止一个吧?”您问。
“当然。”我说,“城堡的本性是对峙,如果只是一个,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在,有的城堡因为有国力支撑而十分堂皇,有的城堡则因为有国外背景而相当热闹。我呢,只能吟诵鲁迅的诗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但是我比鲁迅更彻底,连戟也没有。”
您点了点头,似乎不想再问,却还是轻声问了出来:“堡外生活既孤独又艰险,你能不能,从哪个边门重返一个安全的城堡?”
我说:“我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个城堡。官方体制对文化创造,有利有弊,弊多利少。古今中外都产生过不少排场很大的官方文化,这当然也不错,但是一切真正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化大多不在其内。这是因为,行政思维和文化思维虽有部分重叠但本性不同。前者以统一而宏大的典仪抵达有序欢愉,后者以个性而诗化的秘径抵达终极关怀。现在,前者太强势了,连很多自命清高的学者都在暗暗争夺行政级别,这更使很多行政官员对文化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和无知。长此以往,前者极有可能吞没后者。您看现在,财源滚滚而文事寂寥,精神枯窘而处处嬉闹,便是征兆。因此,我要不断地站在外面提醒,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您又问:“那么另一个城堡呢?”
我说:“对那个城堡我曾抱有希望,希望它能批判专制弊端,揭露权贵集团,推进政治改革,但现在已经失望。因为它掺入了太多的投机、虚假和表演。我曾多次试着与这个城堡里的人对话,发觉他们大多自命为中国的救赎者,却以揭秘的腔调散布着各种谣言,而且总是把一切文化问题全都推向政治批判,好像天下除了政治批判之外就不存在别的问题。他们那些貌似激烈的言论,初听起来还有一点刺激,再听下去就无聊了。”
您说:“看来,你只能左右不是人了。但是,我要以长辈的身份告诉你:不怕。大智不群,大善无帮,何惧孤步,何惧毁谤。”
我说:“对,不怕。”
与余鸿文先生的对话有点累。他的那么多盘问,我知道,正是代表众多长辈对我的审讯。
接下来就不会这么严肃了,急着想说话的,是徐扶明先生。徐扶明先生历来寡言,现在仍然微笑着等我开口,他很可能像往常一样,只听不说。
徐先生,我的朋友,刚才我在安灵堂,一心只想把您从曾远风附近移开。您告诉过我,人生如戏,角色早定,他永远打人,您永远挨打。在这里你们靠得那么近,又是面对面,我不放心。
但后来一想,不移也罢。他从前打人,靠的是诬陷、造谣、告发,现在到了你们这里,他毕生功夫全废,那您还怕他什么呢?
从此,您可以近距离地盯着他看。我早就发现,凡是害人的人,目光总是游移的。他会用眼睛的余光来窥探您,您还是不放过。世上再阴险毒辣的人,也受不住您这种盯住不放的目光,只能快步逃离。但是,在这安灵堂的小格子、小盒子中,他能往哪里逃?因此在我看来,这就是“末日审判”。审判的法官,就是一生的被害者,审判的语言,就是盯住不放的目光。
您的目光,过去的主题是惆怅。我曾经责怪您为什么不增添一点愤怒,现在我不责怪了,只劝您增添一点嘲讽。像曾远风这样一直气焰万丈的人最后也不得不让您来日夜看管,看管着他无声无息、无亲无友的终点,给一点嘲讽正合适。
更需要嘲讽的却是人世间,居然怂恿了他那么久,给他喝彩,给他版面,给他伸展拳脚的平台,几十年间没有对他有过一丝一毫的劝阻和批评,使他无法收手,难于后退。直到他一头扎在这里,人们才弃之如敝帚,转身去物色新的替代者,让他们来制造新的不幸。这,还不值得嘲讽吗?
徐扶明先生,在中国戏曲声腔史的研究上,您是我的师长,但在社会人生奥秘上,我要不客气地说,小弟我可以做您的师长。今天我要问您一句:为什么曾远风永远打人,而您永远挨打?
我看到您在摇头,直愣愣地等待着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很简单:他打人,是为了不挨打;您挨打,是因为不打人。
打人,也叫整人、毁人,细说起来也就是从政治上、道德上、名誉上攻击他人,这种事情全世界都有,但在中国却变成了一个魔幻事业。
您会问:怎么会是“魔幻事业”呢?
我要告诉您:这,与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有关。很多民众只要从攻击者嘴里听到别人可能有什么问题,就会非常兴奋地相信,还会立即把攻击者看成是政治上的斗士,道德上的楷模,大家都激情追随,投入声讨。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事态已经变成了那个被攻击者与广大民众的对决,攻击者不再担负任何责任。有些官方媒体又会火上加油,把每一场围攻看成是“民意”,把被攻击者看成是“有争议的人物”,使攻击很快就具有了正义性。
因此,攻击者一旦出手,就有金袍披身,从者如云。这几十年我们都看到了,那么多中国人一拨又一拔地轮着受难,只有一批人奇迹般地立于不败之地,那就是他们。
您在“**”中受到曾远风的攻击而入狱多年,其实也有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可以脱身,那就是攻击别人,包括攻击他。而且,这种攻击永远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因此,您的受难,并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您自己,您不会攻击他人。
我也和您一样,从来没有做过“以攻为守”的事情。对此,我的克制比您更加不易。您老兄身上可能压根儿不存在向别人进攻的能力,我却不是。您知道,我是历届“世界大学生辩论赛”的总评审,在语言上的攻伐之道,那些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但是,对于放弃攻击,我们两个都不会后悔。
不妨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您跟着我,痛痛快快地把他们骂倒了,世上多了两个机智的攻击者而少了两个纯粹的文化人,我们会满意吗?我想,我们反而会后悔。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胜利。只希望有一天,新的“曾远风”又要当街追打新的“徐扶明”时,中国的民众和传媒不再像过去和现在这样,一起助威呐喊。
仅此而已。
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也还需要长时间的启蒙。
也许会有这一天,但对我来说,华发已生,暮雾已沉,好像等不到了。
与徐扶明先生说完话,当然就躲不过近在咫尺的曾远风了。其实我也不想躲,很想与他交谈一番。但估计,他也只会听,不会说。
从哪儿开口呢?与他这样的人谈话,我一时还拿不定方向。
曾远风,在年龄上你是我的前辈。你告发徐扶明先生“攻击样板戏”的时候,我才十九岁;徐扶明先生终于平反,而你又转身成为“**”的批判者时,我已经三十三岁;你向我告发那个姓沙的左派编剧时,我四十一岁;你向全国媒体告发我为一个流亡人士的后辈写序言时,我四十三岁;你参与那几个“啃余族”对我的围攻时,我五十六岁;你突然以“异议分子”的身份向外国人告发中国的很多人和很多事时,我五十九岁。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你一定还实施了很多很多我不知道的告发,请原谅我挂一漏万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你以不寻常的方式陪伴了我大半辈子。
亲人的陪伴增加了我的脆弱,你的陪伴增加了我的坚强。因此,你对我相当重要。
你早年读过中文系,后来的身份,是“编剧”、“编辑”、“杂文作家”。你让我想到十几年来一直在诽谤我的那几个“啃余族”与你一样,清一色出自于中文系,都曾经染指文学创作,却又文思枯窘而改写批判文章和告发信。有趣的是,当年你向我告发的那个左派编剧,后来也走了一条与你相同的路:借由文艺玩政治,天天伤害无辜者。
说远一点,你曾经效忠过的“***”里边,也有三个人是文艺出身。如此一想我就霍然贯通,原来你们把文艺创作中的虚构、想象、夸张、煽情全都用到了真实社会的人事上了。你们把伪造当作了情节,把狂想当作了浪漫,把谩骂当作了朗诵,把谣言当作了台词,把围攻当作了排演。只可怜了广大无知的观众,居然弄假成真。
我刚刚在与徐扶明先生谈话的时候曾说到,很多浅薄的民众特别容易追随像你这样不断地从政治、道德、名誉上攻击他人的人,使你们经常“金袍披身,从者如云”。现在我要加一句,这些民众最值得同情之处,不是追随你们,而是不知道你们全在扮演。
近几年,你们这帮人都齐刷刷地扮演起了“异议分子”,开始改说“民主”、“人权”、“自由”之类的台词。这,实在太搞笑了。这些美好的社会课题,不正是我们一直在奋斗的目标吗,怎么一转眼被你们抢了过去?你们又在“盗版”了。盗版毕竟不是正版,同样这几个概念,从你们嘴里说出来全都变了味道,成了反讽。
先说“民主”。这个概念你们在文章中天天高喊,前面还隐藏着一个“大”字,诱骗民众进行大诬陷、大批斗、大伤害。其实你们内心是害怕广大民众的,例如你们最嫉恨我的书连续畅销二十年,其实就是嫉恨广大读者的“阅读民主”。为此我不禁要笑问:敢不敢进行几次民意测验,让广大民众在你们和我之间做一个选择?不敢了吧,还“民主”!
还有“人权”。这么多年,你们用大量肮脏的谣言伤害了我的名誉权,伤害了我妻子的工作权,伤害了我父亲的生存权,所有这些人,都没有一官半职。难道,这都不是“人权”?
再说“自由”。你们用集中诬陷的手段侵犯了我的写作自由、声辩自由、居住自由,但是凭着媒体的起哄、法律的放任、官方的漠然,从来不必支付任何代价,不必做任何道歉。我想问,古今中外几千年,还有什么人比你们更“自由”?还有什么人比你们更需要还给他人以“自由”?
你听得出来,这是反问,不求回答。真正的问题也有一个,存在心底很久了,还是说出来吧:那么多年,你们这批人难道从来都没有担心过法律的追诉?你们难道就能断定,中国的法律一直会像过去那样偏袒你们?
对于这个问题,你也不必回答。既然你老人家已经来到这里,不说法律也罢。我只希望你还是认真地看一看你的对面,那儿有一位与你同龄的老人,因为被你诬告而入狱多年。平反之后,他烧掉了你的罪证,没有说过你一句重话,而你却没有投过去一个抱歉的眼神。我现在终于明白,一种冥冥之中的力量把你们两人安排得那么近,可能是别有深意。
如果有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却特别想与他说话,这个人就是余颐贤先生。
直到此刻我仍然不知道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心目中只是一团迷雾、一堆疑问。隐约间似乎有一股妖气,但也可能是仙气,似远似近。越是这样就越是好奇,我要腾空心境,去面对这位姓余的老人。我不知道他以前习惯讲什么方言,余姚的,慈溪的,绍兴的,宁波的,还是杭州的?想来想去,今天我还是与他讲童年时的乡下话吧,那种语调,立即就能带出故乡的山水。那里,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是余颐贤先生长期出没的地方。
余颐贤先生,我没有见过您,不知道您是什么样子的。在想象中,您是一个黑衣人。头上还戴着一顶黑毡帽,帽檐压得低低的,别人很难看到您的眼睛,您却能看到别人。
您的名字,在家乡各村所有余姓同胞中显得特别斯文,一定有一点文化背景,但是乡亲们谁也说不清。您的名声不好,我从小就知道您是盗墓人,乡亲们叫“掘坟光棍”。他们又把你的名字叫成“夜仙”,那是根据谐音读错了。但这么一叫,他们就把吴石岭、大庙岭的夜晚,一半交给了虎狼,一半交给了您。
不好的名声也有好处,那就是让您获得了安静。盗墓,只要不去触碰各个时期当红大人物家的祖坟,就很难成为一个政治话题。因此,你在国共内战和后来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都安然无恙。人们有兴趣把一个名声很好的人一点点搞脏,名声越大越有兴趣,却没有兴趣去对付一个名声不好的人。这就像,一块白布太干净、太晃眼了,大家总要争着投污,即使后来风雨把它冲洗干净了,大家也要接着投;而您从头就是一块黑布,不会有人来关注您。
您在黑乎乎的夜晚好像也动过我曾外祖父的墓,这使我家前辈对您的印象就更坏了。印象的改变,是您在另一个黑乎乎的夜晚给妈妈办的识字班送了课本。这事看起来不大,但对好几个乡村却是雪中送炭。那几个乡村当时正要从长久蒙昧中站立起来,您伸手扶了一把。
有了这件事,我开始相信乡间有关您的一些正面传闻。例如,我小时候曾听邻居大婶说,那个笃公终于在我们村找到已经疯了的女友,是您引的路。而且,您还把自己的一间房子让给他住。这是真的吗?更重要的是,我听李龙说,有一次吴石岭山洪暴发,一个预先挖通的渠口把水引走了,救了山下好几户人家。一个柴夫告诉李龙,这个渠口是您花了半个月时间一锹锹挖通的。这就是说,您在无声无息的游荡间,也做了无声无息的大好事,可能还不止一件。这是真的吗?
我没有期待您的回答,却发现您有了动静。您看着我,轻轻地像咳嗽一样清了一下喉咙,似乎要讲话,但跟着而来的是低哑的笑声。笑声很短,转瞬即逝,这让我很兴奋,因为我有可能与您交谈了,就像我与余鸿文先生。
我多么想引出您的话来,但您对我来说太陌生,很难找到具体话由,因此只能说得抽象一点。
我说:“天下万物转眼都走向了对面,连给它们定位都是徒劳。很多人和很多事,可能在对面和反面更容易找到。”
说到这里我停了下来,等您。很奇怪,您的目光已经不再看我,而是看着远处,看着天。
我决定换一种语言方式。像少数民族对歌,像古代诗人对联,先抛出上一句,来勾出对方的下一句。
我根据您的行迹,说了一句:“最美丽的月色,总是出自荒芜的山谷。”
终于听到了您的声音,您说:“最厚重的文物,总是出自无字的旷野。”
我太高兴了,接着说:“最可笑的假话,总是振振有词。”
您接得很快,马上说:“最可耻的诬陷,总是彬彬有礼。”
我说:“最不洁的目光,总在监察道德。”
您说:“最不通的文人,总在咬文嚼字。”
我说:“最勇猛的将士,总是柔声细语。”
您说:“最无聊的书籍,总是艰涩难读。”
我说:“最兴奋的相晤,总是昔日敌手。”
您说:“最愤恨的切割,总是早年好友。”
我说:“最动听的讲述,总是出自小人之口。”
您说:“最纯粹的孤独,总是属于大师之门。”
我说:“最低俗的交情被日夜的酒水浸泡着,越泡越大。”
您说:“最典雅的友谊被矜持的水笔描画着,越描越淡。”
我不能不对您刮目相看,余颐贤先生。您显然是娴熟古今文字的,但此间的机敏却不是出自技术。好像有一种冥冥中的智慧,通过您,在与我对话。那么,就让我们把话题拓宽一点吧。
我说:“浑身瘢疤的人,老是企图脱下别人的衣衫。”
您说:“已经枯萎的树,立即就能成为打人的棍棒。”
我说:“没有筋骨的藤,最想遮没自己依赖的高墙。”
您说:“突然暴发的水,最想背叛自己凭借的河床。”
我说:“何惧交手,唯惧对峙之人突然倒地。”
您说:“不怕围猎,只怕举弓之手竟是狼爪。”
我说:“何惧天坍,唯惧最后一刻还在寻恨。”
您说:“不怕地裂,只怕临终呼喊仍是谣言。”
我说:“太多的荒诞终于使天地失语。”
您说:“无数的不测早已让山河冷颜。”
我说:“失语的天地尚须留一字曰善。”
您说:“冷颜的山河仍藏得一符曰爱。”
我说:“地球有难余家后人不知大灾何时降临。”
您说:“浮生已过余姓老夫未悟大道是否存在。”
我说:“万般皆空无喜无悲唯馀秋山雨雾缥缈依稀。”
您说:“千载如梭无生无灭只剩月夜鸟声朦胧凄迷。”
像梦游一般,我们的对话完成了。此间似有巫乩作法,使我们两人灵魂出窍,在另一个维度相遇,妙语连珠,尽得天籁。这不是我们的话,却又是我们的。
我最后要说的是:您真是“夜仙”。与您对话,我有点害怕。既然您那么厉害,请一定在那个世界查一查我们余家的来历。古羌人?唐兀人?西夏人?蒙古人?汉人?若是汉人,又源出何处?是山西?是湖北?是福建?是安徽?是浙江?……
但是,我似乎已经听到您的回答:这都不重要。沧海滴水,何问其源?来自无限,归于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