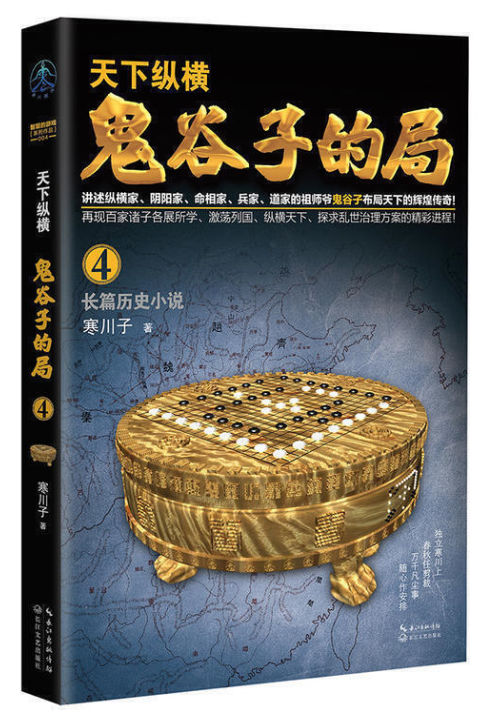审美中的理解与逻辑思维的根本不同,在于它以想象为枢纽。德国近代美学家让·保罗说:“想象能使理智里的绝对和无限的观念比较亲切地、形象地向生命有限的人类呈现
。”与保罗同时代的哲学家谢林干脆把理智和想象的关系提炼成一个命题:“在艺术里,这种理智的形象就是想象
。”其实,想象岂止仅仅与理解、理智有关,保罗认为,它也“是其他心理功能的基本精髓”。
在戏剧审美中,想象的最基本任务是充实舞台形象
。让·保罗说:“想象力能使一切片段的事物变为完全的整体,使缺陷的世界变为完满的世界;它能使一切事物都完整化,甚至也使无限的、无所不包的宇宙变得完整。”
歌德认为,剧场感知主要作用于观众的外在感官,眼睛所看到的戏剧场面是有限的,只有让外在感知接通观众的内在感官,他们的印象才会强烈和深刻,而内在感官主要就是想象力。想象力的作用,是在观众脑海里造成整片的印象
。整片印象一旦形成,反过来会使外在感官产生错觉(幻觉)。面对片断恰如面对全体,面对缺损恰如面对完满。
他借莎士比亚的戏剧为例指出:
眼睛也许可以称作最清澈的感官,通过它能最容易地传达事物。但是内在的感官比它还更清澈,人们通过语言的途径把信息最完善最迅速地传达给内在的感官。语言能开花结果,而眼睛所见的东西,则是外在的,对人们并不发生那么深刻的影响。莎士比亚完全是诉诸人们内在感官的,通过人们内在的感官幻想力,整个形象世界也就活跃起来,因此就产生了整片的印象。关于这种效果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去解释,似乎就像使我们误认为一切事情好像都在我们眼前发生的那种错觉那样。
观众比戏剧家更喜爱这种想象的幻觉,因为这使他们在剧场中加添了一分自由。在这种自由中,理解为想象指路,想象为理解鼓翼,一起飞向歌德所说的整片印象。
观众整片印象的产生,就是对舞台形象的修补。心理学家们把
这种想象称为再现性想象。
法国哑剧表演艺术家马尔索和奥地利哑剧表演艺术家莫尔肖两手空空上台,一声不响地表演,观众却跟着他们进入到了一个个有声有色的戏剧情境之中,这就是诱发和借重观众的再现性想象的典型例子。观众为自己理解了这种特殊的语言而高兴,更为自己进一步与哑剧演员一起通过想象而创造了一个幻觉世界而喜悦。例如,看懂了哑剧演员现在正在没有钢丝的舞台上模仿杂技演员走钢丝,这固然是令人高兴的,但看了一会儿,观众慢慢地感觉到
了钢丝的晃动,风的干扰,站不稳的腿,不敢往下看、又忍不住往下看的眼,满头的汗……观众非常满意这种“错觉”,往往“错觉”越深,掌声越响。这是在享受着一种由表演技巧引起的想象的乐趣。
观众的想象能够百倍地扩大表演效能。例如,哑剧演员一人表演老年妇人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与邻里好友边打毛线边滔滔不绝地讲话,唇舌面颊的活动与打毛线的双手的活动一样灵敏迅捷。实际上,台上既不见毛线,也不见邻座,更没有发生任何谈话的声音,但这一切全都可以借助观众的想象补上,补得比实有其物、实有其人、实有其声更加生动。
如果说,哑剧表演是发挥观众想象的特例,那么,中国传统戏曲则是发挥观众想象的常例了。正如哑剧大师马尔索所说,中国艺术家的手势和身段变化多端,妙不可言,这种象征性艺术是令人震惊的,越是看上去简单,就越是困难。
盖叫天说,在戏曲表演中,“青山、白云、乱石嵯峨的山峰和崎岖不平的山路,都要靠演员的身段给表现出来,让观众随同演员身历其境地一起生活在这幻景中”。
想象中的景物也能比实际景物更加扩形,或者更加显微。梅兰芳在《贵妃醉酒》中把杨贵妃所赏之花的形、色、香,全都描摹得淋漓尽致。嗅觉、味觉、触觉,本不属剧场感知的范畴,但通过想象,它们却可补充和强化剧场感知。
戏剧家焦菊隐指出:
在欣赏戏曲的时候,正因为戏曲最初并不企图消灭剧场性,观众一进剧场就以积极的态度,相当主动地参加到舞台生活里去,在戏剧进行中,他们的想象力
一直是极为活跃的,他们用他们主动的活跃的想象力
,去丰富和补充舞台上的生活。
和表演一样,戏曲舞台美术也特别强调尊重观众的想象力
在演出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它尽量用最少的东西,激发观众的想象力
的最大活跃,使观众通过他们活跃的想象
,参与到舞台生活中来,补充丰富台上的一切,承认台上的一切。
在焦菊隐看来,调动观众的想象是中国戏曲艺术的重大奥秘。
舞台形象的空灵化、简洁化,由于能够有效地承载想象,渐被世界上众多的戏剧家所趋附,并且进一步出现了符号化、抽象化的倾向。前面说到过的奥尼尔主张的面具,就是演出主体的符号化和抽象化。奥尼尔认为,一个戴面具的演员来演古罗马人,要比一个不戴面具的现代人来演更能引发观众的真实感,因为观众可以把自己对于罗马人的想象加入那张空灵的面具。但是,不难看出,作为符号化的艺术手段,不管是中国戏曲中的一桌一椅还是奥尼尔的面具,都不能推崇过甚,更不能使之独立化。符号,只有在结构整体中才有意义,只有在动态流程中才有价值。一个戴面具或不戴面具的演员是否能给观众以一种“古罗马人”的真实感,更重要的是看整个戏剧情境是否“罗马化”。要让中国戏曲中的一桌一椅在观众想象中再现为其他丰富的视象,功夫在演员身上,功夫在桌椅之外。符号化、抽象化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引发观众想象。
比再现性想象更进一步的,是创造性想象。
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曾列举过约翰·辛格的《骑马下海的人》和奥尼尔的《毛猿》的例子。观众听到渔家老妇人在失去所有亲人后平静的自语,可以想象到她的人生经历,还可联想到人与自然力的悲壮搏斗;同样,观众在听到被毛猿弄伤的人在奄奄一息时说的话,也能联想到很多内容。这种联想,范围已远远超过再现性想象了,因此就成了创造性想象
。
不仅优秀的剧作家期待着观众的创造性想象,优秀的导演也有这种期待。他们甚至更迫切地希望能用一些创造性的艺术细节来击发观众的创造性想象。
这里可以举出梅耶荷德导演小仲马的《茶花女》的例子。当男主角阿芒和女主角玛格丽特第一次相遇时,阿芒就爱上了玛格丽特,他把花瓣一片一片地撒到玛格丽特头上;后来他正式求婚时,又把彩纸撒在她的头上;最后由于父亲的阻难,阿芒误会了她,把赌余的纸币向她头上撒去。观众看到此处,立即便能联想到,这位可怜女子迎受过多少残酷的投掷。正是这种联想,创造出了象征意义。
再如,这出戏第一幕,医生为玛格丽特检查身体,高大窗户外射进来的阳光照着一张绿丝绒椅子,椅子上一块刺目的黑色,等到医生离开时从椅子上拿起黑大衣,观众才知道这块黑色是什么——其实此时他们还没有真正懂得。直到剧终,玛格丽特倒在绿丝绒椅子上死去,她黑色的身影正恰与第一幕那块黑色一样,观众立即产生联想,于是才真正懂得了第一幕那块黑色所象征的死亡黑影。
梅耶荷德的这种手法还是局部性的,也有一些戏剧家追求着戏剧的整体性象征,因而也对观众的创造性想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奥尼尔就曾这样寄语美国戏剧: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扩大观众想象的范围,一定要给公众一个这样的机会。据我所知,公众人数逐年增多,并且在精神上日益渴望参加对生活作出富于想象力的解释,而不仅仅把戏剧等同于忠实模仿生活的表面现象。
对观众想象的这种要求,与戏剧领域里理想主义的追求紧密相联,那就不仅仅是在说一种具体的审美心理机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