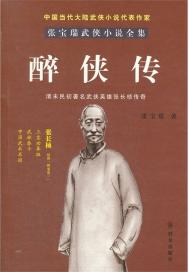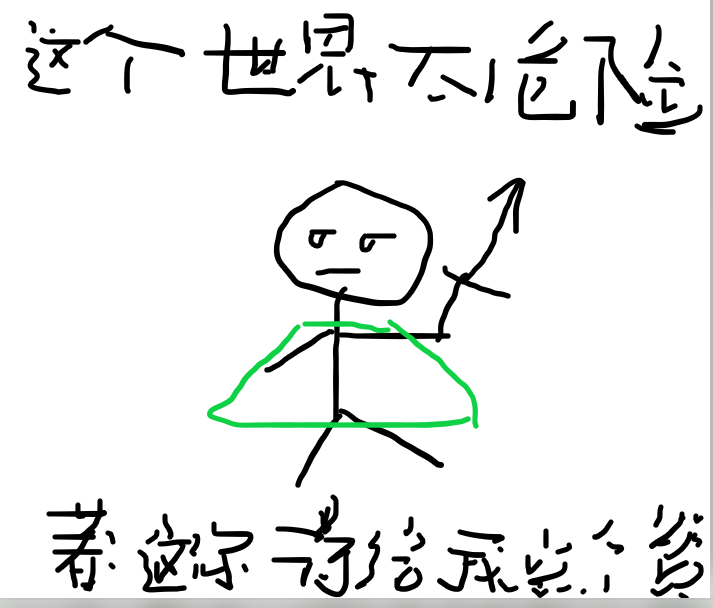·编写手记·
遥远遥远年代里的某一天,原始人捕杀了足够的猎物,饱餐了一顿。也许是熊熊燃烧着的火的温暖,劳顿了一天的人们没有像以往那样,倒头呼呼大睡,也没有人打闹嬉戏——像其它动物群种常做的那样,而是静静地坐着,脑中琢磨一些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们在沉思。回顾一整天的外出打猎觅食的过程,望着身边脚下的猎物的残骸,他们感到自己与猎获物的不同。于是,第一次,人类将自身所处的种群与其他的动物种群有意识地区分开来。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人”,——当然,也许当时还没有这一名称,不同的人类群体对自身的称呼也各不相同,但重要的是,他们意识到自己是独特的,是完全与其它的生物种类或群体相区别的。
这一次“沉思”具有重大意义,它宣告了人类的诞生。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一种事物的存在是靠它与其他事物相区分来获得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原始人开始将自身所属的种群与其它生物种群相区别的那一刻,就意味着人类诞生了。从那一刻开始,原始的人类群体就不再是动物的种群,而开始演变成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所谓文明,也应该是从这一刻开始的。于是,人类逐渐告别蒙昧,文明程度越来越高,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扩展,人类的自我意识也在不断地深化和强化。在人类不断加深对自然界、对其他物种认识的过程中,也开始对自身发问,开始思考自身,审视自身。在人类对自身的审视中,被思考最多的也许就是这一问题(其实一切问题最终也终必归结到这上面):人是什么?“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乃是人类对人自身属性、归属带有终极性质的追问,它关注的实质上是那些人之为人的东西,是人的本质。换句话说,它试图回答的是这样一些问题:到底是什么使我们成为“人”、被称为“人”的?我们作为“人”,与自然界里其他动物、其他物种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这些被称之为“人”的特殊动物,到底是什么?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出现了许多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如果我们做一个大致的考察,就会发现,各种文明形态所以不同,从根本上讲,是与他们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相关联的,换句话说,因为不同文明,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各不相同,他们的表现形式也往往大不一样。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我们传统的儒家文明中,我们的老祖宗在对人的认识上,好像更重视的是对社会既有等级秩序的顺从和维护,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究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固然,儒家文明也提倡“仁”,所谓“仁者,爱人也”。但对“仁”的提倡,是在对既有社会规范服从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且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带有本质论色彩的儒家所谓“仁”的观念,实际上是站在精英的立场上来讨论的,并非我们一般人所认为的“以人为本”观念,而是以秩序、等级为本的。这样,在儒家观念里,“人”实质上是制度、等级、秩序的附属物。儒家这种“人”的观念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祖先的世界观:既然“人”只是秩序、等级的附属物,那么“人”在面对社会,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就只能是围绕着社会旋转,只能是等级、制度的奴仆。于是我们明白,中国文化传统中奴性的广泛存在和根深蒂固,是有其深刻历史根源的,是与我们先人对“人”的这种看法分不开的。
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则有很大不同。在基督教文明中,“人”是上帝的造物,上帝创造了人,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西方的一些关于“人”的基本理念。比如,平等观念,因为既然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创造物,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那么所有的人在绝对公正、绝对永恒的上帝面前就都是平等的,哪怕身为国王,在上帝面前也和俗世社会里低贱的乞丐一样是上帝的子民,而且也都是带有原罪的罪人(圣经记载,人类祖先违反上帝的告诫,经受不诱惑而偷吃了智慧果,被上帝赶出了无忧无虑、永远与幸福相伴的伊甸园),——在基督教的理念中,所有亚当和夏娃的子孙,都继承了亚当和夏娃的罪愆。由此继续延伸,一个必然的逻辑推论就是,既然所有的人,无论是乞丐还是国王,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才子佳人,他们都是上帝面前平等的罪人,那么所有人就都是不完美的,都是由缺点的,而且永远不可能完美,永远不可能没有缺陷。于是,必然的结论就是,人世间根本不存在绝对正确、永远完美的人,任何对上帝之外的世俗之人的崇拜都是荒谬可笑的,更是危险的。因为,对世俗之人的崇拜,其后果必然是专制的降临。基督教文明下的这种对“人”的看法,还包括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我们不仅不应该崇拜俗世里的任何人,而且对于凡尘俗世里的任何人造物,比如国家、民族、制度等等,也不应该崇拜。这种崇拜是对上帝的冒犯,因而是错误的,不应该的。
不过,这并不是说,西方基督教文明蔑视人、贬低人,否定人的存在和价值,相反,对人的意义和价值的肯定,对人的存在、人的创造力的颂扬,一直贯穿于西方社会中。因为,既然人是上帝的造物,更重要的是,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的,那么人的身上,就有了上帝的灵性。换句话说,人的身上具有某种神性。因而,人就是尘世里万事万物中最为高贵的被造物,其他一切上帝的造物,都是为了人类的存在而存在。于是,必然的结论是:人是万物之灵。
在高扬人的高贵和伟大这一方面,我们东方的儒教文明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是具有很大相似性的。《尚书》中就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意思是说,天地生万物,是万物的父母;而我们人类,则是世间万事万物的神灵。这一观念至少在表面上看,与基督教的观念是相似的。类似的说法也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说:“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意思是说,人超然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之上,是天地之间最为尊贵的。而人的至尊至贵体现在:上,人类高于万事万物;下,人类挺身于天地之间。这儿,董仲舒对人类给予了高度评价。这种评价是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对人的评价,是具有某种形似的。
说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人的高度赞扬,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对人的赞颂只是形似,是因为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虽然高度赞美人,讴歌人的创造精神,但是这种讴歌是以另一面作为背景的——西方社会一直贯穿着一种对人的怀疑,对人的警惕。这种对人的怀疑和警惕,其实并非是从基督教进入欧洲之后才有,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存在。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就不断告诫人类,要人们在不断向自然界索取,忘情于追逐外在的功名、财富、富贵、利禄时,千万要不要忘记“认识你自己”。所谓“认识你自己”,在苏格拉底这里实际上就是指:人要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在雅典所做的中心工作,就是提醒雅典的公民们,同神相比、同大自然的无限丰富相比,人的知识是有限度的,在神和自然面前,人是无知的。苏格拉底对人的无知的强调,不是否定人类的智慧和人的创造精神,而是警醒人类,时刻告诫人类:任何狂妄都是无知的表现,因而是可笑的。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与基督教的观念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前边我们已经谈到过基督教信仰中,拒绝承认任何世俗之人或人造物的全知全能、绝对正确和永远的真理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的蒙田说人类的无知是“众师之师”。有趣的是,当蒙田承认人类无知,并称其为“众师之师”的时候,背后隐含的不是对人的否定,不是消极,而是对人的肯定、是积极进取。因为,所谓人类的无知是“众师之师”,其传达的意思是:当人类知道自己无知、知道自己的限度之后,人类就会一次次警醒自己,并由此激励自己不断进取,不断努力,使自己的智慧和知识不断获得增长;又因为人类知道自己无论拥有多么丰富的知识,都始终是无知的,所以他永远都不会流于狂妄,而保持一种有尊严的谦卑。
于是,在对人的认识上,在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上,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东方人肯定人,肯定人的伟大,强调人对其他自然物的特殊地位甚至权力,这是一种单纯的肯定。西方人则不同,他们也肯定人,肯定人的意义和价值,甚至肯定人对自然界其他事物的特权,但是肯定的背后,始终又是以对人的警惕,对人的狂妄及其后果的警觉为背景的。
这儿简单梳理了东西方对人是什么的不同回答,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醒人们,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不是只有一个答案,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答案。那么,哪一个回答或说哪一个答案是正确的?对这一问题,我们不想作出回答,也无法作出回答。想说的只是,在很多时候,用对和错、正确或错误这一类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解释、分析人类现象,往往是于事无补的。在更多的情况下,对包括“人是什么”在内的人类问题的解答,往往各有其合理性,又同时各有其局限性。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学会运用理性去分析、思考和判断,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人类许多问题的解决,其实都是以对问题复杂性的把握为前提的。不过说到“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不管各种具体的回答是什么,始终保持一种有尊严的谦卑,则是最为合理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