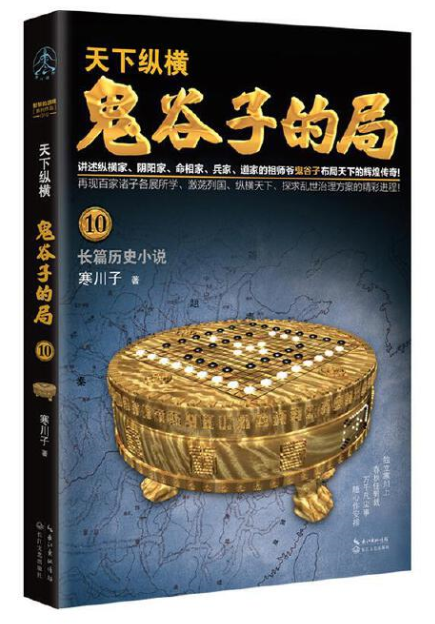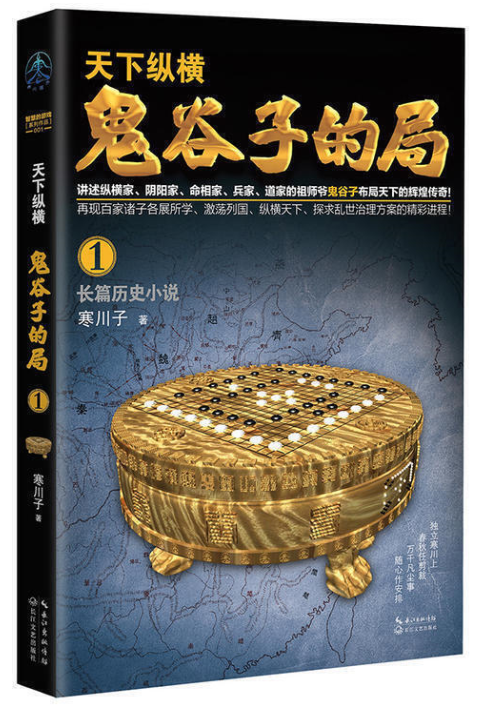【美】卡耐基
我们时代的问题是恰当地管理财富,以使同胞手足之情能维系贫富之间的和谐关系。……
……
……我们的责任就是去做切实可行的事,走出我们这代人在这个时代可能走出的下一步。如果在现存条件下,我们切实可做的事是把普遍人性之树拗弯一点,使之有利于结出硕果,那么,不顾现实、拼命卖力去拔这棵树是一种犯罪。我们也可以去要求去除那些不合我们理想的高级人物,砸烂个人主义、私有财产、财富积累法则和竞争法则。然而这一切正是人类经验的最高成果,是社会迄今生产出最美好果实的土壤。这些法则在发挥作用时,有时是不平等或不公正的。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它们又似乎是不完美的。尽管如此,这些法则如同那些现存的高级人物一样,是迄今人类所能完成的最好,最有价值的事情。
我们刚才确定了一项前提条件。在此前提下,人类的最高利益得到促进,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我们承认这些既存的条件,以此去观察形势,即可得出局面大好的结论。不过随后问题又会冒出来——假如上述一切都是正常的发展,那么我们必须对付的问题只有一个:当文明的基础法则把财富置于少数人之手后,这些人应当如何合理地处置他们的财富呢?我以为,我正是对此问题提出了真正的解答。请注意,这里所谈的财富并非那种经多年努力攒下的积蓄,人们通常靠着它的利息维持舒适的生活,或作家庭教育费用。这点钱算不上财富,它只是小康生活的保障,每个人都应争取得到它。
我所说的是剩余财富,它有三种处置方式。它可以作为遗产由死者家属继承,可以捐赠给公共事业,也可以由活着的所有者进行管理。迄今为止,世界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的多数财富都是以第一和第二种方式使用掉了。让我们依次考查一下每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最不明智的。在君主国家,封地和大部分财产都传给长子,以便父母能把名号爵位完整无损地传给下一代,并从中获得一种虚荣心的满足。今日欧洲,这一阶级的状况已说明这种愿望或野心是何等无聊无益。贵族继承人由于自身的愚笨或由于土地价格下跌而变得生计窘迫,即使在英国,最严格的继承法也无法维持这个世袭阶级的地位,它的土地亦迅速流入外人之手。而在共和体制下,传给子女的财产分配方法要公平得多。但是,无论在哪个国家,有头脑的人都势必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人们为何要把大笔财富留给子孙呢?如果说这样做是出于人之常情,那么,这种常情是否是一种误其子弟的感情呢?一般说来,种种观察证实,这样做对子女并不利,只会令其不胜负担。对国家来说,这种做法也没好处。大笔的遗产赠款往往给接受人带来弊多利少的影响,这已成为不容置疑的定论。因此,人们在向妻女提供一定合理的生活之资,向儿子多少给点津贴之后,就不知该如何去做了。聪明人很快就能得出结论,从自己家庭成员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着想,这种遗赠方式并非处置财产的好方法。
这并不是说,那些没能教育好子女,使之具有谋生手段的人就应该对子女撒手不管,任由他们沦落贫寒。如果有人认为把儿子供养起来,让他们无所事事地生活也挺好,或者采取另外值得称道的做法,培养子女的责任感,不是为钱而是为公众事业工作,那么,从父母角度说,向子女遗赠财产也是合情合理的。世上也有些百万富翁的儿子不为财富所累的例子,他们虽然有钱,却能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这类情况实在是不多见的,虽然弥足珍贵,不幸罕有其匹。而人们必须注意的是规律而不是特例。看一看向继承人遗赠大笔资产的通常结果吧。有识之士必定会说:“我给儿子留下万能的美元,无异于给他留下一个诅咒。”他还会意识到,不是为了子女的幸福而是出于家族的虚荣,人们才会遗赠大笔财产。
再看看第二种方式:死后将财富留作公共事业之用。如果说一个人乐于在自己死后才让自己的钱有益于世,那么,这只能说是一种财富的处置方式。了解一下这些捐赠遗产的效益,结果却不能告慰那些希望身后做些好事的好心人。遗嘱的真正目标往往不能达到,他们的真实意愿也未能履行。这类例子可不算少。在许多情况下,这笔遗产花得冤枉,最终变成了遗嘱人干蠢事的纪念碑。应该好好记住,赚钱需要多大本领,花钱也需要多大本领。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有益于社会。除此之外,如果说人做了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本来不值得赞颂,那么一个人只是死后才把财富留给社会,社会也就无须感谢他,这是天经地义的。人们完全可以这样想,这些人既然用这种方式留下了财富,如果他能携财而去的话,他会一点财产也不留下来。这些人的赠礼缺少格调,人们不会心怀感激地想起他们。所以人们对这种遗赠普遍不持欢迎态度就不足为奇了。
对大笔遗产课以越来越多的遗产税的做法正在进行,这是一个值得欢呼的征兆,它表明社会舆论出现了越来越强的、值得大书特书的变化。宾夕法尼亚州目前除了某些例外,普遍征收市民1/10的遗产税。前些时候,在英国国会上提出的预算也建议增加遗产税。最有意义的是,新的税收将采用累进制。在所有税收形式中,这种税制似乎是最明智的。有些人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聚敛财富(这些财产若能妥善地用于公众事业,定会有益于社会)。有必要让这些人明白,以国家形式存在的社会是不能容忍它所应有的份额遭受如此剥夺的。国家通过征收遗产重税表明,它谴责自私的百万富翁们毫无价值的生活。
国家在这一方向上继续前进是值得欢迎的。诚然,确定富人死后通过国家机构返归大众的遗产限额是不容易的。这种税收一定要采取累进方式。从留给受赡养人的合理资财开始起征,留的钱财越多,税额就越是倍增。直到百万富翁为止,他们的积蓄将和夏洛克的家私一样,起码是——“另有一半充公上交国库”。
这一政策将有力地促使富人在生前参与财富管理,这就是社会须臾不可忘的目标,它迄今已为人民带来了最丰硕的收获。无须担心这一政策会毁损企业的根基,或降低人们积累财富的积极性。因为这个阶级的抱负就是留给后人巨大的财富,使自己死后为人称道。这一政策将会吸引他们更多的关注,而把自己的大笔家产交给国家确也算得上一种颇高尚的野心。
我们现在只剩下一种处置巨额财富的方法了。然而在这种方法中,我们可以找到纠正当前财富分配不均的真正良药,求得穷人和富人的调和——一种和谐的秩序——这是和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着实不同的另一种理想,它只寻求现存条件下的不断进化,而不是彻底推翻我们的文明。这一方式是以强烈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逐步实现它。在这一方式的支配下,我们将建立一个把少数人的剩余财富以最佳方式变为多数人财产的理想之国。这笔财富虽说是经少数人之手予以管理,其目的却是为了公众利益。它能成为改善人类生活的更有效的力量。这比把财富零零碎碎分给老百姓要好得多。即使最穷的人也会最终明白这一道理,并同意让自己的某些同胞集聚大笔资财,用于公众福利。这样做符合大众的根本利益,它比把资财逐年地分配下去要更有价值。
以库珀基金会为例,让我们看看它对纽约那些无计谋生的人广泛施惠的效果如何。库珀先生在生前曾以工资形式(这是所有分配方法中最高级的形式,它强调工作报酬,而非一意宣扬慈善)发放过大致相等的财富。如果我们对前后两种方式略作比较,便不难从中找到改善人们处境的可行办法,而这种办法正埋藏在现存的财富积累法则当中。库珀先生的财产,如若以少量份额平均分给民众,那么其中的大部分将会浪费在人们难填的欲望深壑里,有些难免成为纵欲的借口。即使是那笔使用最得当的款项(它直接用以改善穷人的居住条件)是否能对老百姓的整体产生良好效果,也大可值得怀疑。这种方法自然比不上库珀基金会代代相传、持续产生的效果了。对此,那些鼓吹暴力或激进变革的人应当仔细权衡。
另一个例子是蒂尔登向纽约市遗赠500万元,修建公共图书馆。谈及此事时,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说,要是蒂尔登先生将自己的余生用来好好管理这一大笔钱该有多好。这样做,就不会有法律争议和其他因素阻碍实现他的目标了。姑且让我们假定,蒂尔登先生的百万家私最终得以为城市建起一座宏伟的图书馆,其中的书刊典籍将免费向所有人永远开放,那将是不可估价的壮举。若从曼哈顿岛一带的居民利益出发,把这百万资财零星地分掉就能更好地促进他们的长远利益吗?恐怕最狂热的共产主义鼓吹者会对此存在疑问。而多数有头脑的人却会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
人生中的机遇难得,人的眼界难以展宽,我们所完成的最佳业绩往往是最不完美的;但富人还是应当感谢上苍对他们的珍贵赐福。他们有幸能在生前为同胞大众的长远福利奔走操劳,出钱出力,使大家都能从中获得长久利益,同时也使自己变得高尚。生活的最高目的可能正是这样达到的。我们无须像托尔斯泰伯爵那样去仿效基督的生活,而应该认清时代的条件变化,根据现实要求,以相应的方式来振兴基督精神,坚持为同胞利益工作(这是基督生涯和教诲的精髓)
,但要以另一种方式工作。
因此,富人的责任可归结如下:第一,他应成为生活简朴无华的典范,杜绝招摇与奢侈。他只对亲属提供保证其合理需求的适当费用,并将此外的多余收入视为由他管理的信托基金。他应当精心筹谋,使这些钱对社会产生最佳效果——这样,富人就只是他的穷兄弟的代理者和信托人,用他管理上的超人智慧、经验和能力来为他们服务。这样要比穷人自己去管理钱财好得多。
这里我们将面对某些难于确定的问题,如:留给家人多少钱财才算合理适度?生活简朴无华的界限是什么?奢侈的标准又是什么?在不同的条件下当有不同的标准,对此难做明确回答,恰如我们不可能精确指出良好风度和高雅举止是由哪些动作组成的。这一类美德虽然尽人皆知却难下定义,而一旦有人违反,公众就会迅速有所反应,在财产上亦是同理。鉴别男女服饰是否高雅的规律在这里也是适用的。过分突出显眼便不合常规。如果有哪个家庭以好炫耀著称,住宅家什豪华,挥金如土,铺张成性,我们就不难判断出这个家庭的性质或文化素养。同样,无论富人们管理财富还是捐赠财富,我们都可以判断出这究竟是使用剩余财富还是滥用剩余财富,究竟是慷慨地帮助大众还是一味囤蓄家财、至死方休。这一判决由最明达的公众情绪作出。社会肯定会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且这种判断很少失误。
我们已经指明运用剩余财富的最佳途径。要想精明理财,人们必须认识到人类进步的一个严重障碍就是不分对象地大发善心。与其把富人的百万家私拿去鼓励懒惰、酗酒和下流行为,不如把这笔钱扔到海里,这于人类倒更有利。在今天所谓的慈善事业中所花费的每1000美元,恐怕有950美元花得不值得。这种花钱方式其实是在生产它所试图医治弥补的社会弊端。有个著述颇多的著名哲学家回顾道,某天他去朋友家做客,曾经路遇一个乞丐,并给了那人25美分。他对那个乞丐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乞丐会如何花掉这几文钱,不过他完全有理由怀疑这几文钱是否会用于正途。此人自称是赫伯特·斯宾塞的信徒,这位没头脑的慈善家以后不管捐多少钱恐怕也抵消不了他付出的25美分的负效果。他只是在寻求情感上的自我满足,使自己摆脱烦恼——尽管他在各方面都算是品行高洁,但这件事却可能是他一生中最自私最恶劣的行径。
济世救人之举主要应考虑如何帮助那些能自助者,向那些希望改善的人提供一定资助,使之得以如愿,或给那些有抱负的人以资助使之能成功。要去帮助,而不要或尽量少去包办一切。施舍从来不能改善个人或民族的处境。除了少数例外,那些值得帮助的人往往不主动求助于人。真正有价值的人除了在偶发事故的情况下根本无需人帮助。当然,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一定情况下需要真正的帮助,这一点谁也不会忽视。但由于彼此缺乏对别人情况的了解,这种个人对个人作出的有效帮助势必是有限的。在细心而热诚地去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人的同时,必须同样注意不去帮助那些不值得帮助的人。这样做的人才是真的改革者。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施舍行为如不是扬善而是奖恶的话,那就更糟糕了。
因此,富人们肯定应向彼得·库珀,巴尔的摩的伊诺克·普拉特,布鲁克林的普拉特、参议员斯坦福和其他人学习。这些人知道造福社会的最佳方式就是向社会提供一个促进人们上进的切实阶梯——建造公园和娱乐设施,以有利于民众的身心健康;安排艺术活动,让人们赏心悦目并提高审美能力;发展各式各样的公共设施,以改善人们的普遍环境——用这种最合算的方式将剩余财富返还给大众,给他们带来长期的利益。
贫富问题就将这样得以解决。积累法则依然如故,分配法则亦不受局限。个人主义继续存在,但百万富翁将只是穷人的信托人,暂时保管一大部分日益增加的社会财富。但他们要为社会管好用好这笔财富,使之发挥比公众管理更大的效益。人类的发展将这样进入一种新的精神境界,人们将清楚认识到,只有让那些有思想而且认真的人掌握财富,并为大众利益逐年运用财富,才称得上一种得当的处理剩余财富的方式。这一前景已为期不远了。但暂时还会有些骤然死去的大企业股东,由于来不及抽出他们生前的股份,只好被判作公共福利之用。然而他的同胞对这样的死者不存哀思。这种人生前理财营业,死后抛下百万家私,辞世之际却“无人哀泣,无人嘉奖,无人颂扬”。无论他把带不走的财富用于何处也于事无补,公众对这种人会作出如下判决:“死时越有钱,死得越丢脸。”
以我的观点,这种公众舆论本身就是财富的福音。如果我们遵循它,我们肯定能在某一天解决贫富对立问题,并给世界带来“太平盛世,人性归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