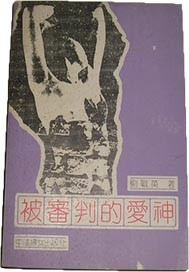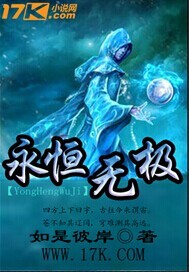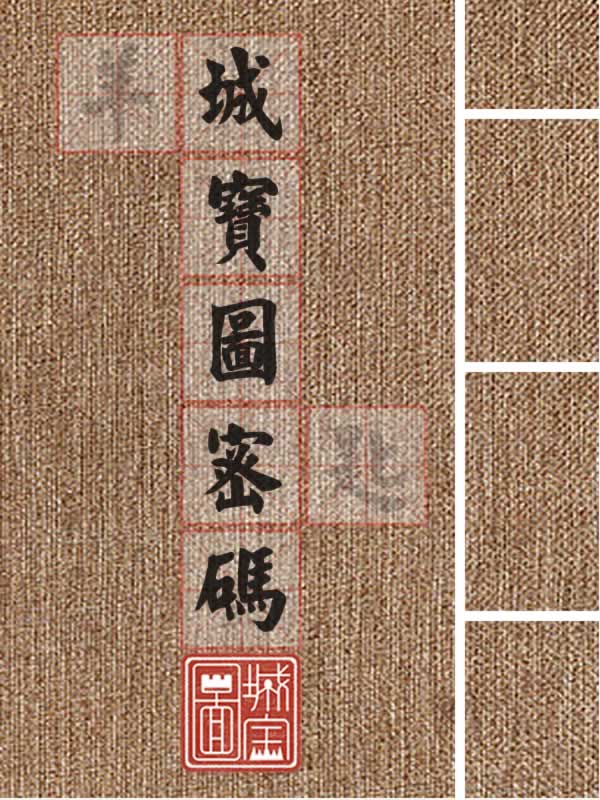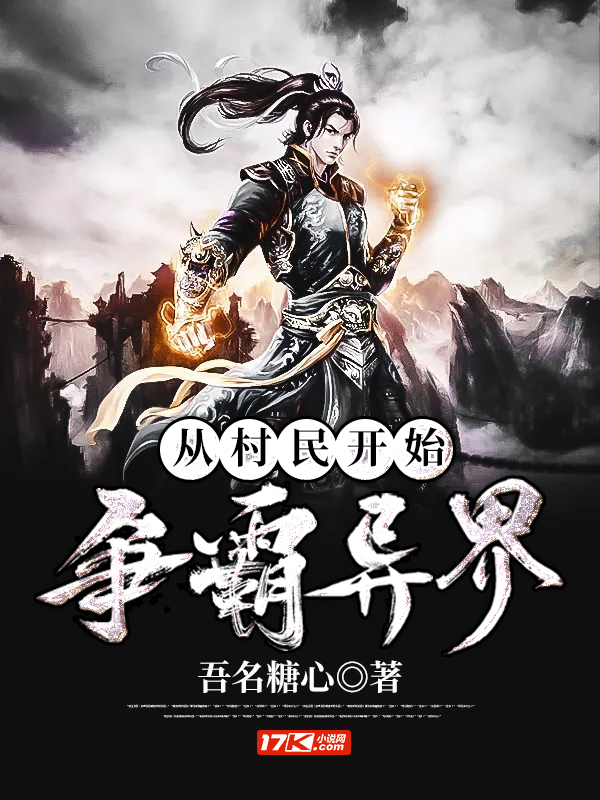解析一个费无忌,我们便约略触摸到了小人的一些行为特征,但这对了解整个小人世界,还是远远不够的。小人,还没有被充分研究。
我理解我的同道,谁也不愿往小人的世界深潜,因为这委实是一件气闷乃至恶心的事。既然生活中避小人惟恐不远,为何还要让自己的笔去长时间地沾染他们呢?
但是回避显然不是办法。既然人们都遇到了这个梦魇却缺少人来呼喊,既然呼喊几下说不定能把梦魇暂时驱除一下,既然暂时的驱除有助于增强人们与这团阴影抗衡的信心,那么,为什么要回避呢?
我认为,小人之为物,不能仅仅看成是个人道德品质的畸形。这是一种带有巨大历史必然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值得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共同注意。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的充分呈现,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专制和社会下层低劣群体的微妙结合,结合双方虽然地位悬殊,却互为需要、相辅相成,终于化合成一种独特的心理方式和生态方式。
封建人治专制隐秘多变,需要有一大批特殊的人物,他们既能诡巧地遮掩隐秘又能适当地把隐秘装饰一下昭示天下,既能灵活地适应变动又能庄严地在变动中翻脸不认人,既能从心底里蔑视一切崇高又能把封建统治者的心绪和物欲洗刷成光洁的规范。这一大批特殊的人物,需要有敏锐的感知能力,快速的判断能力,周密的联想能力和有效的操作能力,但却万万不能有稳定的社会理想和个人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上的小人实在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对一种体制性需要的填补和满足。
《史记》中的《酷吏列传》记述到汉武帝的近臣杜周,此人表面对人和气,实际上坏得无可言说。他管法律,只要探知皇帝不喜欢谁,就千方百计设法陷害,手段毒辣;相反,罪大恶极的犯人只要皇帝不讨厌,他也能判个无罪。他的一个门客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他反诘道:“法律谁定的?无非是前代皇帝的话罢了,那么,后代皇帝的话也是法律,哪里还有什么别的法律?”由此可见,杜周固然是糟践社会秩序的宫廷小人,但他的逻辑放在专制体制下看并不荒唐。
杜周不听前代皇帝只听后代皇帝,那么后代皇帝一旦更换,他又听谁呢?当然又得去寻找新的主子仰承鼻息。照理,如果有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相对稳定的行政构架,各级行政官员适应多名不断更替的当权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在习惯于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政治恶斗的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每一次主子的更换就意味着对以前的彻底毁弃,意味着对自身官场生命的脱胎换骨,而其间的水平高下就看能否把这一切做得干净利落、毫无痛苦。闭眼一想,我脑子里首先浮现的是五代乱世的那个冯道,不知为什么我会把他记得那么牢。
冯道原在后唐闵帝手下做宰相,公元九三四年李从珂攻打唐闵帝,冯道立即出面恳请李从珂称帝,别人说唐闵帝明明还在,你这个做宰相的怎么好请叛敌称帝?冯道说,我只看胜败,“事当务实”。果然不出冯道所料,李从珂终于称帝,成了唐末帝,便请冯道出任司空,专管祭祀时扫地的事,别人怕他恼怒,没想到他兴高采烈地说:只要有官名,扫地也行。
后来石敬瑭在辽国的操纵下做了“儿皇帝”,要派人到辽国去拜谢“父皇帝”,派什么人呢?石敬瑭想到了冯道,冯道作为走狗的走狗,把事情办妥了。
辽国灭后晋之后,冯道又诚惶诚恐地去拜谒辽主耶律德光,辽主略知他的历史,调侃地问:“你算是一种什么样的老东西呢?”冯道回答:“我是一个无才无德的痴顽老东西。”辽主喜欢他如此自辱,给了他一个太傅的官职。
身处乱世,冯道竟然先后为十个君主干事,他的本领自然远不只是油滑而必须反复叛卖了。被他一次次叛卖的旧主子,可以对他恨之入骨却已没有力量惩处他,而一切新主子大多也是他所说的信奉“事当务实”的人,只取他的实用价值而不去预想他今后对自己叛卖的可能。
我举冯道的例子只想说明,要充分地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一个人的人格支出会非常彻底,彻底到几乎不像一个人。与冯道、杜周、费无忌等人相比,许多忠臣义士就显得非常痛苦了。忠臣义士平日也会长时间地卑躬屈膝,但到实在忍不下去的时候会突然慷慨陈词、拼命死谏,这实际上是一种“不适应反应”,证明他们还保留着自身感知系统和最终的人格结构。后世的王朝也会表扬这些忠臣义士,但这只是对封建政治生活的一个追认性的微小补充,至于封建政治生活的正常需要,那还是冯道、杜周、费无忌他们。他们是真正的适应者,把自身的人格结构踩个粉碎之后获得了一种轻松,不管干什么事都不存在心理障碍了。人性、道德、信誉、承诺、盟誓全被彻底丢弃,朋友之谊、骨肉之情、羞耻之感、恻隐之心都可一一抛开,这便是极不自由的封建专制所哺育出来的“自由人”。
这种“自由人”在中国下层社会某些群落获得了呼应。我所说的这些群落不是指穷人,劳苦大众在物质约束和自然约束下,不能不循规蹈矩,并无自由可言,他们的贫穷不等于高尚却也不直接通向邪恶;我甚至不是指强盗,强盗固然邪恶却也有自己的道义规范,否则无以合伙成事,无以长久立足,何况他们时时以生命作为行为的代价;我当然也不是指娼妓,娼妓付出的代价虽然不是生命却也是够痛切的,在人生的绝大多数方面,她们都要比官场小人贞洁。与冯道、杜周、费无忌这些官场小人真正呼应得起来的,是社会下层的那样一些低劣群落:恶奴、乞丐、流氓、文痞。
除了他们,官场小人再也找不到其他更贴心的社会心理基础了,而恶奴、乞丐、流氓、文痞一旦窥知堂堂朝廷要员也与自己一般行事处世,也便获得了巨大的鼓舞,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最有资格自称“朝中有人”的皇亲国戚。
这种遥相对应,产生了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就像磁体的两极之间所形成的磁场,一种巨大的小人化、卑劣化的心理效应强劲地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上有朝廷楷模,下有社会根基,那就滋生蔓延吧,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呢?
那么,就让我们以恶奴型、乞丐型、流氓型、文痞型的分类,再来看一看小人。
恶奴型小人:
本来,为人奴仆也是一种社会构成,并没有可羞耻或可炫耀之处。但其中有些人,成了奴仆便依仗主子的声名欺侮别人,主子失势后却对主子本人恶眼相报,甚至平日在对主子低眉顺眼之时也不时窥测着掀翻和吞没主子的各种可能,这便是恶奴了,而恶奴则是很典型的一种小人。谢国帧先生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中有一篇《明季奴变考》,详细叙述了明代末年江南一带仕宦缙绅之家的家奴闹事的情景,其中还涉及到我们熟悉的张溥、钱谦益、顾炎武、董其昌等文化名人的家奴。这些家奴或是仗势欺人,或是到官府诬告主人,或是鼓噪生事席卷财物,使政治大局本来已经够混乱的时代更其混乱。为此,孟森先生曾写过一篇《读明季奴变考》的文章,说明这种奴变其实说不上阶级斗争,因为当时江南固然有不少做了奴仆而不甘心的人,却也有很多明明不必做奴仆而一定要做奴仆的人,这便是流行一时的找豪门投靠之风。本来生活已经挺好,但想依仗豪门逃避赋税、横行乡里,便成群结队地签订契约卖身为奴。“卖身投靠”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孟森先生说,前一拨奴仆刚刚狠狠地闹过事,后一拨人又乐呵呵地前来投靠为奴,这算什么阶级斗争呢?
乞丐型小人:
因一时的灾荒行乞求生是值得同情的,但当行乞成为一种习惯性职业,进而滋生出一种群体性的心理文化方式,则必然成为社会公害,没有丝毫积极意义可言了。乞丐心理的基点,在于以自秽、自弱为手段,点滴而又快速地完成着对他人财物的占有。乞丐型小人的心目中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他们认为世间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又都是自己的,只要舍得牺牲自己的人格形象来获得人们的怜悯,不是自己的东西有时可能转换成自己的东西。他们的脚永远踩踏在转换所有权的滑轮上,获得前,语调诚恳让人流泪,获得后,立即翻脸不认人。
乞丐一旦成群结帮,谁也不好对付。《清稗类钞·乞丐类》载:“江苏之淮、徐、海等处,岁有以逃荒为业者,数百成群,行乞于各州县,且至邻近各省,光绪初为最多。”最古怪的是,这帮浩浩荡荡的苏北乞丐还携带着盖有官印的护照,到了一个地方行乞简直成了一种堂堂公务。行完乞,他们又必然会到官府赖求,再盖一个官印,成为向下一站行乞的“签证”。官府虽然也皱眉,但经不住死缠,既是可怜人,行乞又不算犯法,也就一一盖了章。由这个例证联想开去,生活中只要有人肯下决心用乞丐手法来获得什么,迟早总会达到目的。
流氓型小人:
当恶奴型小人终于被最后一位主子所驱逐,当乞丐型小人终于有一天不愿再扮可怜相,当这些人完全失去社会定位,失去哪怕是假装的价值原则之后,他们便成为对社会秩序最放肆的骚扰者,这便是流氓型小人。
《明史》中记述过一个叫曹钦程的人,明明自己已经做了吴江知县,还要托人认宦官魏忠贤做父亲,献媚的态度最后连魏忠贤本人也看不下去了,把他说成败类,撤了他的官职,他竟当场表示:“君臣之义已绝,父子之恩难忘。”不久魏忠贤阴谋败露,曹钦程被算做同党关入死牢,他也没什么,天天在狱中抢掠其他罪犯伙食,吃得饱饱的。这个曹钦程,起先无疑是恶奴型小人,但失去主子、到了死牢,便自然地转化为流氓型小人。我做过知县怎么着?照样敢把杀人犯嘴边的饭食抢过来塞进嘴里!你来打吗?我已经咽下肚去了,反正迟早要杀头,还怕打?——人到了这一步,说什么也多余的了。
流氓型小人比其他类型的小人显得活跃,他们像玩杂耍一样在手上交替玩弄着诬陷、造谣、离间、偷听、恫吓、欺诈、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引蛇出洞、声东击西等等技法,别人被这一切搞得泪血斑斑,他们却谈笑自若,全然不往心里放。
流氓型小人乍一听似乎多是年轻人,其实未必。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时间积累的恶果,因此有不少倒是上了一点年岁的。谢国桢先生曾经记述到明未江苏太仓沙溪一个叫顾慎卿的人,做过家奴,贩过私盐,也在衙门里混过事,人生历练极为丰富,到老在乡间组织一批无赖子不断骚扰百姓,史书对他的评价是三个字:“老而黠”,简洁地概括了一个真正到位的流氓型小人的典型。街市间那些有流氓习气的年轻人,不属于这个范围。
文痞型小人:
当上述各种小人获得一种文化载体或文化面具,那就成了文痞型小人。我想,要在中国历史上举出一些文才很好的小人是不困难的。宋真宗钓了半天鱼钓不上来正在皱眉,一个文人立即吟出一句诗来,“鱼畏龙颜上钓迟”。诗句很聪明,宋真宗立即高兴了。可怕的是,他们也能以同样的聪明和快捷,用文化工具置人于死地。
文痞其实也就是文化流氓,与一般流氓不同的是他们注意修饰文化形象,知道一点文化品格的基本经纬,因而总要花费不少力气把自己打扮得慷慨激昂。作为文人,他们特别知道舆论的重要,因而把很大的注意力花费在谣言的传播上。在古代,造出野心家王莽是天底下最廉洁奉公的人,并把他推上皇帝宝座的是这帮人;在现代,给弱女子阮玲玉泼上很多脏水而使她无以言辩,只得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自尽的也是这帮人。他们手上有一枝笔,但几乎没有为文化建设像模像样地做过什么,除了阿谀就是诽谤。他们脚跨流氓意识和文化手段之间,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特别具有伪装,也特别具有破坏性,因为他们把其他类型小人的局部恶浊,经过装潢变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污染。
影响虽大,但他们的人数并不多,这可能要归功于中国古代的君子观念对文化队伍的渗透。历来许多文人有言词偏激、嘲谑成性、行为不检、表里不一等缺点,都不能目之为文痞,文痞的根本特征在于经常地用文化手段对大量无辜者进行故意的深度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