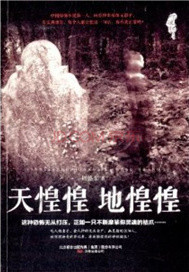历代理论家大多承认,在艺术中,真实感比真实重要,感觉上的“自然”比真实重要,感觉上的合情合理,也比真实重要。因此,“自然”和“情理”往往作为一种感觉性的命题,与历史真实对峙。
莱辛
写一部从真实事件中取材的戏,常常会产生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违背了事实真相;二是不违背事实真相但看起来却不大合理、不大自然。这两种问题,究竟哪一种更严重、更不能容忍呢?莱辛认为是后一种,他说,天才会犯前一种错误,却不会犯后一种错误。
观众的真实感具有很大的威力,既代替不了,也伪饰不了。有的剧作家在幕前声明“以下演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企图以历史真实来引诱观众的真实感,结果,在感受效果上并无补益。一个真实的事件到了剧场里,极有可能变成“不真实的真实事件”。即使是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来看戏,当他们以观众的身份坐下来的时候,审美感知立即会笼罩一切,丰富而确实的历史知识并不能代替他们的剧场真实感。
17世纪的法国官方理论家沙坡兰写过一篇批评高乃依悲剧《熙德》的文章,历来被戏剧界所诟病,但那篇文章对观众的剧场真实感问题发表了很不错的意见。沙坡兰说:
史诗和剧诗的目的既在使听众或观众得益,也只有用近情理的事而非实事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它用这个工具更能把人们引导到这个目的地,因为人们容易接受它;反之,实事却会显得奇特而令人难信,人们反而会把它看作非真而不愿置信,因此反而不容易达到目的。
只有近情理的东西才不遇到听众和观众方面的抗拒。
沙坡兰的这些话已触及审美心理学中的重要课题。启蒙主义者狄德罗是反对沙坡兰所立足的整个美学基地的,但他在观众真实感的问题上却得出了与沙坡兰相近似的结论。他揭示了观众在剧场里往往对历史真实十分漠然却对天然事物十分敏感的有趣现象,并为这种现象找到了社会心理方面的依据:
观众并非永远要求真实。当他认假作真的时候,可以历几百年而不觉察,可是他对天然的事物还是敏感的;当他一旦获得印象,就永远不会把这种印象丢掉。
那么,真事能不能入戏呢?也能,但必须先看一看,这件真事能不能使观众感到真实。有些真事,发生的方式和过程恰合乎人们获得真实感的心理过程,那就成了“天造地设”般的良好题材。莱辛说,剧作家之所以有时也需要利用一段真实的历史,“并非因为它曾经发生过,而是因为对于他的当前目的来说,他无法更好地虚构一段曾经这样发生过的史实”,“为此而花费许多时间去翻看历史书本,是不值得的”。
艺术家看中的,不是这件事本身,而是这件事发生的方式。但是,即使是以最佳方式发生的真实事件,艺术家仍要进行加工改造,使之具有更内在的可信性。
例如,真实事件常常不可能把有关人物的内在性格显现出来,结果难免使真实感受到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莱辛那句颇为令人费解的话显现出了真理性:人物的性格,使事实变得更真实。这里所说的真实,无疑是指真实感。
荀慧生的演出
剧本为真实感的取得提供了文学基础,而这种真实感要直接地出自观众的感知,还有赖于演员。一个好演员能使某些真实感较差的剧作在舞台上焕发出充分的真实感。有一位剧评家在看了京剧艺术家荀慧生演出的《勘玉钏》和《元宵迷》
之后曾发了这样一番议论:
两出戏,传奇性都很强,孤立地读剧本,甚至会产生如何才能合情理的担忧,担心那些乍看上去未免轻巧的桥,承担不了许多破空而来的开阖驰骤。但,只消进入剧场,只消荀先生一出现在舞台上,他的人物塑造立即吸引了你,一切看上去迂徐曲折的转角,尽皆畅通,一切偶然在他血肉丰满的性格刻画之下,都化着了必然。
这位剧评家在读剧本和看戏时的两种不同直感,正说明了演员的表演对于观众获得真实感的重要意义。
在欧洲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相信,全部舞台艺术的使命就在于用尽可能真实化的手段把剧本提供的情境再现出来,让观众产生一种“感同身受、身临其境”的幻觉。幻觉,是真实感的全面积贮状态,是真实感的最高形式。然而,不仅东方的戏剧家们历来不赞成这种观念,而且在欧洲的戏剧家中间,异议也越来越多。不少理论家认为,一心一意制造幻觉的表演并不是优秀的表演,陷于幻觉而不能自拔的观众也不是好的观众。
1822年8月,法国巴尔梯摩剧场上演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演到第五幕奥赛罗要动手扼杀被冤枉了的妻子苔丝德蒙娜的时候,一个正在剧场值勤的士兵朝台上开了一枪,打伤了扮演奥赛罗的演员的手臂。这种事情,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发生过。如果剧场真实感以产生幻觉为目标,那这个开枪士兵就要算是最好的观众了,因为他完全进入了幻觉。
《奥赛罗》剧照
司汤达借这件事得出结论:戏剧即使能给观众造成某种幻觉,那也是一种不完全的幻觉。忘乎所以的完全幻觉万一产生,也只是转瞬即逝。绝大多数观众完全清楚他们自己坐在剧场里,在看一件艺术品的演出,而不是在参与一件真事。马丁·艾思林赞同司汤达的意见,认为戏剧所制造的那种富于真实感的假象和幻觉,不应该是完全而又纯粹的。那个开枪士兵不是好观众,好观众不会那样一意孤行。艾思林说:“在看《奥赛罗》时,我们为主人公的不幸深深地感动:可是就在他倒下了而我们热泪盈眶的那一刹那间,我们也会几乎像患了精神分裂症似的自言自语:‘奥利弗的停顿多么漂亮!他仅仅是一抬眉毛,就那么出色地达到了这个效果。’”
司汤达
这就是说,观众在剧场中处于一种双层次的重叠感知之中。
有的表演艺术家能以高超的演技引导观众对角色获得充分的真实感,甚至使他们忘记演员的存在。巴尔梯摩剧场演奥赛罗的那位演员的演技不得而知,但像意大利女演员爱列昂诺拉·杜丝那样善于制造幻觉的表演艺术家确实是存在的。据记载,1891年杜丝曾到俄国演出,当时一位俄国观众说,她从出台的第一分钟开始,“女演员一下就消失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女人施展着女性的一切威风”,“仅在出场的几分钟之后,就能迫使您忘了您主要是来看看名人的,或者说,就能把您吸引到所扮演的人物的生活里去,而把一切评论性的分析、想法通通撇在一边。至少对我来说,这种表演是立刻和直到剧本末了(只有不多几处例外)都留下这种印象的”。在演剧艺术相当发达的彼得堡,杜丝的表演引起如此虔诚的惊叹,可见这样的表演在世界剧坛的视野内也极为罕见。更多的情况正恰与彼·温堡的用语相反:不是“不多几处”使观众想到了这是在演戏,而是“不多几处”使观众忘记了这是在演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