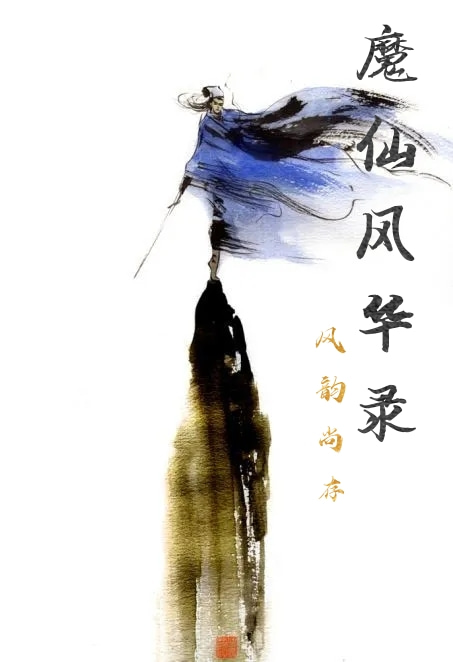同样由于心理美学上的原因,喜剧美不适合观众的情感投入。
观众要对审美对象保持轻松而畅快的笑,必须使自己处于一种“心理安全”状态。也就是说,审美对象不牵涉审美主体。这就要求观众一直处于俯视的高位之上,避免缩短其间的距离。
为了实现观众的心理俯视,喜剧艺术家总会对喜剧人物进行夸张、变形、丑化、傻化。一旦产生感动,哪怕仅仅是同情,俯视的距离就缩短了,喜剧美也就随之减少。
俯视心理维护了人们对自身正常状态的确认,这是件大事,为此,不惜牺牲一系列具体的合理性。对此,可以随手举一个莫里哀的例子来说明。莫里哀在《吝啬鬼》中写尽了爱财如命的阿巴贡的种种丑态,但是,阿巴贡后来发现,自己放高利贷的对象居然是自己的儿子,最后丢失金币箱也与儿子有关。照理,他面对儿子应该说几句动气的话:“我这么老了,为什么还要存钱?还不是为了你!”这本是合乎寻常情理的,但是,如果他这么一说,观众也就同情他了,很难再嘲笑他,喜剧美也就结束。因此,莫里哀没让他这么说,反而让他不近情理地保持着变态。这种表面上的不合理,却维持了观众对阿巴贡的俯视高度,随之也维持了对吝啬这种人类通病的俯视高度。
显然,这又是心理美学的默默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