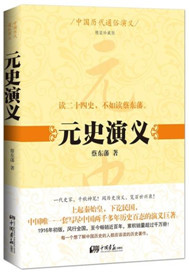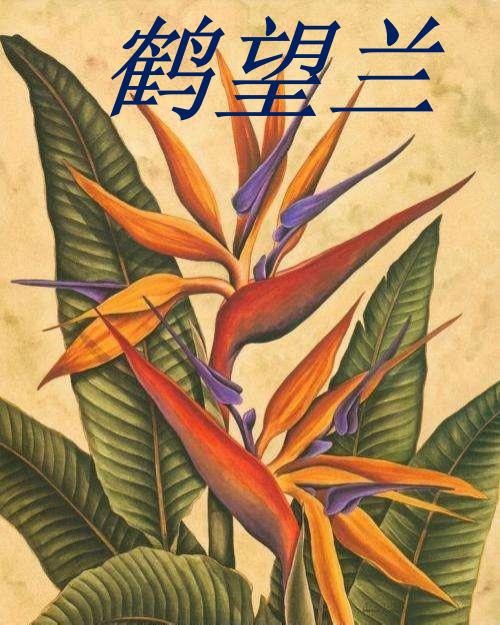足足一个星期了,思平一放了学就往医院跑。
思平的奶奶住院了。
从学校到医院有四站路,思平往常是坐车去的。可是今天老师拖了堂,思平奔到汽车站,那里有黑压压的一大片下班工人。思平挤不上车,就把书包往背后一甩,小步跑了起来。
冬天的夜色来得早,街上已经显得有点灰蒙蒙了。思平跑跑走走,额上沁出了细小的汗珠子。
他必须在五点钟前赶到奶奶的病房,替下妈妈,让妈妈回家去烧晚饭。妈妈吃了饭还要去上夜班。
而爸爸,他的研究所在浦江东边的郊区,搭车摆渡即使再顺利,也得过了七点才能赶到医院。
从五点到七点,是思平陪伴奶奶的时间。
思平急匆匆地跑着,横穿马路时,差点撞上了一辆自行车。那骑车人绕了个大“S”形,才算没有倒下。既然没出事,思平就跑开了。背后传来他的嚷嚷声。肯定是在骂人。管它呢!五点钟快到了。
自行车,又是自行车,哪来这么多的自行车!一个星期之前,奶奶就是被自行车撞了一下,仰面跌倒,后脑着地,当场就昏了过去的。
她住的是“重危病房”。那个撞倒了奶奶的窦叔叔,一听说奶奶生命垂危,嘴唇刷地白了。妈妈哭出了声。素来不动声色的爸爸,用手指拭掉了眼角上两颗大大的泪珠。
已经看见医院大楼了,思平放慢了脚步。他觉得浑身燥热,棉毛衫裤粘粘地贴在身上,唉,这一身棉毛衫裤穿了快两个星期了。要在以前,奶奶早就会催着思平换下了。
干净的棉毛衫裤是放在哪儿的?思平不知道。爸爸自然更不知道。他只知道资料卡片放在哪一格书架上。妈妈也向来是管洗不管收,连她自己换衣服也要喊奶奶:“妈呀,我那双毛巾袜子您收哪儿啦?”
今天一大早,思平又听见她在喊:“妈呀,我那……”她马上就住了口。不一会儿,她在希呼希呼地吸鼻子,一定是又哭了。
是的,奶奶不在家里,家里的人才感到,没有了奶奶,生活一下子就失去了平衡。
一个多星期之前,思平放了学还可以钻到校阅览室去,翻上一个多钟头的《少年文艺》呀、《萌芽》呀。思平还喜欢慢吞吞地荡马路;走过集邮公司时,看看有没有新发行的小型张。天黑了,思平才回到家里。奶奶总是一面端出香喷喷、热乎乎的饭菜来,一边叨咕着:“哎呀,现在的学生子,读书真辛苦呀,真比上班的人还要忙呀!”
思平使劲咽了一口唾沫,他感到有点饿了。书包里还有半个面包,是早上吃剩的。等到了病房,替下了妈妈,就找杯开水将就着吃吧!
妈妈不在,坐在奶奶病床旁的是那位撞倒了奶奶的窦叔叔。他正出神地盯着输液管,思平走到他跟前,他才发现。
“呵,你来了,你快来看看,”他一面指指玻璃管,一面紧张地说,“怎么滴得这么慢,是不是不滴了?”
思平大吃一惊,他屏住气往玻璃管里看,咳,这窦叔叔真是瞎七八搭!那透明的液体,正在缓缓地、均匀地滴着,完全正常嘛!
窦叔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才说:“你妈妈先回去了。不过她今天调休,等一会就来。”说完,他拎起热水瓶,又带上了同病房一位中风瘫痪老太的吃过没洗的饭碗,走了出去。又大又重的翻毛皮鞋,震得地板都有点发抖。
“这小青年,良心蛮好的。”中风老太说,“就是有点毛手毛脚。”
尽管他把奶奶撞得这样,思平却不全怪他。
他天天一下班就来看奶奶。他对思平一家人都毕恭毕敬,一脸将功赎罪的神情。对十三岁的思平也这样,总是给他让座。
唉,思平实在实在受不了他那负疚的恭敬。
不能怪你的,叔叔!思平总想跟他说。
不怪我怪谁?他会问。
怪我!思平要告诉他。
那天是星期天,爸爸妈妈都出去了,家里只有奶奶和思平。奶奶在烧酱油蛋,当油下锅后,发现酱油用光了。“思平,帮奶奶去买点酱油来。”“晓得了,等我做好这道题。”“喔唷喔唷,你在做功课呀,好了好了,奶奶自己去买。”锅在炉子上坐着,蛋在锅里煮着,奶奶在马路上跑着,奶奶撞上了自行车……
世上的事哪有这么巧的?思平心里很内疚:要是我听奶奶的话,去买酱油;要是我晓得心疼奶奶,去买酱油;要是我向来肯帮奶奶做事,不推三阻四,去买酱油,那么,奶奶不是……
门通地一响,窦叔叔进来了。他先把洗干净的碗筷放到了老太的床边橱上,转身将热水瓶搁到思平面前,又从口袋里挖出几块“速溶咖啡”和巧克力糖来,“还没吃饭吧?先用这个充充饥吧!真对不起,害得你们全家都六神不安。”
“不,”思平忍不住说了,“不怪你的,我……”
窦叔叔摆摆手,打断了思平:“有些事,在法律上或许可以不负责任,可是在良心上,会留下一辈子悔恨的!”
思平紧紧地闭上了嘴。他怕自己一张嘴透气,眼泪或许就会滚出来。这个心直口快、毛手毛脚的叔叔,像是用他那只又长又粗的手指,拨动了思平心底上的一根低音弦,震得思平的心隐隐作痛。
窦叔叔走了,他还要去夜大上学。病房里静悄悄的,邻床的中风老太好象睡着了。这两天她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昨天晚上,护士已经把一块写有“危”字的红牌子挂到她的床脚边了。可是她的女儿却不以为然地说,不碍事的,死不了。思平瞧着她那张枯槁的脸,禁不住想:如果这老太真的死去了,她那个满口恶言毒语的女儿,会不会在良心上,留下一辈子的懊悔呢……
没人回答思平。窗外已经一片漆黑。
妈妈很快就来了,手里拎了一只大提包。
她的眼睛肿肿的,红红的,一见思平就告诉他:“今天上午,你奶奶差点……还好医生抢救得快……”
她没有再说下去,只是低头给奶奶掖了掖被角,又依次看了看输液管和氧气瓶,然后从提包里拿出了一只饭盒子递给思平。
“我不想吃,”思平说,“我吃过面包了。”
“那就放着吧。”妈妈说着,又从提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只小钢精锅子。
“这是什么?”思平问。
“白木耳汤,给你奶奶吃的。”
“可是,奶奶……”思平想说,奶奶滴水不进,怎么吃呀?
“你奶奶喜欢吃白木耳……”妈妈话没说完,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低声说了一句:“我去热热这白木耳汤。”转身就走了出去。
邻床老太在说呓语,她那含含糊糊、断断续续的声音,像是在推动着一个长满了尖刺的仙人球,让这球慢慢地滚过思平的心头。
思平想起了那天妈妈买来白木耳后跟爸爸的一段对话。
“我最近胃酸多,不能吃甜食。你自己补补吧!”爸爸说。
“我不吃那东西。滑腻腻的,像鼻涕一样。”
“思平呢?”
“他像我,也不爱吃。”
“那就算了。”停了一停,爸爸又开了口,“妈最近好象有点咳嗽,给她熬汤喝,怎么样?”
“白木耳又不是咳嗽药水。”妈妈回答,“我已经从厂医室配来罗汉果止咳糖浆了,好几瓶呢!”
妈妈当然不是没有道理。喝了止咳糖浆,气管炎果真好了。
从那以后,思平总感到有一只长满了刺的仙人球常常滚过心头。
说实在的,妈妈平时对奶奶还是不错的。思平从小长到大,从来没有看见她们俩吵过嘴。奶奶进医院后,妈妈忙里忙外,瘦了一大圈,总是把奶奶收拾得千干净净的。奶奶躺在平平整整的被窝里,虽然脸色有点黄,面孔有点肿,但非常平静,好象在午睡一样,根本不像邻床老太,即使睡着了,也好象在听着她女儿的呵斥,一脸的苦相。
是的,除了思平之外,没人知道那白木耳的事。连奶奶自己也不知道。
如果奶奶知道了,妈妈只肯配几瓶公费的药水给她止咳,而不愿花钱买点白木耳让她补补,她还会这么平静地安睡着吗?她会不会也像那位老太一样,心中带着刀刻般的伤痕、脸上带着刀刻般的皱纹,露出一脸的苦相?
有些事,瞒一瞒,骗一骗,或许更好呢!
“可是,在良心上呢?”窦叔叔的话忽然在思平的耳边响了起来。
良心是瞒骗不过去的。
思平觉得自己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妈妈在奶奶昏迷不醒,危在旦夕时,居然去烧了一锅白木耳汤,为什么她又这么真心诚意地希望奶奶能醒过来,喝上一口她烧的白木耳汤?
这是因为,妈妈亏待过奶奶,伤痕留在妈妈的心上了!
思平忍不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仰头去看窗外,只见黑沉沉的夜空中,有几颗星星在闪烁,而那亮点愈看愈模糊了。他怕旁边的中风老太发现自己的眼泪,连忙把头伏到了奶奶的床边柜上。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这么遥远,却依然这么清晰。
“思平自己走,好吗?”
“不嘛,要奶奶抱。”
“思平乖,奶奶抱不动了,让奶奶背背思平,好不好?”
奶奶背上了思平,一只手扶着墙,一只手托住思平的屁股,慢慢地,慢慢地直起了身子。
这是思平第一次发现,原来奶奶的动作这么慢!
这又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好象不很遥远——
“奶奶,我的暑假作业本子呢?前两天还在五斗橱上看见过的。”
“哎呀,好象是有一本,一两个月了,皮也没有了……”
“不叫‘皮’,叫‘封面’!在哪儿呀?我们明早就要交了。”
“要命!我刚刚卖掉一叠废纸,会不会……”
“嗳哟一一我明早就要交了呀,你赔!你赔!我要你赔!”
奶奶奔下楼去,奔过马路,奔到废品回收站,才不一会儿,就夹着那本掉了封面的本子奔了回来,一头的灰,一脸的汗。
这是思平第一次看到,奶奶居然还能奔得这么快。
这些又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呵,很近很近好像就在眼前。
“思平,快吃饭了,帮奶奶抬抬桌子。”
“晓得了,让我把吉他的两根弦调调准。”
弦没调准,奶奶一个人拖动桌子的声音却响起来了……
“思平,快点,奶奶吃不消了!”
思平这次反应很快,因为他扭头一看,奶奶正在搬一只箱子,那箱子马上就要翻倒了。思平冲上去,用手一托,箱子就稳住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电视屏幕上,阿根廷队的马拉多纳踢进了一只球。
“都是你!都是你!人家看了一个多钟头了,就是为了看马拉多纳破门,现在好,也不晓得是怎么破的!”
“马拉破的门?这有什么好看的?”
“嗨!你啥也不懂!”
一声大吼,奶奶愣住了。整整一个下午,平时喜欢叨叨咕咕的奶奶,紧紧闭着嘴,没有说一句话。
思平第一次感到,奶奶的沉默中,透着那么多的困惑和滋心……
哦,这一件件、一桩桩的事儿,怎么平时都没在意,而在这静静的病房里,却一下子全都涌上了心头?
妈妈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把钢精锅放在桌上,盛了一魔白木耳。
她端起一碗满满的白木耳汤,走到了邻床老太的跟前。
“老太,”她喊她,“趁热尝一碗吧!”
话音未落,她啊呀一声,把碗一搁,转身就跑了出去。
思平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几个医生和护士已经冲进来了。
一阵忙乱之后,老太被一块好大好大的白布蒙上了。
思平呆呆地看着这一切。爸爸不知什么时候电已经来了,帮着护士移动着病房里的桌子、椅子什么的。
门口忽然响起了嚎啕声,哭声很凄惨,听得出来,是老太的女儿。
那个在病房里收拾的小护士,鼻子嗤了一声,说:“现在哭得伤心来,老太活着的时候,为啥不待她好一点!”
几乎是同时,思平和爸爸、妈妈,都回过头来看奶奶,看奶奶的脸,看奶奶头边的输液管,看那咝咝响着的氧气瓶。
哦,奶奶,您可千万千万要醒过来,要活下去呀!给思平,给爸爸妈妈,当然也给那个窦叔叔,弥补过失的机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