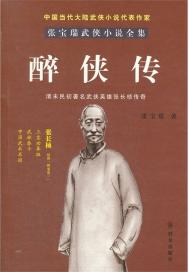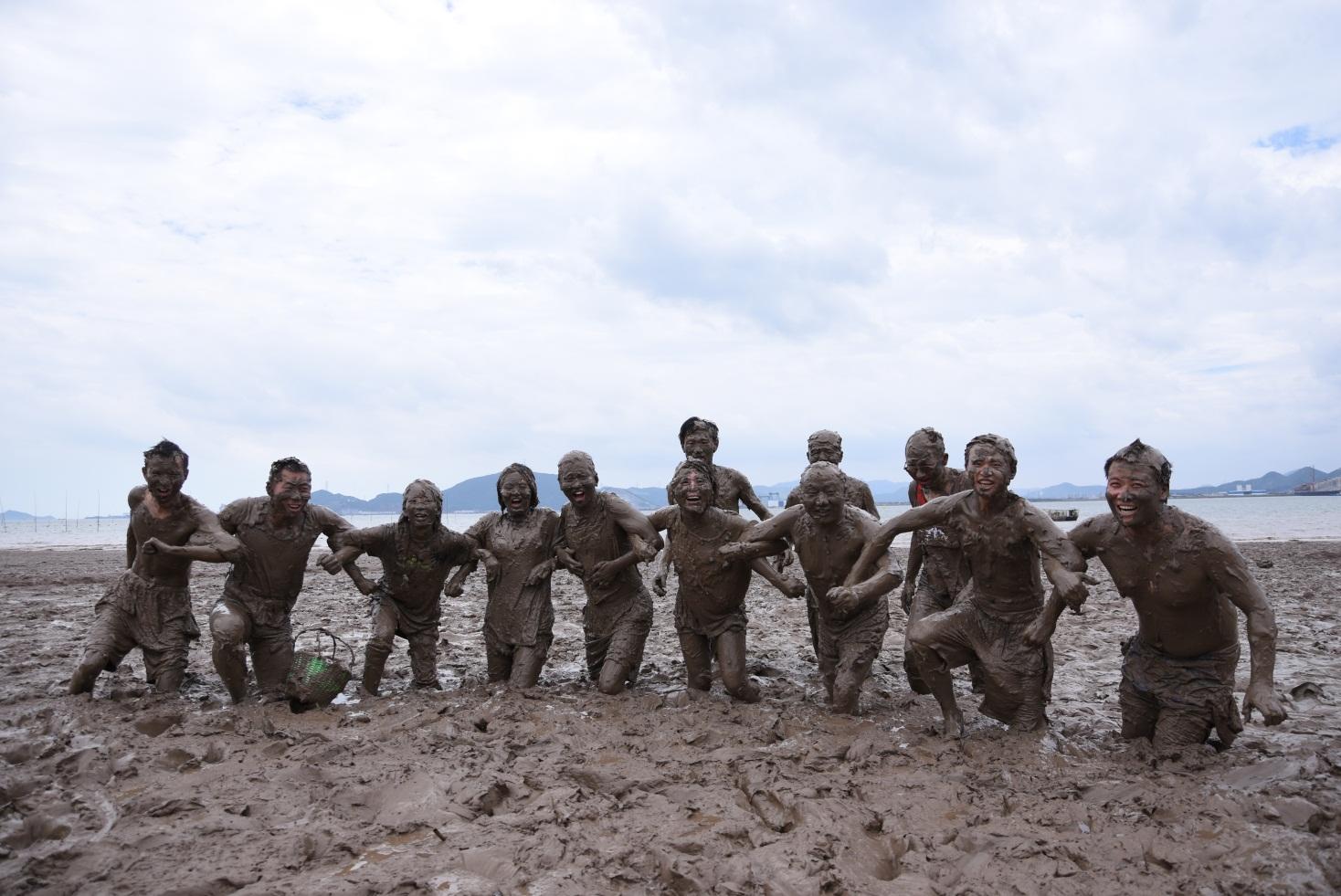都市供给我们可写的东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俞天白许多年前有过一本《大上海沉没》,反响不错,然后他就再来了一本《大上海崛起》,像是信手拈来似的。陈丹燕的上海老风情专题从“风花雪月”开始,至今已经“金枝玉叶”、“红颜遗事”地结成了一长串珠宝项链。
这些都是都市里的作家把都市生活作为写作的土壤,辛苦耕耘便不断地有了成功收获的实例。都市的土壤厚实,很肥。
当年我写《阿花》,但后来发现自己的生活资料库里有关都市女性命运的鲜货还很充沛,就出了个集子《上海女性》。再过若干年,因为长期生活于上海这个大都市,家庭的背景又令我格外地关注那些从事实业的工商业者,于是就写下了长篇《紫藤花园》。近年我开始对当下都市生活产生了表现的欲望,陆续拿出了一些中长篇,其中有《田教授家的28个保姆》、《田教授家的28个房客》及《99玫瑰》等。我自己的创作体会告诉我:都市的题材,都市的感受,对都市的探究,看来是够我写一辈子的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文学创作上的“重农轻城”观点很得势,很压迫人。当年全国只有一个作家逃过政治迫害的厄运、只有一部靠专写农村的作品才走上“金光大道”的那几年。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挺直了腰背说,我们喜欢写都市,或者我们只会写都市,或者我们以为写都市更足以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甚或我们觉得都市文学更能体现文学自身的特质,昭示着文学发展的走向……至少,我们是不会因此而被打人另册的了。
我总觉得都市与文学艺术有着最起始的依存关系。文学艺术处于原生态状态时都市尚未形成,比如我们的诞生自然是要远溯到人类的刀耕火种期的,那时候并无都市这种社会形态,但是,当文学进入成熟期并且作为独立于物质之外的精神产物,它在人类社会的生存和流传,却切实地借助过都市的形成和发展。且不说我们通常所指的中国文学之滥觞《诗经》,它那“风、雅、颂”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都已经浓浓地浸透了都市的精神,就说古罗马古希腊吧。那个雅典,该是最早形态的都市。有雅典这样的煌煌大都,有在那大都会里积聚着变化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背景,有都市里活生生地出演着的抢夺权利、金钱、美女(或者美男)的残酷的争斗,才会衍化出壮烈的《普罗米修斯》、诡谲的《俄狄普斯王》以及惨烈万端的《美狄亚》;而雅典的豪华的剧院所提供的舞台,雅典的热情的理解文学价值懂得文学欣赏的观众(或者读者),又是已经生成的作品的即时消费者、有效的传播者和遗产保存者。数千年以后的我们,还能拥有这么多的精神财富,谁能不说是得益于雅典这个都市的存在?
都市的生活是土壤,培育了文学,都市的需求是市场,催生了文学;都市的期望会推动文学的发展和变化。有都市在,文学永远也不会消亡。
生活在都市里的作家是很幸运的。他可以直接感受相对来讲比较先进的生活形态,其中包括先进的思想、先进的生产关系、先进的文化艺术、先进的思维模式、先进的消费观念,等等。我们不能不承认城乡区别,而这个区别的实质是先进程度的差异。我前不久见到一个新闻报道,上言一些经济学家在北京讨论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忧心忡忡地提出“中国是个城市短缺的国家”。他们搬出数据说,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是47%,而我国只达到了30%,这是一种“历史欠账”,社会若要进一步发展,那就是应该迅速加快都市化的进程。我从这篇报道中看到了都市文学发展的先进意义。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所指的“先进”,是一个总体性的、本质性的、而且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的角度而言的“先进”。我们不能从某些具体的方面、某个具体的问题、甚或以某些具体的个人来作局部的横向比较。比如农村自然环境比城市洁净优化,比如农民相对来说比较纯朴厚道,比如这位老张头虽然一字不识但他可比你们城市里的张董事长张主任张教授伟大高尚得多,诸如此类。我们只是说,在人类的历史上,都市的发展是文明发展的象征,都市是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最发达的滋生地、集中地和扩展地。身为作家能够与都市共在,他就已经先天获得了优越的创作条件,至于这份得天独厚的条件,能否转化成优秀的、杰出的、能够进入人类文化宝库而永久流传的成果,那则是要因人而异的了。
我相信文学的产销地——都市,命定地会造就最优秀的作家,虽然不是我,但一定是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