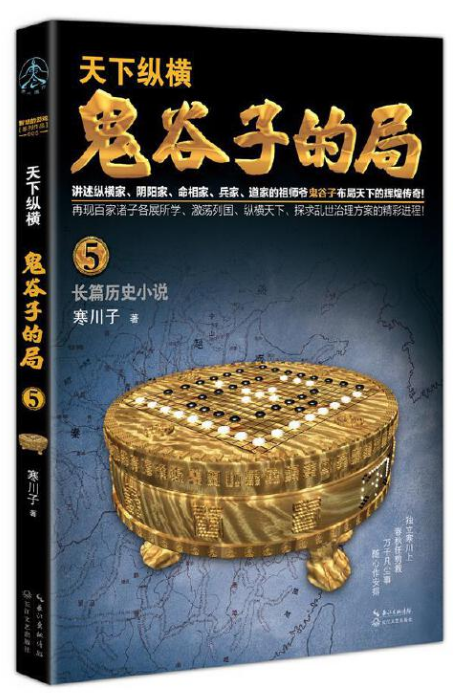请允许我把话扯远一点。我的祖籍是山东。据家谱所载,是燕王扫北时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而来的。有一说是同时迁来弟兄两人。但弟兄俩在路上干了一架,从此兄弟分家。到了山东地界后,一个在城东落了户,一个去城北扎了根。这样同一县里就有了两个邓庄。我是城东邓庄人,我们庄人都是一个祖宗的后代,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和城北邓庄则素无来往,是否有同族关系,本族人意见都不一致,倒是不认这门亲的多。不过近年台湾邓丽君小姐歌声传入大陆后情况有所改变。因为有情报说,邓小姐也是山东我县人氏。我们村是肯定没有这一户人家的,邓小姐若真是出身本县,就定是城北那个邓庄。有人觉得这光荣不能归他村独享,这个同宗还是认了好。
我村风水虽没造化出歌星,据说却出了位有钱的美国公民,按辈分我要叫他叔叔。
这位叔叔(我绝不是因为人家成了美国人就冒认洋亲,有家谱为证。)虽说出了五服,但他家和我家走得较近,小时候和他常在一块玩。他父母去世得早,由哥哥当家。他哥哥想由他这儿改变一下门风。就竭尽全力供他念书,在一段时间内,他和我称得上我村仅有的两大知识分子。因为我念完了四年初级小学,而还升了初中。他一升中学,就进城住校,我参加了八路军从此就很少见面了。1943年冬天,我们的队伍住在我村附近,我乘机回家探亲,碰上他放假回来娶媳妇。我去祝贺了一番。那一年他大概是十五六岁。此后部队南下,我和家人失去联系,当然也就再也没见过他,全国解放后我回家探亲,见到他的哥哥,问到他的情况。他哥哥叹了口气,悄悄告诉我说:“日本投降后,县城为中央军所占,城乡交通就全断了,全国解放前整个中学往南方撤退,他随着去了台湾。他媳妇就在结婚时和他过了5天日子,从那以后再没见过他。我女人已去世了,几个孩子就靠这个小婶给带看,她要再走了,这个家可怎么维持呢?”我认为这问题很可笑,便说:“解放台湾还不是一句话的事,这还能等多久吗?”
从此我再没回过家乡,也就再没打听过这一家人的事。
*****之后,家乡有人来北京办事,顺便来看我,说起家乡新闻。他们讲跑到台湾去的叔叔来信了,原来他早已离开台湾去美国了。现在很有钱,当了大资本家了。他想回来探亲,来信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叫他家里人给他去封信。他侄子问这信咋写法,公社干部研究好久,到现在还没回信呢!我问为什么没回信,现在开放改革,欢迎海外侨胞回来观光探亲。他们说不这么简单,他问家里有什么人?主要是问他女人还在不在。他女子以前倒是在的,二十多年一直没改嫁也没离婚,把几个侄子全拉扯大了。到文化革命时可过不下去了,从城市里来了一伙串连的红卫兵,说这村里隐藏着一个台湾国民党反革命家属,走资派一直包庇着她,要再不揪出来斗倒斗臭,那就连包庇她的人一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本家的人给她送了信,那女人连夜跑了,后来从外地来了封信宣布和邓家断绝一切关系。现在这信怎么写法呢,照实写影响不好,对外边人说这些,搞不好还要犯错误,不照直写,万一他真回来了,发现说的都不是实话就更不好。所以到现在还拖着。但是总拖着也不行,现在开放搞活,农村发展生产,也想引进外资,听说他很有钱,把财神爷放跑了也不合政策不是?
闲话说完,他们就走了,过了一年又有人来时,告诉我他侄子回了信,照直把真情告诉了叔叔,从此这人就再也没回过信。估计他收到信知道女人已离家,便不回来,大家很为放走这么个财神爷而遗憾。
1987年冬天,忽然我村支部书记和那位叔叔的亲侄儿一起半夜到我家来了,说是叔叔从美国回来了,今天到北京,他们来接他不知住在哪个饭店。问我可和他有过联系。我说我从没和他有过联系,根本不知道他回来的事。他们就要到一些饭店去询问,我说北京这么多饭店,如果没一点线索,怎能问到呢。我劝他们先住一夜,第二天一早买火车票去。他们听了我的话,不久就从山东写了信来,说是他们到家叔叔已经自己来到了,希望我回家乡去和他相会,还说这次回来带来不少钱。要在家乡作些投资,现在决定先为每个侄子修个养鱼池,以后还想买套房子,希望我去给他作作参谋。我工作走不开,只好谢绝了。
过了一个月,他回美国,路经北京时来电话约我见面。多年不见,为了给他选择礼品,我们夫妻还真费了点心思,后来选定一件景泰兰花瓶,心想他既是有钱的人,居住条件总会不错,送陈设品还算合用。
按他说的地址,我在招待所见到了他,一见面立刻都互相认了出来。他显得很疲惫,但还是很兴奋。穿得很朴素,行李也很简单。我问他为什么从第一次来信后过了这么久才回来,是不是因为那个婶婶走的事?他苦笑一下说:“那没什么,这次找着她了,我们谈了好久,她已经又结婚了,这样更好,我在台湾也已经又结过婚,两个孩子也都大了,不然也很难安排。”
问他何时到的美国?他说,他到台湾先服了几年兵役,退伍以后,就到一个建筑单位去当炊事员。那个公司承包了沙特阿拉伯的工程,他随着去了沙特阿拉伯。那里工程完了,他想回台湾也还是没办法,就设法去了美国。在那仍然当他的厨师,收入还不错,这次回来就为侄子们投资修建了两个鱼塘。还给他们留了点钱,多年没来,也请全村族里人喝了几顿。大家都很高兴。第二天他就要走,我们一起吃过饭就告别了。走前我把花瓶送他,他却说什么也不要。我见他态度坚决,只好作罢。我问他在美国的住址,以后若去美国,好去看他和没见面的婶子。他说他正要搬家,等住定了再写信告诉我。但给我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说如果我去美国,打这个电话就可以找到他。
这次到美国不久,我就打电话找他,接电话的是个中国妇人,我还以为是没见过的婶婶呢。说过几句话才知道,对方是个中国餐馆的女老板,她说这个人早已不在我这里做工了,不过有时还到我这儿来借宿。你留下电话号码好了,他来了我叫他回你电话。我问他家中电话号码,对方说他在美国没有安家。我只好把电话挂上了。心中颇为疑惑。是不是女老板听错名字,他在美国这么久,而且据说发了财,怎会没有个家呢?
到麻省后,我又请郑清茂帮我打了一个电话。清茂一看电话号码说,看来这地方距此不远,是一个电话局。电话仍是女老板接的,她说那位叔叔还没来过,我又把清茂和愁予的号码告诉了她,请她转告那位叔叔。13日下午4时我在愁予的系里讲演,中午才动身。早晨小陆就开车来接我到附近另一个大学区去玩玩。她刚用很便宜的价钱从同学手中买来部二手车,车还很新,不过她的驾驶技术还不大行,为此特请了一位中国同事来帮忙。她们先拉我到一个著名女校去参观,这里比起麻省大学,似乎要更清静正规些,建筑也更带古典味。街上几家商店,大多更带文化气息,因为在一家古董店我流连了过多时间,出来时已到了中饭时间。小陆一定要请我吃饭,她那同事又坚持请我吃中餐。这里没有中国餐馆,所以又拉我到数十里外另一个较大的镇上去。找到了一家颇不错的中国料理。菜做得很好,可是我心中有事,一是惦着这位叔叔的电话,一是看到这个镇与清茂家方向刚好相反。怕耽搁时间太多,误了下午讲课,结果饭菜滋味都没吃出来,真辜负了小陆和朋友一片好心,匆匆吃完,赶回清茂家时,果然他们已经坐在车内等我。清茂说:“4点钟讲课,我们绝不能迟到,现在真要争分夺秒,动作快些。”我从这个车门出来就钻进另一个车门,还没来得及和小陆告别,车就箭一般开了出去。
车子上了公路,平稳前进了,清茂才不慌不忙地说:“你那位本家叔叔来电话了,说晚上再往愁予处打电话。”我问他:“弄清楚他住在什么地方了吗?”清茂慢吞吞地说:“就是刚才你们吃饭的那个镇上。”过一会儿我们还要从这个镇处经过,不过来不及去找他了,我问他:“那镇上有几家中国料理?”他说:“大概只那一家。”我半天没说出话来,我想他就在我刚才吃饭的那个店里,怎么会就没见到呢?
这晚在愁予家,他果然来了电话。我很为与他失之交臂而遗憾,因为不能再见面了,所以电话谈了很长。我问他为什么来美国这么久没把家搬来?他才告诉我:“去年以前,他在美国一直是非法居留。不仅没能把家搬来,十多年来也没到台湾探过亲,只在几年前他太太以旅游名义到美国看过他一次。在美国他没有自己租房子,从来是给哪家干活就住在哪家店里,或是几个同样的流浪汉合租一间屋大家伙住。”他不接收我送的花瓶,原因就是他根本没有摆花瓶的地方。说到这里他停一会儿,勉强笑了一声又接着说:“我想你回去之后,是没必要把这些与家乡人道及的,离家这么久,家乡人都传说我发财了,对我有好多期望,我不愿让家里人失望。”我问他:“这样你能负担得了吗?是不是太苦了你?”他说:“那倒不至于,在美国挣钱还是容易,十多年我确实积蓄下了十几万美元,这点钱在美国不算什么,拿回去就很顶用。”我问:“你不还要养活台湾的家人吗?”他说现在那边不用花费太多了,两个孩子都已工作,他太太对他在家乡的作法也很谅解。美国纪念建国二百周年,实行大赦,去年起他已有了长期居留权,所以才敢回大陆去探亲,目前正办理入籍手续。他不会英语,美国**限期他学会英语,才准办理。为此他正在加劲补英语,等英语考及格,入了美国籍后许多事都好办了,工钱也会增加的。再干几年,再积点钱,就不打算在美国住了,大陆物价便宜。他想在家乡买所房子,和老伴回去养老。有十万美元就可度个舒服的晚年,这个目标不难达到。
我问他,在美国这么多年,怎么英语还不及格?他说:“非法居留打工的,哪有时间去学英语呀,何况成年累月都在后厨房干活,偶尔休息两天,只是在唐人街上转,也用不着英语,现在临阵磨枪,为了安心念书才租了间房子自己住,所以好久没上那家餐馆去,错过了我们见面的机会。”
放下电话,心中很不是滋味。家乡人都把他当成腰缠万贯的美国财主,为此有的人对他带有更多的羡慕和索取心愿,当然,按他所有确也可以算个美金万元户了,以我家乡标准,倒也该列入财主队中去。不过人们若都能听到昨晚那几个青年说的话,知道点非法移民在美国受的苛刻待遇,心情该会有点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