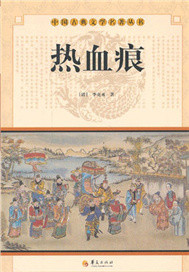这天晚上,举行了“中国诗歌之夜”。会场设在河边一个现代派造型的剧场里。台上挂着二道幕,白色幕布上涂上、也许是洒上或甩上去各种颜色,相当好看,就是有点乱的慌。幕布前边放了一排椅子,所有的中国人和要在这会上朗诵的演员全面对观众坐在椅子上,演员们用马基顿语朗诵郭沫若、艾青、田间、臧克家、严辰、萧三、邵燕祥、公刘、李瑛等人的诗。到会的中国人,邹荻帆、张志民、刘绍棠和我,各朗诵两首中文诗,由翻译先把译稿读一遍。
邹荻帆和张志民的诗,全是从南斯拉夫出的中国诗集中选出来的,已有译文。只有我和刘绍棠是专为这诗歌晚会现写的,现由大会雇用的翻译在我朗诵前由他口译一下。
我年轻时也写过诗,但从未被人们看上眼,我也明白自己诗才有限便以停写来藏拙。这次我写了两首与邹荻帆、张志民的诗一块朗诵,实在是打鸭子上架,为了不至出丑只得从表演上去找补。我上台演过戏,胆大皮厚,便把那诗分成高高低低的音调,快快慢慢的节奏,再配合上举手、昂头、作苦脸之类的动作。这样全武行地一闹果然剧场效果大增,为我鼓掌的人显然比给两位正式诗人鼓掌还用劲,两位诗人无可奈何。整个晚会都是在热烈友好气氛中度过的。马其顿姑娘们向每一个朗诵诗歌的人都献了花。原来传说只有现代派和朦胧诗才会受欢迎。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现实主义的诗,读到精彩的句子时人们也鼓掌。
我们的诗受到欢迎,自然和翻译的成功分不开,为我们口译的大会雇来的翻译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在北京学了几年汉语,学了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又娶了一个广东知青作妻子。他的汉语水平和聪明看来满够用。诗大概是译得不错的。但他也学了一身北京某些青年的那股吊儿郎当的油气。他没参加任何单位,只在作自由的职业翻译。
可他又和中国人挺友好。让他陪着买东西,决不会吃亏。他对中国的感情发自内心,很自然。
诗歌晚会散场后,马其顿对外联络委员会和文学界宴请中国代表团,这在大会是例外的待遇。其他代表团都由一个统一的欢迎派对招待。出席宴会的虽然只限于南中两国的人员,可人数很多,外交界首脑,各共和国作协**,大会主持人,全到了。宴会设在珍珠饭店的二楼大阳台上。下边露天酒吧正在跳交谊舞和民族舞,歌声笑声不绝于耳,俯身一看灯光闪耀,色彩缤纷,充满了快乐气氛。但这里跳舞的多半是30岁以上的人,没有太年轻的。地下室还有个迪斯科舞会,年轻人都上那儿去。一位作家领我到地下室看看。那里更热烈、更活泼。喊呀、鼓掌、跺脚应有尽有。有成对跳的,有单人跳的。单人独跳,自得其乐的人更为多些,我问领我来的那位作家:“你不跳吗?”他说他这年纪混在年轻人中未免有点惭愧了。其实他才四十来岁。我们***同志60岁还带头跳迪斯科呢,从这点看中国人自有走得远的地方。我当真认为宾雁的青年气概是十分可贵的。
宴会前一半连谈连吃很轻松、很友好,谈到中间,有人提出中间出版南斯拉夫诗集的话题来了,空气骤然紧张。诗稿的编辑者马其顿作协**杜多罗夫斯基、马其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马特夫斯基、塞尔维亚作协**布拉可维奇都发了言。据说今天郊游时他们知道了这本诗碰到困难。他们表示,如果是出于印刷、发行等技术上的原因可以理解,如果别的原因就很遗憾。马其顿人很难想象在他们的诗集里可以没有那位诗人的诗……他们措词、口吻不一,但观点一致、态度一致。每个人都谈得很长,我认真地听着,饭吃到午夜,快散了,他们想听听我有什么看法。我说:“感谢大家坦率、热情的发言,我相信凭我们的友谊,我们总会找到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来使诗集早日出版,今天晚了,明天再说。”
这天晚上回来,有人对我发出忠告。说我为这诗集作的考虑是多余的,应当按南方提供的书稿原样出版。另外方面如果也要求出本W诗人的书,也照出。叫他们去吵好了。中国作家不用管这些闲事,不必自找麻烦。
我很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和勇敢,但谢绝了他的独到建议。我觉得那不符合我们中国人交友之道,中国交友讲究与人为善,息事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