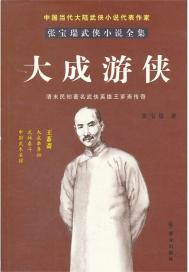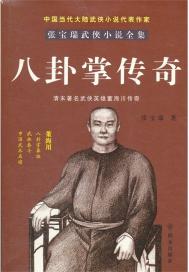一九五九年的仲秋,在莘塍公社出现与炎热的气候极为和谐的火热政治氛围。
震耳欲聋的锣鼓,迎风猎猎的彩旗,布满大街小巷的标语,载歌载舞的演出,一派热烈。
几天来,周雪影异常的繁忙和兴奋。
她被光荣地抽调到公社临时成立的文工团,用文艺节目动员和欢送广大支边青年到宁夏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和西北边疆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从年龄上讲她已经是三十二岁,可是无论从她的身段还是从她的容貌上看依然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加之她具有独特的歌舞天赋,在少女云集的文工团依然挑大梁,几个重要歌舞节目都由她领衔。
这种政治派生物的文艺演出,主题突出,感情热烈,时间性强,整天像赶场似的,不仅在公社演,还要到各个生产队去演,常常一天之内要演出三四场。
可是,周雪影明明很累却不觉得累。
此刻,她感受到的,是荣耀和自豪。
你想,文工团所挑选的一个个都是如花似玉的妙龄少女,惟独她是曾生育过七个孩子的女人。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公社的干部没有嫌弃她出身不好,张曼新的父亲既有历史污点又刚出了问题,仍叫她参加文工团,怎么不令她感到自豪呢?
因此,她为了不辜负公社领导的厚望,保障演出,晚上就住在距公社比较近的南垟幼儿园,连回华表村的工夫都没有了,对儿女们也顾不上照料了,可谓是满腔热情,全身心地投入。
这日,周雪影刚刚参加完演出回到宿舍,突然门外响起欢快的锣鼓声。
周雪影心里纳闷:没听说文工团有谁的孩子去支援宁夏呀,怎么把支边的荣誉证书敲锣打鼓地送到这里来了呢?
“周雪影同志,祝贺你的儿子参加到支援宁夏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行列!”
门外一声男人粗门大嗓的呼喊,把方才还困惑的周雪影愈发地震懵了,仿佛她坐着的不是木凳而是发射椅,倏然间把她的身子弹了起来,她忽地冲到门口,两个眼珠瞪得像对儿铜铃铛:“你们说什么?谁的儿子参加支边啦!”
来人在铿锵的锣鼓声中将荣誉证书交给周雪影,喜眉笑眼告诉她:“是你的儿子呀,不会错的,不信你看看证书上面写的名字。”
周雪影急忙拿过证书一看,“张曼新”三个字像三支箭镞带着骇人的寒光射到她的眼里,她感到眼前一黑,腿一软,立刻瘫坐在木凳上。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怎么可能呢?
这几天自己虽然没有回家,但也见过两次曼新呀,怎么没有听到他提起过想报名去宁夏的事儿呢?
莫非他想瞒着我,一个人偷偷地走?可是,这种事儿能瞒过初一,还能瞒过十五么?最后家长总是会知道的呀!
周雪影想。
然而,他明明知道这件事儿是谁也瞒不住的,却为什么要瞒着我这个做母亲的呢?是怕我知道了不同意他去?不,恐怕不会这么简单。因为,去宁夏支边是上面提倡的,又是一件光彩的事儿,他执意要去,谁敢硬行阻拦呢?那样岂不是犯了天条!
可是,不是为这个又不是为那个,到底是为什么呢?
周雪影越想思绪越乱。
他父亲刚刚离开华表去了三溪口村,怎么又发生这样预料不到的事儿呢?
莫非他恨我?
周雪影左思右想,觉得这件事儿非同一般。
她心里乱极了,好像胸口塞着一团麻线头,一时间摘不清,也理不出个头绪来。
她急得直哭。
她哭的原因,除了觉得张曼新年龄太小,满打满算才不过十五岁,个子又不高,看上去还像个孩子,一个孩子孤身一人到大西北怎么能吃得消呢?就说是生活苦点累点男孩子能够忍受得了,尤其他生性刚强,可衣服破了需要缝缝补补怎么办呢?万一再有个病有个灾的就更没有人伺候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周雪影觉得张曼新这种做法是对她这个当母亲的一种莫大的亵渎。
她受不了!
要劝劝他,能不去尽量还是不要去;即使他非要去不可,也要谈明白以后再让他痛痛快快地走。
怎么能让孩子心里结着个疙瘩呢?
于是,周雪影决定把张曼新叫来,与自己睡在一起,母子两个推心置腹地谈谈。
傍晚,天阴得像个水盆,不多时,下雨了。淅淅沥沥的雨丝,在微风的拂动下,疏密有致地斜织着,在天地间罩上一条大网。雨丝落在地上和轻叩屋顶的声音,嘈嘈切切,似春蚕吞噬桑叶一般,将白昼残余的光亮快速地咽到肚里。雨丝大一阵儿,小一阵儿,紧一阵儿,慢一阵儿,那绸缪的雨意,似失落者昏灯下无边的叹喟,又像独行者黑夜中惆怅的脚步,或许还像那血气少年铁马冰河的纵情驰骋,又仿佛是沦落人盘腿相视那无尽的倾诉,这几多伤怀,几多豪迈,几多感慨,交织成人世间多维的生活体验,又过滤出绵绵不断的人间情意。
周雪影与张曼新母子的交谈,伴随着这缠绵悱恻的雨意,铺展开来。
“曼新,是不是明天就要到公社里集中了?”
“是。”
“集中干什么?”
“学习。”
“要学习几天?”
“五天。”
谈话声单调枯燥,缺乏水分。
“曼新,你参加支边怎么不告诉妈一声呢?”
无语。
窗外,雨大一阵儿小一阵儿地下个不停,密密的雨脚斜斜地编织着,迷蒙、苍浑、冷瑟。
“你是怕我阻拦你?”
“嗯。”
“不光是因为这个吧?”
无语。
谈话声坚涩、沉闷、缺少回响。
“曼新,妈问你,你到底为什么去宁夏?”
“想改变一下环境。”
“这里的环境就不好?”
“不好。”
“为什么?”
“这里不是我张家呆的地方!”
“这话是谁说的?”
“我爸告诉我的。”
“他、他还说什么来着?”
“我爸说叫我逃命去吧。”
“你知道到了宁夏环境就好么?”
“到宁夏总有两种可能。”
谈话声渐进响亮急促,像雨大时叩击屋顶。
“曼新,妈再问你一句,你恨妈么?”
“恨。”
“妈什么地方值得你恨呢?”
“总打我。”
“还有呢?”
“您看不起我爸,不该叫我爸……”
谈话声骤然激烈、火爆,有些针锋相对。
“曼新,你说恨妈,妈不怪你。我们自从到了华表,妈打你的时候是多了一些。一来是你有时太调皮,二来妈操持这么多人的家务活,累了,脾气就不好,就拿你撒气,今天回想起来,妈很后悔。妈说这些,你能理解么?”
无语。
“妈再问你,你知道妈叫你爸一个人回青田究竟为了什么吗?”
无语。
“从表面看,自从你爸走后,妈的处境似乎好了一些了,其实,许多苦衷,妈只能有泪往肚子里咽呀!你们兄妹小,我又给谁去诉说呢?……”
谈话声哀婉凄恻,如泣如诉。
风声,雨声,谈话声,声声入耳,叩击着心胸,弹拨着周雪影与张曼新的母子感情之弦,在茫茫的夜空中交汇成湿漉漉的情丝,稠密而绵长。
张曼新在公社集训了五天,每天晚上周雪影都把他叫回来睡在自己身边,长谈不止。
张曼新呢,多年没有挨着母亲睡觉了,如今依稀感觉到母亲的体温,就像儿时依偎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幸福而陶醉,无形之中增加了一种天性中对母亲的亲近和爱戴。
周雪影觉得张曼新大了,又要马上离她而去到遥远的西北边陲,应该让他知道自己的一切,哪怕是过去不愿启齿的事情。她不仅感伤地讲述了在三溪口村遭受的种种磨难,也痛心地诉说了满心期冀自己的丈夫张式春成为一个顶门立户的强汉的失落,并悲痛地道出了为了儿女和妹妹周玲一家的前途硬着心叫张式春独自一人回青田的矛盾而痛苦的心理,直率地说出了近一两年来当地驻军有的军官向她求爱,她婉言谢绝,而且永远不会做出对不起自己丈夫和儿女们的事情来的心声,还进一步痛心地检查了自己由于内在的和外在的压力在很坏的心境下对张曼新过于严酷的打骂,可谓句句真情,满腔母爱呀。
“妈,您不要再说了!”一直闭着嘴唇的张曼新深深被母亲那情真意切的话语打动了,哭叫一声,猛地将头扎在周雪影的怀里。这种子对母的独特动作,足以说明张曼新对母亲原来的成见全部冰释和化解。
周雪影任凭泪水小溪似的流着,用手抚摸着性格耿直的儿子的头,既是聊以**又是劝解地叹息一声:“嗨,不说这些属于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还是说说你去宁夏的事情吧。”
“妈。”张曼新一扬下颏儿,用手给母亲拭去流淌的泪水,静心在听着。
“你在公社集训了五天,该听的大道理和宁夏的介绍也都听了,妈也说不出更多的什么。想来想去,还要嘱咐你两句话。”
“妈您说吧,我一定牢记在心。”
“第一,就是要时刻听党的话,尊重领导,与一起去的支边青年搞好团结。”
“嗯。”
“再有一点,去宁夏是你选择的,就不要再后悔。今后,无论遇到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都要咬牙挺住。我和你爸离你那么远,想帮你也帮不上。”
“知道了。”
“好了,明天你就要出发了,这几天一直没睡多少觉,今天早些睡吧。”
“哎。”
张曼新觉得心里熨帖极了,将头轻轻偎在母亲的胸前,闻着母亲温柔的鼻息,鼾然熟睡了,脸上不时泛出小儿般甜蜜的笑靥。
翌日,瑞安县城像开了锅似的锣鼓喧天,彩旗飞扬。
该县三千多名支援宁夏的青年列成军阵般的方队,在家乡父老的簇拥下,井然有序地乘坐解放牌汽车,要到金华会合其他县支援宁夏的青年,然后再乘坐闷罐式火车,直抵宁夏首府银川。
“曼新,记住,到了宁夏马上给妈来信!”当汽车快要开动时,周雪影看着在所有的支边青年中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儿子,扯起嗓门喊了一声,便急忙转过身去。
她不愿用眼泪为儿子送行。
虽然眼泪往往是女人的专利。
“知道了!”张曼新应一声,也蓦地回过身去。
他也不愿让母亲看到自己的眼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
“嘀——嘀——”
一字排列的汽车开动了。
马达的轰鸣声,发自千百个喉咙的送别声,惊天撼地。
张曼新的眼睛一眨不眨,上下嘴唇死死地闭着,目视着汽车前进的方向,牙帮骨堤坝般耸起。那特有的目光和特有的神态,似乎是在思索着人生的真谛和品味着向前奔驰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