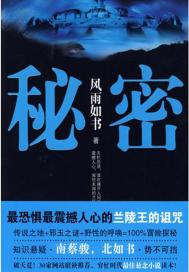第51章 小有所屈大有所伸
●人主之有为于天下,其心未尝不欲朝廷之尊而纪纲之肃也。而人主之所为,则每有以自隳其尊而坏其所谓肃然者。以其道不足以制欲故也。盖朝廷纪纲之所系,莫大于法,而所以守是法而无所挠屈者莫重于人臣。然臣守之于下,而君每抑之于上。欲心一动,勃郁炽烈,惟恐夫人执法以沮吾之意而不得以快其所欲。不知夫称快于一时者,乃所以自坏其维持天下之具。愚谄者挠法以从君于昏,忠义之士气沮势夺则慨然引去,卒至于剥落解散,不可收拾,而危亡不旋踵而至。盖小有所伸则大有所屈,势之必然而理之固然也。
[译文] 君王对天下有所作为,他的思想动机不能不希望朝廷地位尊贵和纲领法纪严正。而君王的所作所为,却总是因自身的原因而破坏了朝廷的尊严和所谓令人生畏的法纪。因为他的为君之道不足以制约自己利欲之心的缘故。朝廷用来维系人心的,没有比法纪更为重要的了;而恪守法纪并表现得不屈不挠的,没有比人臣更为重要的了。但是臣下在下面恪守纲领法纪,君王却在上面加以压制。君王的利欲之心一旦萌发,便愈演愈烈,只担心臣下实施法纪以阻挠他个人的意志而不能尽情地放纵他的欲望。他不清楚那称快一时的做法,正是他自己用来破坏维持天下统治的法纪的因素。愚昧谄媚者阻挠法纪的实施而与昏君同流合污,忠义之士的气节和地位受到压抑和侵夺而愤然离去,终于导致朝廷分崩离析,局面不可收拾,而国家危亡很快到来。在小的方面得以伸展,在大的方面就会出现挫折,这是形势和事理发展的必然结果。
●古之贤君,气听命于心,情受制于礼,蓄威屈势,使守职不为所夺,得以自伸。凡法之所在,虽卑且贱,不敢震之以威,从其所重。夫是以朝廷尊而主威为之振,纪纲立而奸邪为之寝。古之人有行之者,汉文是也。细柳之师,亲屈帝尊而劳之。闻军中不驰之令,则按辔徐行。盗环犯跸之罪,赫然发怒欲诛之,闻张廷尉不奉诏之言,则乐受而无难色。邓通之贵幸,其宠之非不至也。一戏于殿上,则丞相申屠嘉檄召欲斩之。夫以天子之尊而庇一弄臣,则孰敢谁何者?而嘉持法召之不疑,帝亦遣之不吝,必俟其已困辱,然后徐遣使持节以谢丞相而召之。太子,君之贰;梁王,(太后)[皇后]之爱子:其势非不尊也,一不下司马门,则公车令张释之追止而劾奏之。夫以父子兄弟之亲而少差以礼,亦未尝为甚过者,而释之持法劾之不恕,帝亦受之不却,必免冠谢太后以教太子不谨,然后(太后承教)[太后乃使使承诏]而赦之。夫汉廷诸公之所为,自敌己以下,受之而不能堪,而文帝敛威抑气使将军得以行其令,使丞相得以举其礼,使廷尉得以执其法。不牵于爱,不役于情,伸臣下之所为,以肃朝廷之纪纲。当是时,上而宰相,下而百司,内而朝廷,外而军旅,法之所在,凛若秋霜,隐若雷霆。窥伺之心息,陵犯之风消。非有孝武之光烈、宣帝总核信必之政使然也。盖惟礼义以养其心,和平以收其气,抑情以执法,屈己以伸臣下而已。若汉景帝则不然。溺于久安,偃然有自用之心。凡文帝之所为,优容奖借、不敢挫折其臣下以自坏者,景帝一切反之,非有功不侯,此高帝之法也,而王信奈何欲侯之?封同姓以填天下,此高帝之法也,而晁错奈何欲纷更之?故周亚夫执旧约以争外戚之封,申屠嘉因奏庙埂以欲诛纷更之臣。此二者固宏纲大法之所在,神器宗庙之所赖,以维持全安于无穷者,而景帝皆挫抑不用。一饿死,一呕血死。王信果侯,晁错果用,则景帝一时岂不进退如意而甚快也哉!然亚夫死而王信侯,则毁高帝之典刑而启封拜外戚之端。申屠死而晁错用,则纷更高帝之法而启吴楚七国之祸。愚故曰"小有所伸则大有所屈"者,此之谓也。
[译文] 古代的贤明君王,气质受思想支配,感情受礼法控制,收敛自己的威力,抑制自己的权势,使恪守本职工作的官员不受侵扰,能得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凡是有法纪存在的地方,即使是地位卑贱的人,朝廷也不敢用权威去震慑他们,放任他们做好本职工作。因此朝廷的地位随之尊贵,而君王的权威也因此树立起来;法制健全,而奸邪不法之人就会因此消声敛迹。古代的君王有对上述做法身体力行的,这就是汉文帝。由周亚夫率领的驻扎在细柳营的部队,汉文帝降低自己的身份前去慰劳。文帝听说军中有不许驱驰的命令,就拉紧马缰绳缓缓而行。对于偷窃高庙坐前玉环和冲撞銮驾的罪犯,文帝大怒,要杀掉他们;当听到廷尉张释之不执行文帝旨意的话语后,便高兴地接受了释之的意见而没有一点为难的样子。邓通位尊并为文帝所亲近,他所受到的宠爱无所不至。一旦他在朝廷上有失礼节,丞相申厝嘉就用檄文将他召到丞相府中要杀掉他。凭天子的尊严而庇护手下的宠臣,有谁敢过问呢?而申屠嘉依法将邓通召到丞相府而没有疑虑,文帝将邓通遣送到丞相府也没有吝惜之心。文帝一定等到邓通处境窘迫不堪时,才不急不忙地派使臣拿着朝廷的符节向丞相道歉并把邓通召回朝廷。太子是君王的副手,梁王是窦皇后的爰子,他们的地位不是不尊贵,然而他们一旦在司马门不下车步行,公车令张释之就追了上去制止他们的越礼行为,并向文帝检举他们的罪状。凭他们父子兄弟的骨肉之情而稍稍失礼,何况也未曾有较严重的越礼行为,而张释之依法举报而不加以宽怒。文帝也没有逃脱法律的约束,在薄太后面前一定脱下皇冠向太后道歉,说自己教育太子不够慎重,然后太后才派使臣持诏书赦免了太子和梁王的过失。汉代朝廷的各位公卿的所作所为,受到与自己地位相当或不如自己的人的批评,往往还接受不了,而文帝却能做到收敛皇帝的威严和气势,使将军周亚夫得以实施军令,使丞相申屠嘉得以端正朝廷的礼制,使廷尉张释之得以执行国家的法令。文帝不为爱子之心所纠缠,不为个人感情所驱使,让臣下放心大胆地工作,以严肃朝廷的法制。正是此时,上至宰相,下至百官,内至朝廷,外至军队,凡是法制存在的地方,使人觉得像秋霜一样寒冷,像雷霆一样威重。观察时机有所图谋之心熄灭了,侵犯他人利益的风气消失了。这并不是只有汉武帝那样的辉煌功业和宣帝那样的综合名实、信赏必罚的政治才出现这种局面。汉文帝只是用儒家的礼仪采养育他的思想,用心平气和的态度来收敛帝王的气派,抑制个人感情来执行朝廷制定的法令,降低个人身份让臣下放心地工作罢了。象汉景帝就不是这样。他沉醉于长治久安之中,安然自得地有自以为是之心。凡是文帝的所作所为,诸如对臣下宽容大度、勉励推重、不敢随意凌辱以自毁为君之道的做法,景帝都反其道而行之。没有功劳不封侯,这是汉高祖订的法令,(而为什么要封王信为侯呢?封同姓为侯以安抚天下,这是汉高祖订的法令,)而晁错怎么要随意更改呢?因此周亚夫根据汉高祖的法令对景帝晋封外戚王信为侯的做法据理抗争,申屠嘉借向景帝启奏晁错侵占高庙陵地的机会而要杀掉违背汉高祖法令的大臣。周亚夫和申屠嘉这两个人固然是国家宏纲大法的体现者,国家政权的依靠者,[有了这样的人,]可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他们在政,治上却受到了景帝的压抑而得不到重用。一个饿死了,一个吐血死了。王信终于被封侯,晁错终于被重用。景帝一时间难道不举黜如意而较为开心吗?然而周亚夫郁郁而死,而王信得以封侯,便破坏了汉高祖订立的常规,而开了对外戚授官封爵的先例。申屠嘉愤懑而死,晁错却得到了重用,便打乱和更改了汉高祖制订的法令,却导致了吴楚等七国反叛朝廷的祸害。我因此说"在小的方面得以伸展而在大的方面就会出现挫折",就是指景帝而言。
●夫立法以维持天下,其大者犹宫室之上栋梁垣,其小者盖瓦级砖。非甚狂惑,孰肯自隳其垣栋而自揭其管籍哉!惟其情欲之来,志气不能以自禁,随动而流,随触而勃,遂至于溃裂四出,甚坏而不可救。故夫至公无私,我以存天下之法,常情所不能忍。于机微眇忽之中,而遏其横流不可救之祸,自非以气御志、以道胜情之君,畴克尔哉!武帝天汉中,胡建得守军正丞。监军御史为奸,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建约走卒诛之。竟斩御史,然后奏闻。武帝报曰:"'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建何疑焉!"
[译文] 制定法律是用来维持国家的安定,根本大法犹如宫室上面的栋梁和四周的墙壁,具体法规犹如宫室上面的瓦片和墙壁上的砖块。人不是到了比较狂妄昏惑的地步,谁能毁坏自己宫室和掀掉自己的坐席呢?只有他萌生了个人的情感和欲望,他的意志和气节不能约束自己,随着感情的冲动,欲望如持续不断的流水,伴随着触及物体而浪花四溅,它的破坏程度是很严重的,是不能补救的。因此大公无私,以维护国家法制为己任,这是人的一般感情所接受不了的。在日常的细枝末节上,就能防止无法补救的灾祸的发生,倘若自己不是用气节来支配自己的志趣、用道义来制约自己感情的君主,谁还能这样呢?汉武帝天汉年间,胡建得到驻守京师北军正丞的官职。监军御史为非作歹,他凿穿北军的围墙作为贸易市场。胡建与手下的士兵约定好,竟杀了御史,然后上奏武帝得知。武帝答复说:"国家的礼制仪节不适用于军队,军队的礼制仪节不适用于国家。'对于胡建的做法还有什么值得怀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