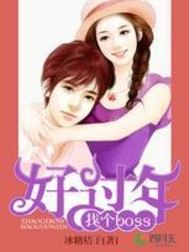两个主角突然离场,让南宫俊和墨子君变得更加焦头烂额,气氛十分尴尬。还好南宫俊有着极好的应变能力,凭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让大家相信了云熙是因为准备新品而劳累过度。
事情也确实如此,送到医院后经过仔细的检查,医生的诊断是因为过度疲劳,加上受了精神刺激所以才会晕倒,她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安静的休息。安置好一切,温仕凯又返回到会场,除了避嫌,他还有
一个目的就是找南宫俊和墨子君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看着病床上那苍白的脸庞,额头渗着细密的汗珠,紧锁的眉头,干涸的嘴唇,站在黑影里的男人脸上闪过一丝阴霾。
“怎么每次都被人欺负?”黑色的身影从暗处走出,缓缓抬起手臂,手掌停留在她的眉间,迟疑了片刻,轻轻地抚向紧皱的眉头。
“不是我,不!不要!妈妈……”云熙不断的梦呓着,两手紧紧的抓着被子,痛苦的表情似有逃不开的纠结,一滴晶莹的泪珠滑落……
妈妈……这样痛苦纠结的呼声深深的冲击着荷鲁斯的心,他的手因内心极度的痛苦而变得颤抖,触碰到那滴温热的泪,他不再拥有的东西。“眼泪”这种无用的东西,好似多年前已经用尽了一般,他不再需要,那是懦弱的代表,让他十分鄙视;却在此刻,这声虚无的呼唤,这滴温热的泪,深深的触动了他那颗冰冷的心,像是揭开了尘封的记忆,痛苦蔓延着……
荷鲁斯将胸前的皮绳挂链摘下套在了云熙的脖子上,然后拿起手机打开了录像功能……
再次醒来,敏锐的嗅觉让他敏锐的发现自己身处的环境——医院!为什么会在医院?谁又受伤了?睁开眼眸的瞬间,他环顾四周,发现自己的手正紧握着一只纤细白嫩的手,而躺在自己眼前的人竟然是云熙!
这是怎么回事?云熙怎么在医院?他极力的回忆着,尽管这样会很辛苦,能够想起来的确很有限,虽然他们存在同一个身体,有着共在意识的时间却极其短暂。
忽然发现云熙干涸的嘴唇蠕动了两下,他急忙从病床边的桌子上拿起水杯,用棉签蘸着水擦拭着,又用纸巾拭去她额头上的汗珠,这样的温柔恐怕就连他自己看了都会吃惊吧。
突兀间,安静的病房传来一阵手机提示音,羿少龙拿起手机的同时脸色变得愈加深沉。
视频中的影像正是那个住在他身体里的另一个人格,看样子他很生气,似乎知道了羿少龙对云熙情感的微妙变化。
“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吧?不过这可不是我所期待的!记住,她是我的女人,很久以前就是,所以,离我的女人远点!不要轻易挑战我的耐心,否则,我会让你的世界崩塌!” 荷鲁斯极富磁性的嗓音冷冷的警告着,狭长的眸子里尽是桀骜之色,这是他一惯的作风。
羿少龙没想到荷鲁斯居然会这么在意云熙,他现在真的很好奇,他们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他真的一丝记忆都没有,难道这就是心意相通?即便是不同的灵魂,喜好居然如此雷同,还是他对云熙的喜欢,原本就是荷鲁斯的心在操控?
此刻,羿少龙心绪愈加烦乱起来,对于这种威胁视频他当然不会妥协,尤其是那个夺走了他身体和时间的怪物。原本是要远离她的,可事情的发展往往会超出他的预期,现在,他已经无路可退了,偏偏就是这种执念让他又一次向她靠近。
羿少龙正在胡思乱想着,云熙缓缓的睁开了眼眸,目光投向坐在床边的羿少龙,“我这是在医院吗?你怎么在这?”
“你醒了?我……我听说你生病了,所以……抱歉刚才因为临时有急事离开了,不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于自己为什么在这他无从解释,只能以询问云熙的情况来掩饰自己的局促。
面对羿少龙的询问,云熙沉默了,此刻,她的心情无比纠结,虽然自己也是无辜的受害者,可毕竟是因为自己将这些无辜的人牵扯进这样龌龊的绯闻里,她要如何告诉他?她又把事情搞砸了,白费了他的苦心。
面对云熙的沉默,羿少龙有些懊恼,自己又一次陷进了迷雾之中,这十几年他总是在做着不断猜测、推断的工作,以确保事情没有因自己的精神问题给别人带来伤害和麻烦。
“你不说,我自然也会知道。”见云熙一直沉默不语,羿少龙有些赌气的说道。
云熙见羿少龙有些急了,正想要起身解释,却被胸前的一丝冰凉吸去了目光,不知道什么时候身上多了一个皮绳挂链,她拿起仔细端详着,声音却忽然变得颤抖,“这个……这个怎么会在这?他来过吗?你有没有看到他?”她急切的从床上爬起,想要四处寻找,却被羿少龙拦了下来。
看着云熙紧张急切的模样,眼眸含着泪花,手里还紧握着胸前的挂坠。
“你干什么?你身体还没好,你手里拿着什么?”羿少龙拉住她的手,目光触及她手中的挂坠,心情更加沉重了。
这是一块银色的十字形挂坠,立体浮雕设计,中间不是通常的耶稣,而是红宝石雕刻的不死鸟。他知道这是荷鲁斯平常随身携带的饰物,现在居然给了云熙,这是赤裸裸的宣誓主权。
“刚才在发布会上我见到他了,他来了,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云熙苍白的脸庞因为激动而泛着幸福的红晕。
看着云熙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羿少龙的心忽然如撕裂般疼痛,他现在可以确信,这颗痛着的心是自己的。这样的笑容是他不曾见过的,却是因为别的男人呈现在自己面前,严格来说,也不算是人吧,应该说是人格,一个附着在他身上的人格。她要怎么面对自己爱上了一个分裂出来的人格,自己又该如何面对她,这样的两个人唱着三个人的戏,实在有些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