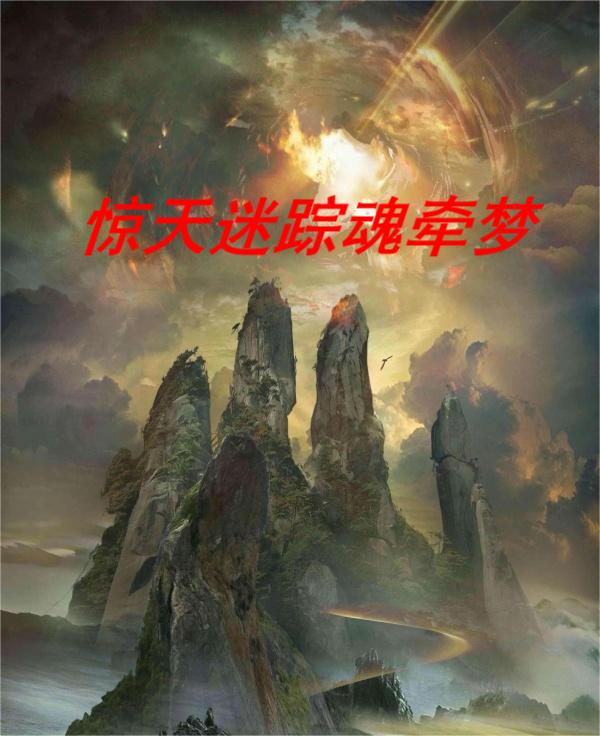幽暗深邃的深海海底,一道红芒,裹挟着骇人的威势,破土而出,如一株巨大的旋转的油纸伞托着长长的伞柄,直直的向上冲去,几千丈的距离,转瞬即至。
此时的海面上空,天有些阴霾,或轻或重的乌云,布满天空,无风,无浪。
红光刚刚破出海面,在其正下方的海水便如同开了锅的沸水一般,一个接一个的巨大气泡,从中泛起爆开,紧接着一道耀眼夺目的七彩气柱,带着一股毁灭气息,爆射而出。
老者一手指着红莲,一手引着宝舟,已然察觉到那股来自脚下的气柱,正朝他疾射而来,上面散发的正是九华玉塔器魂和神秘种籽混合在一起的气息,此刻想躲,已来不及。
难以再细想更多,心念一动,周身紫芒闪动,聚气凝神,把左手引着的宝舟稳稳地端平,向着其前方海面方向猛地一送,而后不再顾及宝舟,右手法决变换,头顶悬浮的烈炎红莲光芒一闪,瞬间出现在他双脚下方,花蕊朝下,向着气柱迎去,眨眼间,便撞在了一起。
“轰……”的一声巨响,海空上方的乌云一沉,似被一张无形大网,兜住了一般,朝着海面挤压下去,那是被撞击形成的真空所拉扯的。
看上去强大无比的七彩气柱未能获胜,顷刻间,化作无数股滔滔气流,形成了数股龙卷风,卷起滔天巨浪,向着海面的四面八方呼啸奔去。
烈炎红莲同样不堪,在和气柱接触的一刹那,稍做阻抗,便被冲的红光黯淡,摇摇欲坠,勉强维持住红莲的形态,好在气柱虽强,但后劲不足,只坚持了三息,便轰然消散,而烈炎红莲也随后像一面易碎的琉璃镜子一般,支离破碎,碎成漫天的焰火,在这阴沉灰暗的海空之间,蔚为壮观。
四散的火灵力,有的在空中燃烧殆尽化作一缕青烟,随风飘散,有的洒落海面,似被沏灭的烛火,湮灭在海水之中,最后都消散一空。
老者在脚下红莲挡下气柱,乍作僵持的那一刻,便已朝宝舟方向瞬移,可终究晚了一步,就在其身形将将变淡,还未完全消失时,脚下巨大的冲击力便席卷而至,使得身形骤然一顿,随后才完全消失。
宝舟被老者拼力送出后,速度惊人,流星一般划过天空,向着天际的海面落去。
老者身形在其后的空中闪出,甫一出现,便踉跄的在空中跌出了数步,强行收住身形,一口暗红精血,喷洒在空中。
“是垂死挣扎的九华玉塔器魂和融合了玄水的神秘种籽,对抗所产生的爆炸?不应该!它们相互消耗,最后只能相互耗尽,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动静。
难道是我的那记炎斩起了作用,木水一路,和玉塔的土属性僵持不下,我的那记炎斩的加入,使得四方相生又相克,木又生火,火又生土,土木难调,水火不容,,如此反复,便再难平衡,随即爆炸,对对对!一定是这样!
咳咳……咳……!
不过未曾想到,九华小儿这缕器魂,竟然如此之强,怕是本体已炼化到准仙器的品阶,这千年岁月,还真是公平呐!”
老者的推断,完全正确,正应了他破阵之前的那句话,确实是他送了九华玉塔器魂一程。
推断的念头在脑海中如电闪过后,喉间又一甜,忙强行忍住,压下胸口翻涌上来的气血,稍作平息,便调动体内残存的灵力,身形再次消失在空中。
下一刻的他,出现在,仍旧在半空中滑行的轻舟旁边,两次超远距离的瞬移,使得他重伤的身体,疲弱不堪。
手扶舟边,身形随舟滑行,朝内看看淡薄金光下,还在安然熟睡的小家伙儿后,抹了抹嘴角下颌的血迹,露出了劫后余生的笑容。
身体刚刚痊愈又受重创,此时的他,体内灵力已所剩不多。
不假于物,而凝成红莲外放,是临仙境中期,双花阶段才能轻松驾驭的,而他为了破阵成功,不惜代价,强行施展,勉强支撑到冲出海底,已然使得身体暗伤遍布了,破阵后又和这气柱搏命一拼,更是雪上加霜。
此刻体内的灵海,只余稀薄的几层薄雾,道池内的灵液,业已见底,莲叶正中的那朵九瓣莲花也无精打采,萎靡暗淡,紫红色的花蕊没有半点灵气吐出。
神识的消耗同样惊人,不但要操控红莲破阵,护身,又要时刻控制着轻舟,以保其内小家伙儿的安全。
神识乃精气神所化,巨大的消耗,使得他的身心愈发的萎靡不振,疲累不堪。
手扶着一侧舟体,把身体小心地翻了进去,避开小家伙儿,坐在靠前舟首这一侧,然后伸手把裹着战裙的小家伙儿轻轻的抱起,自己躺直身体,仰卧在舟头,此时小家伙儿仍旧未醒,自打手中的“种籽”没了以后,小家伙儿就变的有些不一样了,似是少了些灵气,这也难怪,一下子断了那神奇的生机的滋养,一定会变得与之前不同。
把小家伙放在自己的小腹处,两腿微微屈起,顶住甲裙里的小脚儿丫,不让他划落。
双臂环在甲裙上,双手掌心凝出一小团所剩无几的火灵力,使得双掌间变得温热,隔着甲裙,温暖着小家伙儿的身体,因为他感到了此时此刻这片天地的温度,应该是冬季。
做完这一切,他闭上疲倦的双眼,感受着海天之间的灵气,好在这不再是那“四海封绝阵”里,空气中五行之力虽然稀少驳杂,但终究是有的,有就好。
神识落入体内,看到满目贫瘠的灵海,道池,老者无奈又庆幸的在心中一笑,无奈的是刚脱离近千年的困境,又落的重伤加身,庆幸的是,虽是重伤,但终究未死,且又逃出生天,假以时日不难找回失去的修为境界,到时有恩的报恩,有仇的报仇。
只是这恩情该咋还呢?
轻舟上的金芒越来越淡薄,飞行的速度也越来越缓慢,他已经没有更多的灵力和神识来支撑和控制轻舟的护层和飞行了,仅有的那丁点灵力,他要用来运转灵海吸取空气中稀薄的灵气。
就这样先飘着吧,因为刚刚在高空时,他已经看到了远处海天线上,有陆地的存在。
给他点时间恢复身体和灵力,他就有能力带着小家伙儿活下去。
海生今年八岁,个子比村上同龄的孩子要高一些,也壮一些,看上去倒是像有十多岁的样子。
和他爹一样穿着一条紧腿的鱼皮裤,上身是她娘特意给他缝的加厚鱼皮袄,蹬着双鱼皮短靴。
脸色有些黑,又透着些红,那是总在海边玩,被太阳晒,被海风吹的,留着个梳背儿头,圆脸,平眉,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鼻梁不太挺,嘴唇有些厚,一脸的憨厚老实相。
这是他第一次和他爹驾船出海捕鱼,刚刚入冬,正是捕鱼的好季节,他想帮他爹多打点鱼,冬季能存住,到了集市能多换点银钱,等到了开春禁渔期,就不用过的那么辛苦。
走时他娘一遍遍叮咛他,一定要听他爹的话,不许乱跑,海上不比陆上,万一出现什么差错,危险,没地儿哭去。
又嘱咐郑大海,千万要照顾好孩子,别出差错,别看他长的大,可岁数毕竟还小,别老拿着他当大人使唤。
郑大海听了,嘿嘿的笑着,一个劲儿的点头。
海生听了,也嘿嘿的笑着,也一个劲儿的点头。
他娘无奈的摇摇头。
“这爷俩如一个模子刻的一般,除了长相,连那木讷憨厚的性子也一样,不都说养儿随娘么?
唉!真是操心呐!”
海生家的船是他们村里最大的渔船,这是郑大海花了三年时间,从村子北面望夫涯的一侧山腰上,伐回的上好木料,闷着头一点点造出来的,山路难走,坡陡林密,村里人都佩服郑老大的这份能干和执着。
前两年,海生他娘每每听人说起郑老大造大船的壮举时,都似是不在意的说一句:“哎呀!可别夸了,嫁他时,他就说要给我造条大船带我出海,这海生都五岁了,才折腾出来,你说还有啥可夸的!”
说完,脸上又不由得透着幸福和得意。而后就笑着等那些婆娘们,笑骂她的不知足和羡慕嫉妒的话语。
她也是个渔家女,也早早的随父出海捕鱼,知道一条结实,耐风浪的大船,对渔民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活着的饭碗,那就是传家的宝。
她嫁给郑大海时也没奢求着有条大船,奔的是,他人老实,能干,又对自己好,和他过日子踏实。
郑大海娶她时,是对她说过要给她造条大船,让她风光,可她没在意,以为这憨汉子在讨她欢心。
没成想,六年后他真的造了条大船,只是,她有海生牵着,没能坐上去出回海,可一听别人提起,心里还是感到满是美美的幸福。
她家的船能行的更远,也能捕获更多的海货,这两年让她家的生活相比同村的其他人家要富足一些,平时除了担心丈夫的出海的安危外,别的她很知足。
只是今天是海生第一次出海,怎能让她放心的下,祭过海神后,她千叮咛万嘱咐,也不知道那爷俩能不能放心上。
她又回到家,给海神爷爷上了香,又重换了些贡品,祈求多多保佑他们父子和那一船人能平平安安的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