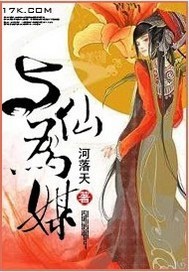傍晚,谷天祈接到署名为武明德的一封信:武府大门为君敞开,见信即刻赴约,否则如图。信的下方是一幅画,画中那个酷似茯苓的女子衣服凌乱,大片肌肤裸露在外面,斜躺在床塌上,一名男子坐在床边,大手正欲抚上那娇嫩的身体。
“混蛋!”谷天祈将信揉成一团,脸上黑云密布,一溜烟的冲出了客厅。云清与陆英丝毫不敢怠慢,跟了出来。
武府的后花园,一座假山前面的亭子里,武明德兴致勃勃的品着茶。
“你这是什么意思?”茯苓将手中的画种种的放在石桌上,气鼓鼓的。
武明德得意一笑,摊摊手,好不无辜地说道:“让我猜猜你为什么生气,是因为我将你画的不够好看还是怪我把它送给了寒医?”
“你!”茯苓蹙眉,想通他话中的潜在的含意之后,气得脸色绯红。混账男人,她在心里嘀咕。他眼眸中不怀好意的笑,她警戒异常。
谷天祈寒着脸,任凭仆人带着穿过长桥来到布局规整、设计巧妙的后花园,来到风景如画的假山前。
“寒医,我的画是不是很逼真?”瞥见他走了过来,武明德故意挑起他的怒气。
谷天祈怒瞪着他,鼻子哼哼两声,一语不发,大手一挥,黄色的粉末顿时漂浮在微凉的空气中。
一个熟悉的声音毫无预警地传入茯苓的耳中,她微微一愣,屏息以待。突然武明德上前搂住她的纤腰,亲密地将她带入怀中,挡在自己的前面,还无耻地用脸颊磨蹭著她的秀发。
谷天祈目光更显得冷峻了。该死的女人,她竟然不排斥别的男人的亲近。
两个男人就这么对峙着,眼神里均是充满杀气。
“你派人送信有何目的?”许久,谷天祈让步结束无声对峙,开口道,他从她隐忍着颤抖的动作觉察到刚刚撒出的天之兰心发挥了毒性。
“没什么目的,就是想向寒医你证实一些陈年往事?”武明德突然从抽出腰间的匕首,抵在茯苓的脖颈处。
茯苓伸出两指,轻轻夹住脖颈处的冰冷剑尖,企图将它移开,试了几次,剑身依然纹丝不动。微微侧首,问,“武公子,这是什么意思?”
谷天祈随意瞥了一眼搭在她脖颈处的利剑,嘴角微勾,略带嘲讽的说,“真可笑!你凭什么觉得胁持她就能让我乖乖顺从你,你知不知道我有千百种毒药能在瞬间置你于死地。”
“你不会,因为你清楚如果那样做她会比我先死。” 看到他垂在身侧的手指不停地抖动着,武明德得意的笑了,“你在乎她!这就是我的筹码!”
茯苓抬首,他的目光中带有三分嘲讽两分凉薄,再加上五分无奈,这是什么意思?她的存在就那么让他困扰吗?
“你想问我什么?” 谷天祈无奈的说。
“我经调查得知玉石吊坠是皇家之物,当年皇上未登基前赠与一位宠爱的侧室,后来这名侧室在分娩当日竟意外遭火焚烧,这位侧室以及所有负责接生的人一并葬身火海。后来皇上追查了几个月也没发现什么线索,只是疑心是先帝的韦后因报复而纵火。如今这枚玉石吊坠重现人间,是否这件悬案有了什么转机?”为表诚恳,武明德将所打探的消息一一说明。
“爱莫能助,因为你说的这些事情我完全没有听说过,这玉石吊坠是我幼年时出去玩意外捡来的。” 谷天祈皱眉,该来的还是来了。
“我查到十几年前你全家遭受灭门之祸,是否跟这枚玉石吊坠有关系?” 武明德试探的问。
“江湖恩怨,总是难免,不提也罢。”提及灭门血案,谷天祈浑身便散发出阴冷的气息
“听说当年潞州别驾的火灾现场并没有婴孩的尸体,有人说那名刚出生的女婴被一个丫鬟抱走,转交给你父母抚养!后来那名小女孩被黑衣人追杀同你爹娘一起坠崖。而现在这枚吊坠重新出现,是不是代表着那名叫无意的小女孩坠崖后生还?”
“我就是无意!找我有什么事?”云清款款走来,抱怨道,“对待女子应温柔怜惜,武公子怎么这么不懂得怜香惜玉呢!”
“你不是,她才是无意!”武明德指着款款走来的云清高声道,“你不过是一个易容成她模样的替代品罢了!”
“我不是无意!” 茯苓表情霎时僵住,全身神经开始紧绷,为什么每个人都逼着她承认自己不是无意这个事实。
武明德根本不理会她的挣扎,一脸得意说,“当日酒财神典当玉石吊坠之后,我便派人立马打探,得知玉石吊坠为一名叫茯苓的姑娘所有。所以我将计就计,故意让你们盗走吊坠,就是想看看你有何反应。如果你没有任何行动,说明这玉石吊坠与你家被灭门无关,可是你偏偏连夜派替身护卫陆英出城前往岩谷,一日后又驾着马车返回唐门分坛岩谷是个什么地方,相信寒医比我这个半个江湖人更清楚吧!现在我们总该可以坐下来好好说那些陈年往事了吧!”
“她根本就不是无意!因为她身上并没有吊坠!”云清反驳道,甚至取下身上的玉石吊坠佐证。
武明德斜睨他一眼,淡淡地提醒道:“寒医大费周章从岩谷请来易容高手,怎么还好将吊坠留在真正的无意身上?如果我是当年那伙人,哪还会管她是不是无意,早就杀了她了。我对她没有恶意,只是想弄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你放开她,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谷天祈悲伤的闭上了眼,露出痛苦的神情。
武明德连忙松手,满脸歉意对茯苓道:“抱歉,情非得已。”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这一招走得真险,倘若茯苓不是真正的无意,倘若寒医不是这样在乎她,自己不但如意算盘落空,小命恐怕也会不保。
“谁能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茯苓眼底闪过怒火,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油然而生。就好像所有人都清楚她的生平,就她不知;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同自己一样的姑娘是易容的,只有她信以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