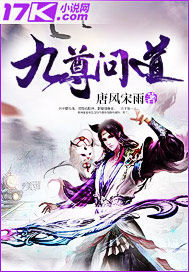云州,宁海平原,自古以来就有边塞江南之称,从昆仑山上融化下的雪水,奔涌成泯河、泠水、问江、端河四条河流,在此间交错,形成网状水域,滋养着这方土地。
云州牧府上洛就建城在端河之畔,是一座屹立千载,养育数百万人口的雄城,这里也是玄王帝恒的大本营,玄王帝恒据此,北抗夷狄,西拒沙匪,往南还能与大乾朝廷争个长短,不可一世之姿,当世无二。
而且比之岐王帝晋结交墨家,灵王帝贤背依仙门,玄王帝恒可谓是全凭一己之力镇压四方,将上洛城建得能与大乾四京一较长短,其间所展露的雄才大略实在令人赞叹不止。
作为北地最大的商业中心政治中心,上洛比南方诸城,更多了一分气派,内城外城层层叠叠有六重之多,除了最中心的玄王宫,以及次一圈的军事政事枢机所在,把城中的坊市居所划分的井然有序。街道正东正西,正北正南,宽处可容十架马车并行,堂皇大气。
往来行人身份多样,有带着奇异珍玩的西域胡客,有载着皮货的草原牧民,有运着茶盐的南方商贾……不一而足,他们的身影充斥于坊市之间摩肩接踵渲染出好一番繁华景象。
城西的安平坊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地方,这里因着靠近小重山,坊市相当热闹,人流往来不绝。小重山并非什么风景名胜,之所以吸引游客,是因为上面坐落着千年古刹宁安寺。宁安寺也并非什么灵隐之地,否则早搬到内城去了,人们来此地上香更多的是一种信仰,一种寄托。
宁安寺没有那些佛宗大庙受到达官贵人的追捧,但却有许多中下小民的信众,由是香火鼎盛。因为更加亲民,所以在这周围也催生出了许多别有风味的面食摊点,开光刻字的珍玩店铺。
刘记面摊就开在小重山脚,因着往来人流众多的便利,也算是小有名气。
方和蹲在路边,捧着个海碗,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哧溜哧溜吃的舒爽,似乎浑然不觉一人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
来人两鬓沧桑面目却显年轻,竟是不知什么时候从岭佑来到西北的苏晗。
“你倒是好胃口。”苏晗轻笑向着老友率先问候。
方和不觉有异,先大口咽下口中面食,又舔去嘴角酱汁,这才从容回答道:“人生在世本就不易,何苦再为难自己的五脏庙。倒是你,不在家当自己的大少爷,跑到这到处风沙的西北做什么?”
苏晗一笑:“近日在家中闲坐,心血来潮之下,替你算了一卦,发现你五行缺我,所以我就来了。”
“嘁,我也替你算过了,你五行缺德,命里欠揍,需要我帮你活络活络。”方和先是啐了一口,接着斥道:“别整这些虚的,你那些花花肠子,我还能不知道。”
苏晗打了个哈哈,装正经道:“为你而来却是真的,你即将突破,没我罩着你,能行吗?当然还有其他顺带,比如天机现世,要找个好的切入点。在家坐着自然不会有机会,所以出来走走,碰碰运气。”
“天机现世?”苏晗前一句话让方和心中一暖,后一句话却让他皱眉道:“这你也信?”
“总是个念想不是,况且信的人又不止我一个,云霄峰上的那位对此不也是深信不疑吗。”苏晗满不在乎。
方和也不再纠缠这个话题,而是奇怪道:“你现在是老徐家的宝贝蛋子,怎么走的开?”
苏晗面色一苦:“还不是向我老弟屈服了,先从经商开始,只是没想到老徐家在这西北还有生意,为了躲开老娘的纠缠,索性选了这个最远最偏的,美其名曰:从底层锻炼。”
两人多年朋友,方和早已习惯了他吊儿郎当的说话方式,甚至有被他带偏的倾向,闻言似笑非笑的嘲弄道:“来西北做生意?你来的可真不是时候,这西北马上就要大乱了,可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到时候赔了血本,老徐家不能与你干休,定要抓了你去做种马,日日下崽,以赔偿损失。”
苏晗不想这多年冷口冷面的老友竟会如此说话,关键是一语中的,说的很准,想起老妈陶氏那殷切的眼神,他忍不住打了个寒颤,赶紧转移话题道:“这西北能出什么事?有玄王帝恒带着神兵轰天彻地椎镇压,连我都要掂量掂量,还有什么宵小敢来作乱不成。”
方和嘿笑着摇了摇头:“这乱子恰恰就出在玄王帝恒自己身上。”
“哦?”苏晗不意听到这些八卦,真的有些兴趣了,追问道:“玄王帝恒惊才绝艳,武功一途早早入了宗师,距离最后的铸炼金身,也只有一步之遥;为人为政更是精明强干,这云州大地被他治理的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官员清廉务实,阡陌路不拾遗……他能出什么乱子?”
方和瞥了苏晗一眼,语气怪异道:“你把帝恒说的如此好,莫不是看上他了。那骚老爷们虽年过四旬,但保养得宜,你有些想法,须也怪不得你。”
“啊呸,呸,呸……”苏晗被恶心到了,啐道:“你丫口齿啥时变的如此伶俐,我这么多年莫不是认识了个假的方奉贤。”
“还不是和你学得,”方和默默吐槽一句,随即解释道:“主要是我认识的帝恒和你所说相差太大,他骄狂自大,目无余子,一向是他老大,天老二的人物,绝不是什么贤王之流。他那群手下包括后宫都各怀鬼胎,相互间争权夺利,搞的整个云州乌烟瘴气,甚至他的嫡长子都被送去观中学道了,他也不管,你说这云州怎能不乱。”
“这到是第一次听说,”苏晗摸了摸下巴,思索道:“可帝恒底蕴深厚,只要他能铸就金身,便可镇压一切,这云州也乱不了吧。”
“哼”,方和冷笑一声:“前提是他真的能够,你似乎忘了一个人,一个被聂海峰光芒所掩盖的人。”
“熙王帝云庭,”苏晗眼睛一亮。
方和颔首道:“不错,你觉得以帝云庭的野心,会放任三王势力成长下去吗?这些年来他借着聂海峰的光芒,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让人几乎忘记了他也是一个滨临突破的宗师巅峰,这种隐忍所图非小啊。如此一来,玄王帝恒危矣,而帝恒是云州的主心骨,云州能有今日全靠他一人之力,他一倒,云州岂能不乱。”
“嗯,有道理”,苏晗也点了点头,不过下一刻他诧异抬头道:“但这些关我鸟事,就算他真乱起来,我拍拍屁股走人,大不了换个地方做生意就是。”
方和白了他一眼:“我本来也没说有你什么事,只是我太一上宗在西北安身,看着西北即将大乱,心绪不宁,向你倒倒苦水罢了。”
苏晗也翻了个白眼,不屑道:“你太一上宗的根基之地在九原吧,在云州这块铺的探子并不大,顶多大乱到来时,卷了铺盖暂避,你们家大业大的,还会在意这点损失?到时候就算云州翻了个底朝天,也影响不到你们吧。”
方和想着这些年太一上宗东宗和西宗的内斗,沙哑着嗓音,满是疲惫地叹了口气道:“也许吧。”
苏晗扫了一眼方和手中空空如也的面碗,催促道:“别在这伤春悲秋了,事不宜迟,赶紧的,给你帮完忙,我还要去云霄峰踩盘子呢。”
说完扯着方和就走,出了安平坊,汇入人群,一路向城外而去,伴着夕阳,间或还有斗嘴声传来:
“对了,你的刀呢?”
“当了,换了刚才那碗面。”
“我欣赏你……”
与安平坊隔了两条街的地方便是这西市有名的勾栏,比不得内城同样场所的奢华却别有一番不同的景致。内城的烟花柳巷背后多有达官贵人支持,与云州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是普通平民和江湖客可以染指的。
而这里就自在很多,简单很多,当然也复杂很多,因为城狐社鼠的道道比那些上层的贵人们也未必少多少,至于说简单则是因为其中的交易没有丝毫道貌岸然的掩饰,更加直接,更加血腥。
入暮时分,两个彪形大汉抬着一支不断蠕动的麻布口袋,一路小跑,自吟风阁后门而入,一直走到后院的一处偏僻小间。
他二人走进里间,带好门,卸下口袋,往地上一倾,其中立时滚出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她双手双脚都被捆住,口中还塞着麻布,此时蜷缩在地,睁着一双圆圆的大眼睛,惊恐地看着屋中众人。
这屋里本是有人的,而且还不少,为首一人戴着八角帽,留着两撇鼠须,形容颇为猥琐。他本是满脸期待之色,但看清那小姑娘的形貌后,脸色立变,抬手就给当先进屋的大汉一脑崩。
“你奶奶个熊,不是说于老头家的丫头年过二八了吗?这是什么玩意?”
那大汉白长那么大个,在八角帽的淫威下,畏惧地缩了缩身子,喏喏道:“于老头的大丫头上月婚配了,只好拿二丫头抵债。”
八角帽听了此话,气得两片鼠须直往上翘,抬手又给了其一脑崩,骂道:“你不长脑子吗?那大丫头年龄刚好,来了就可以用上,这二丫头乳臭未干,还要白浪费老子两年饭菜,我要来有什么用?”
八角帽还待再发火,却被身后一个慵懒的声音制止:“好了,人都带回来了,还能再回去拆了于老头的骨头不成?这小丫头虽然身上没几两肉,但模样倒是挺周正的,这于老头倒是好福气,生两个丫头都这么标致。记得常平坊的李员外就好这口调调,你一会辛苦跑一趟去联络联络。”
“唉,好的,回头我就去,”八角帽转过身对上声音来处,就这么个功夫,却瞬间换上了一副点头哈腰的嘴脸,极尽谄媚之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