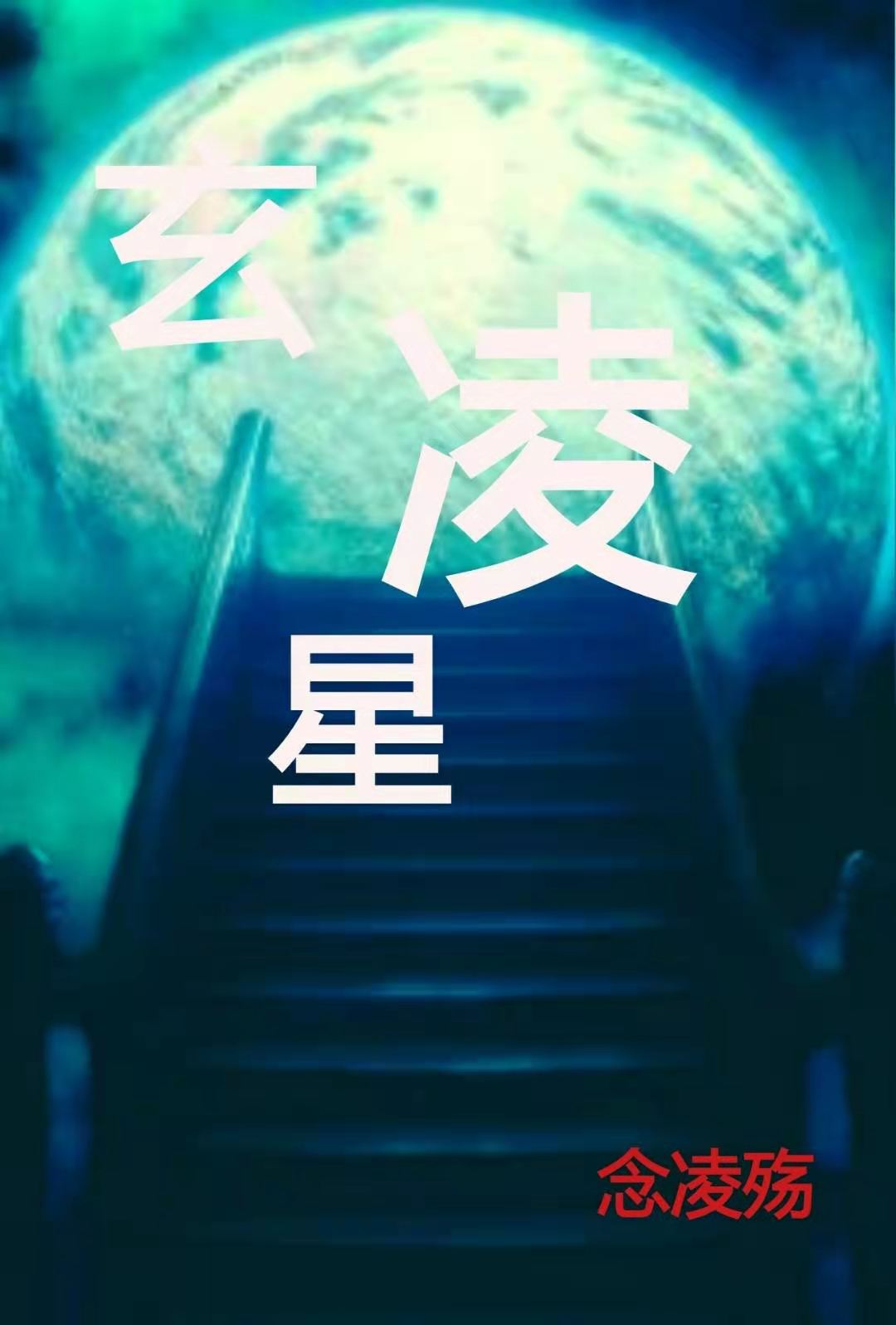明堂高缈,直入云间,迎着日光矗立,金碧辉煌。
帝云庭身着四爪青龙袍,玉带缠腰,环佩缀饰,俊朗的面容上昔日英挺尖锐俱都消失,只剩下一片从容不迫。安静地听着面前两人对话,笑而不语。
他面前两人一者是两鬓沧桑,紫红飞凤服裹身的中年男子,另一人是满头白发,朱红云鹤衫罩体的老者。此时前者面上愤愤不平,道:“如今上将军已铸就金身,皇上居然还不松口,只封殿下为熙王,实在是没有道理。”
老者闻言插话道:“介休此言差矣,‘熙’者光明也,自古以来,以‘熙’,‘晟’,‘昱’为封号者,也就相当于储君了。”
中年男子唐玮听得很是气不顺:“祖老糊涂,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知道熙者是储君之意,天下人谁来钻这个字眼。殿下为大乾昌盛东奔西走,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皇上难道就吝啬这个太子之位吗?”
帝云庭见唐玮语带怨望,连忙出声道:“唐公何必过激,父皇一向对我不喜,这次能做这么大的让步,不止封我熙王之位,还准许到这明堂进学,实质已是储君待遇了,有些事还是徐徐图之为宜。”他已封王,却未称孤道寡,显然是对面前两人的重视。
帝云庭的说法唐玮自是清楚,只是花费这么大功夫还是没能把熙王顶上位,心中多有不甘,发发牢骚罢了。此时帝云庭自己都坦然了,他还有什么好说的,虽然还是有些不忿,但也闭口不再言语。
诸事议毕,两人告辞。
聂海峰不知从何处闪了出来,欲言又止道:“殿下……”
“只是一个储君之位而已”,帝云庭望着明堂之外两道离去的身影,语调悠远:“父皇未窥外景,年岁渐高,总要有个说法的,何必急在一时。”
聂海峰蹙眉道:“殿下,我不明白,为什么镇国公对皇储一事,不发一言,若他能开口,我相信皇上是绝对不会再有犹豫。”
帝云庭转过身来,看着聂海峰笑道:“你呀,带兵打仗行,其他的就……,这一国神器,岂是可以随意处置的。这与先帝时不同,彼时国家动荡,太需要一个乾纲独断的声音,所以镇国公一手把先帝扶持上位。而今虽国家弊病多多,但总体而言却是安定的,若是随意指定皇储,不只是皇室威严扫地,而且带了太多私人感情,也于国无益。其实他老人家对你的认可,就已经是对我的最大的支持了。”
面对聂海峰,帝云庭难得的推心置腹,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话语也尽皆坦然。
聂海峰沉默不语,帝云庭继续道:“有些事情,你要尽快着手了,你在外面越强势,对我就越有利。”
聂海峰躬身行礼:“正要请教殿下。”
帝云庭闭目片刻整理好思绪,才缓缓开口道:“大乾积弊甚多,外有四夷环视,内有藩王割据,士族乱政,门派罔法,这些事情的解决非朝夕之功,而且以我现在的处境也没有插手的资格。所以只能暂且放下,但魔门猖獗不可不制,镇国公隐世,一些魑魅魍魉又有死灰复燃的势头,正好可以用来开刀立威。”
聂海峰颔首道:“属下也正有此意,此举不止利国利民,而且还能得到正道势力的支持,以殿下如今的处境正可将之化为己用。”
正道势力?帝云庭眯了眯眼,显出一丝轻蔑之色,但也不置可否,转移话题道:“魔门六道曾被镇国公一一击溃,极阴真君常圣,实力大损,不复旧观,但现如今竟拧成一股,不再互相内耗,这等情状,委实不可小觑。”
“属下明白。”
“对了,你这次南下,另一件事,也要多加关注。”
“什么?”聂海峰疑惑开口,不觉当务之急还有什么事能与魔门相提并论。
“南海之上,红莲花开,不知你有没有听说过?”帝云庭语气飘忽有着丝丝疑惑,不复之前的智珠在握。
“红莲教?”聂海峰疑声问道,这是南海新兴教派,崇拜圣火,认为尘世污秽,世人皆有罪,理应为圣火涤荡,在圣火中获得永生。“当年镇国公斩杀白莲圣女,捣毁无生老母祭坛,瓦解白莲教,确实是有些白莲教徒逃亡海外,莫不是换个名头又出来兴风作浪?”
“这些教派大多由佛道两家脱胎,其经义文字多有共通,所以常人很难分辨出其中有什么不同。”帝云庭认真解释道:“镇国公剿灭的,准确说,应该是罗教才对,他们供奉无生老母,诵念真空家乡,非佛非道,虽然也以白莲化生,向往生净土,但与崇信阿弥陀佛的白莲教有本质区别。至于这个红莲教派,他们自诩光明,供奉明尊,崇信圣火,定号明教,认为人生而有罪理应为红莲业火所涤荡,他们的教义多脱胎于佛教的慧与智,吸取了许多佛门律宗的精华。只是其中的善恶二元论太过极端,不可不防。更为诡异的是这个明教吸收了很多罗教余孽才能迅速发展壮大。若是常人,良禽择木而栖,改换门庭实属平常,可教徒哪有轻易改变信仰的?个中内情实在匪夷所思。”
帝云庭顿了顿又道:“不过其孤悬海外,与我大乾威胁不比魔门,所以还是当以魔门为主。只是务必搞清楚其跟脚,若日后有变,也可未雨绸缪。”
“是”,聂海峰深知自己于武道一途造诣颇高,但于其他方面却并不出彩,是以对帝云庭的决定还是比较信服的,尤其是能当得起帝云庭如此郑重其事的事情,即便不懂,他也不会多做置喙,而是同样郑重其事的一口答应下来。
帝云庭见他答应的如此干脆,心下起意,又多提点了两句:“你别觉得我是小题大做,如今仙门犹存,你应该清楚上古仙神传说,并非虚妄。这些教派身后多有上古死而不僵的大能支持。这明教来历奇异,竟由罗教改旗易帜而来,很可能背后牵扯到大能博弈,面对上古大能,以你金身修为,恐怕也不够看,由不得我们不谨慎对待。就是不提上古,只说眼前,此届明尊也是金身修为,万万不可小觑。”
聂海峰心中一凛,这些时日他铸就金身,确实有些太过膨胀了,帝云庭这当头棒喝来得及时。他审视自身,拂拭心灵,将那些自高自大的念头排除,再次郑重地向帝云庭称是。
……
南疆之地素来蒙昧,不是无尽的密林就是延绵不绝的山脉,道路不通,便也教化不开。虽也属大乾领地,但少有乾民在此定居,实在是条件太过艰苦。所以大乾朝堂的视野也少有投注在这里。
此时,在与大乾交界处,一座不起眼的土山上,正站着一道披着斗篷的身影,他微微佝偻着整个都缩在斗篷中。操着沙哑的声音向一旁空荡处问道:“事情办的怎么样了?”
他身旁空处一阵荡漾,竟掀起阵阵涟漪,诡异地从中走出一个人来,这人一身黑衣,面目年轻,第一眼看见斗篷人后,连忙行礼,过后才回答道:“这事虽由鬼蜮牵头,但真正操作的还是天心殿的人。”
“呵,那群恶心的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邪后也敢用?”斗篷人语带不屑。
黑衣人苦笑:“欢喜天界已经被打残了,剩下的只有极乐净土和天心殿,天心殿的人虽说恶心了点,但总比极乐净土那些疯子强吧。”
闻言斗篷人不禁默然,尽管大家不算志向相同,但到底此时算是一根线上的蚂蚱,不由有些兔死狐悲之感。
“对了,与南海明教联络的怎么样了?”
黑衣人再次苦笑道:“那群家伙自高自大,不会愿意加入我们的,能说动他们配合我们几次行动,已经是实属不易了。”
“也是,他们和我们终归不是一路,这次聂海峰南下,首要目标就是我们。短暂的蛰伏,势在必行。”
黑衣人发现自己今日苦笑的次数特别多,但却不得不为,跟随叹息道:“是啊,他一铸就金身,便北上草原击败了达瓦太师也门,迫的整个羯戎一族的王帐都向北迁了百余里,北域三藩都重新递了顺表。鬼蜮圣主伤势未愈,闭关不出,我们没有法身镇压,不蛰伏又能怎么办。”
斗篷人身体一僵,斗篷下的眸子闪过一道微弱的金光,对方的话刺激到他了,可却无从辩驳,他虽秘密证就法身,但又能怎么样呢,这注定是聂海峰的时代。他已经得到了确切消息,聂海峰铸就的是货真价实的万象金身,不是删减版的四仪真体。其凭借就是半部“先天八极功”,绝世神功啊。
整个天下自人皇创世,神通功法不知凡几,可能称得上“绝世”的,屈指可数。
都说天下间十方巨擘,魔门六道,世家十七……这些顶尖势力皆有绝世神功镇压,可他们自己心里清楚,那只能算是伪绝世,与真正的绝世还有着不小距离。
所以斗篷人心里清楚,自己绝非聂海峰的对手,与其做那大肆宣传激励人心的无用功,不如瞒下自己秘密铸金身的信息,以后未必不能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于是道:“邪后的计划我们虽然不参与,但你也要盯紧点,日后未必不能从中摄取些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