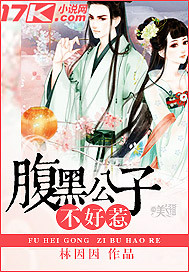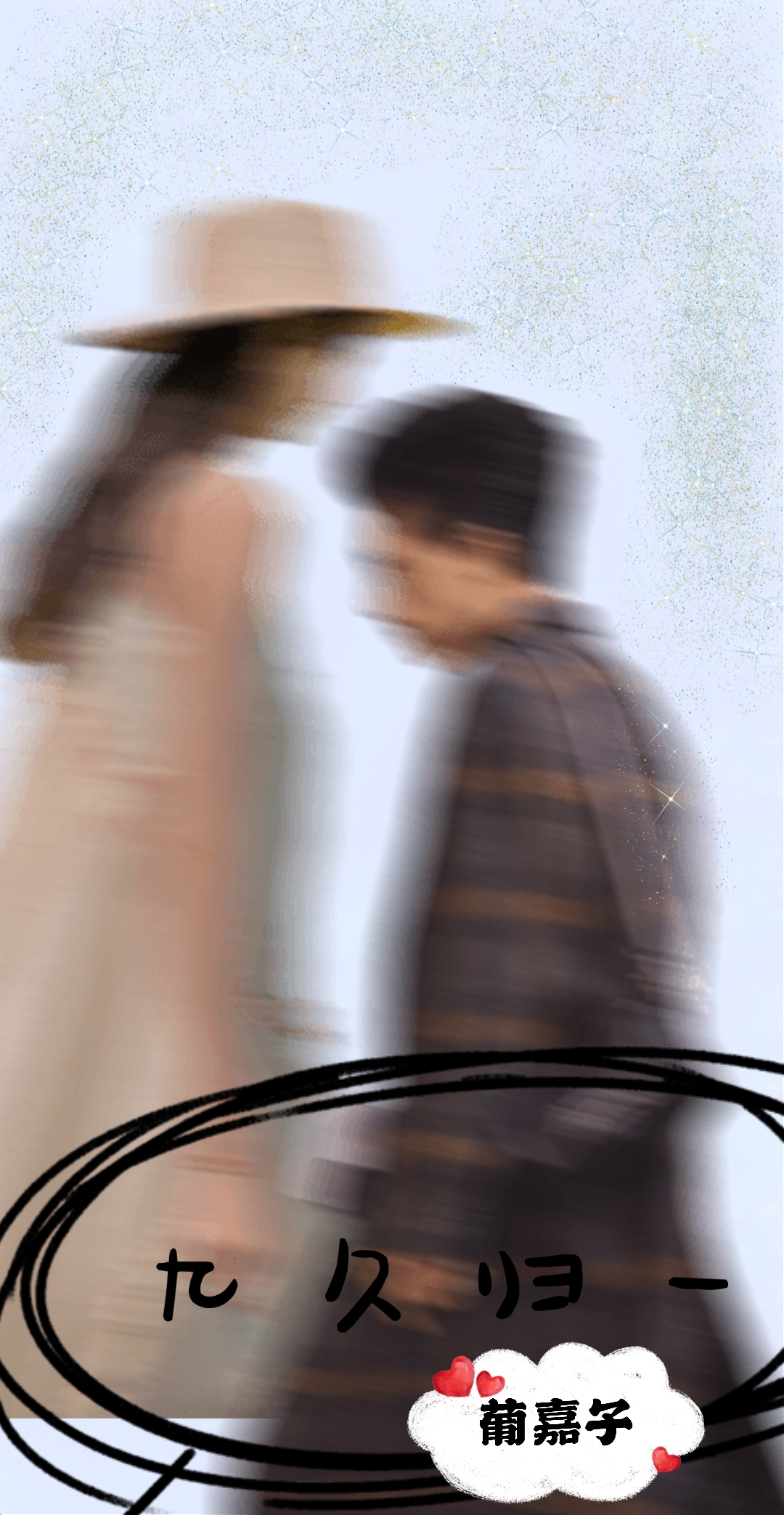昨夜的御书房,一夜灯火未熄,屏退了一干伺候的宫女太监,年轻的帝王端坐在案前,神色莫名,期待,隐忍,晦暗,总之是说不清道不明。
堆积如山的奏折宫人早已收拾好,有条不紊地放置在案前,仔细一看,好似更多了些。可年轻的帝王却只端坐着出神,目光游移,落在大气恢宏的柱子上,落在雕花繁复的屏风上,落在那副大好河山的画上,或者落在灯火摇曳的烛台上,就是不落在折子上,好似这雪花一般的折子是洪水猛兽,只能避着,不能迎头而上。
寂静的夜里,年轻的帝王低声呢喃,“萧钰……”忽地轻笑出声,往日的种种皆浮现在心头。自幼他便是众望所归的太子,可是他不够聪慧。也不是他不够聪慧,是有人比他聪慧,这人彼时萧钰。
小小年纪便心高气傲的太子,如何能忍受太傅在学堂上夸奖的是他的陪读萧钰,而不是他自己?如何能忍受太后,便是自己的父皇瞧见萧钰时眼底的温和和赞赏,全然不似对他的严厉。又如何能忍受自己心心念念的小姑娘心里眼里都是萧钰,见之欢喜,而不是对自己的那般的毕恭毕敬,但是后来,那女子到底成了他的妃,便是那清冷孤傲的慕容惠妃。
其实,原先的慕容惠妃是娇俏的。而慕容惠妃也对谢长安下手了,不是为着旁的,只是求而不得的嫉妒。只是为了给清冷的宫殿里,自饮自酌,一醉方休的往日一个交待。
孩童的世界能有多大?一花一枝便是一世界,一尘一土便是一世界。而满腹怨气的小太子的全世界,便是要让萧钰消失。后来,他也确实这般做了。他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将萧钰推下假山。以为大功告成时却发现萧钰并未摔死,惶恐之后又得了萧钰傻了的消息,立马心安,私以为老天爷是同意自己的。
直到如今,偶然得了萧钰只是装傻扮痴的消息,沉睡多年的心魔再度苏醒,愈发猛烈,直到今日的至死方休,毕竟他不是畏手畏脚的孩童了,也明白了什么叫永绝后患,也想从此高枕无忧。
现在,他在等,再等一个让他期待多年,却隐有失落的消息。
手不由自主地抚上一旁的玉玺,嘴角方才露出笑意,是真心实意的笑,不是见着太皇太后强装恭敬的笑,不是见着太上皇带了点惧意却硬撑着的笑。拿起玉玺在眼前欣赏,威风凛凛的龙,笑道:“这江山,是我萧家的,更是我萧浩瀚的!”
烛火已燃烧至末尾,烛泪盈满烛台,御书房内影影绰绰的烛光不由暗了几分,平添了阴森的气息,莫名有些凉意。
忽地有人推门而入,年轻的帝王眸子蓦地一亮,目光灼灼地等着那扇开启的门,瞧见正是等待已久的人,面上的喜意更甚,不着急询问结果如何,却是仰天长笑,好半晌方才敛了神色,“如何?”
“回皇上,幸不辱命!”
“可是处理干净了?”
“蛛丝马迹不留!”
得了期盼已久的消息,皇帝面上却无半点喜意,而是怅然若失,良久,方才抬头看向案前之人,到底还是浮现了几丝笑意,“好,朕知道了,你且先下去歇息,朕先前应允与你的朕心中有数。”
那人退下之后,御书房复又只他空落落的一人,一时间,皇帝竟无所适从,不知自己该做什么,想些什么。忽地不知打哪来的一阵瑟缩的风过,油尽灯枯的烛火立时熄灭,四下黑暗一片,唯有窗外流泻而进的光辉分外明亮,却异常清冷。
许是心虚,皇帝莫名觉得脊背发寒,私以为萧钰并谢长安的冤魂回来索命,忙不迭地起身往外走去,心中兀自安慰着,“朕乃是九五之尊,有龙气护体,怎的会怕这等小鬼!”
不知觉间,皇帝走至慕容惠妃的寝殿,却见慕容惠妃正在自斟自饮,面色微红,眼波流转,红唇微翘,浑身散发着诱人的酒香,与平日清冷孤傲的模样大相径庭。自慕容惠妃朦胧的眸子里,皇帝好似瞧见幼时的娇俏心头一动,上前抱了酒至微醺的慕容惠妃往寝殿去,眼底是毫不掩饰的欲火。
玉臂四处摸索不到就不,慕容惠妃不安分地挣扎着,娇嗔出声,“放我下来,我要喝酒,喝酒……”软香如玉,这一磨蹭,叫皇帝愈发心焦,恨不得立时便一亲芳泽,所幸床榻便在不远,不过几步便能如愿了。
“放我下来……放我……萧钰……你怎么……不要我了呢?”
萧钰并谢长安长驱直入,因着二人的身份不凡,且怕伤着二人,而谢长安又是个中高手,想拦也拦不住,一干人等尽皆默不作声地任由二人驾着车入了宫,径直往太皇太后的慈宁宫而去。
今晨起,太后方才得知安郡王被血洗一时,登时震怒,二话不说地命人自如意殿架了烂醉如泥的皇帝来慈宁宫,雷厉风行的一顿质问,却只得了皇帝梦呓般的几句话,“左右萧钰都死了,皇祖母你要如何便如吧……”话落,竟笑出了声。
闻言,太皇太后并未惊慌,她在萧钰身边放了人,萧钰究竟是生是死她都了如指掌。到底是斗了一辈子且未曾熟的人,岂是这般绵软无力。
太皇太后只是冷笑,苍老的脸上褶皱层叠,却不损威严,周身的气势依然叫人望而却步,眼底出去厌恶,还有失望,恨铁不成钢的失望,不再多说。
不多时,太上皇施施然而至,却再见着不成样的皇帝后沉了面色,只是叹了口气,却再多说,走至太皇太后身旁坐下,“母后,可是在等钰儿?”
太皇太后颔首,深不可测的目光只望着来路。
浑浑噩噩的皇帝闻言立马清醒过来,瞠目结舌,一脸的不可置信,毫无一台在二人跟前自说自话,“不可能的,萧钰分明是死了的,昨夜便死了,怎么会来!”
话方落,便听得殿外有了动静,皇帝立时怔住,双目直勾勾地盯着殿外。太皇太后则是心安,而太上皇又叹了一口。
萧钰携谢长安进殿,身后右风拖着一人进殿。二人二话不说,落地有声地齐齐跪下,面色平静,眼底却有喷薄欲出的愤怒,“请皇祖母,皇伯父为我安郡王府做主!”
“快些起来,钰儿,你这傻孩子,跪下作甚!”语气愠怒,却是心疼,太皇太后忙唤了宫人上前扶起二人。
二人自岿然不动。
瞧见二人眼底的执拗,太皇太后叹了口气,所幸由着二人去。却在叹气时,不着痕迹地瞥了眼见鬼一般惊慌的皇帝,心里好似有了决定。
萧钰面色清冷,目不斜视,脊背挺得笔直,清冷开口,“昨夜我安郡王府,除却我与长安,并几个近侍,一府一百三十八条人命,尽皆命丧歹人的刀下,鸡犬不留,求太皇太后,太上皇为我安郡王府做主!”
“钰儿!”
匆匆而至的忠亲王三人不再多说,齐齐跪在二人身后,忠亲王不语,萧元不语,只忠亲王妃声泪俱下,“太皇太后,太上皇,昨日钰儿和长安侥幸逃脱,可难保有一日便遭了毒手……臣妇自问钰儿与长安向来淡薄,只往安生过日子,可谁知先是被污蔑通敌叛国,昨夜又险遭毒手,谁知……”
“哼!”皇帝怒不可遏,大步走至萧钰跟前,伸手直指萧钰的眼,冷笑道:“向来单薄?只想过安生的日子?那为何要隐瞒早已恢复神智之事?还不是妄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此等狼子野心,朕如何能容?!”
“若不是当年你将钰儿退下假山,钰儿可会痴傻?”沉默了十数年的忠亲王终是开口,眼底是不可磨灭的疼痛,“当年钰儿聪慧无双,你就因着嫉妒就要置钰儿于死地,如今若是让你知道钰儿恢复清明,你又如何?”
太皇太后不语,太上皇不语,忠亲王妃却惊愕,“什么……当年钰儿竟是被你推下的假山?”忠亲王妃悲愤交加,“你好狠的心啊!”
被揭露了不可见人的阴暗,皇帝面色沉了,心也慌了,不过转瞬又恢复目空一切的模样,“忠亲王,朕念你是朕的叔叔,便不与你计较你诬蔑于朕之事。”
忠亲王却是苦笑,“这些时日,你只知怀疑,便一而再再而三地痛下杀手,若是让你知了钰儿已好,钰儿可还活得过明日?”顿了顿,“诬蔑?世人有眼,污蔑与否,旁人都看得清的。”忽然带了些沧桑,“原是念着情分,便忍下了,不想却被反咬一口,当真是个笑话。”
闻言,皇帝羞愤不已,怒目而视,“你!”却说不出什么反驳之话。
“够了!”
太皇太后双眸微眯,斜倚在一旁,手上的佛珠缓慢的拨动着,却半晌没说话,好似在假寐,良久方才开口,“萧浩瀚,你禅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