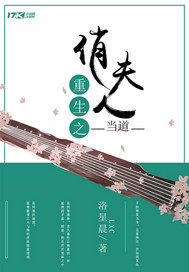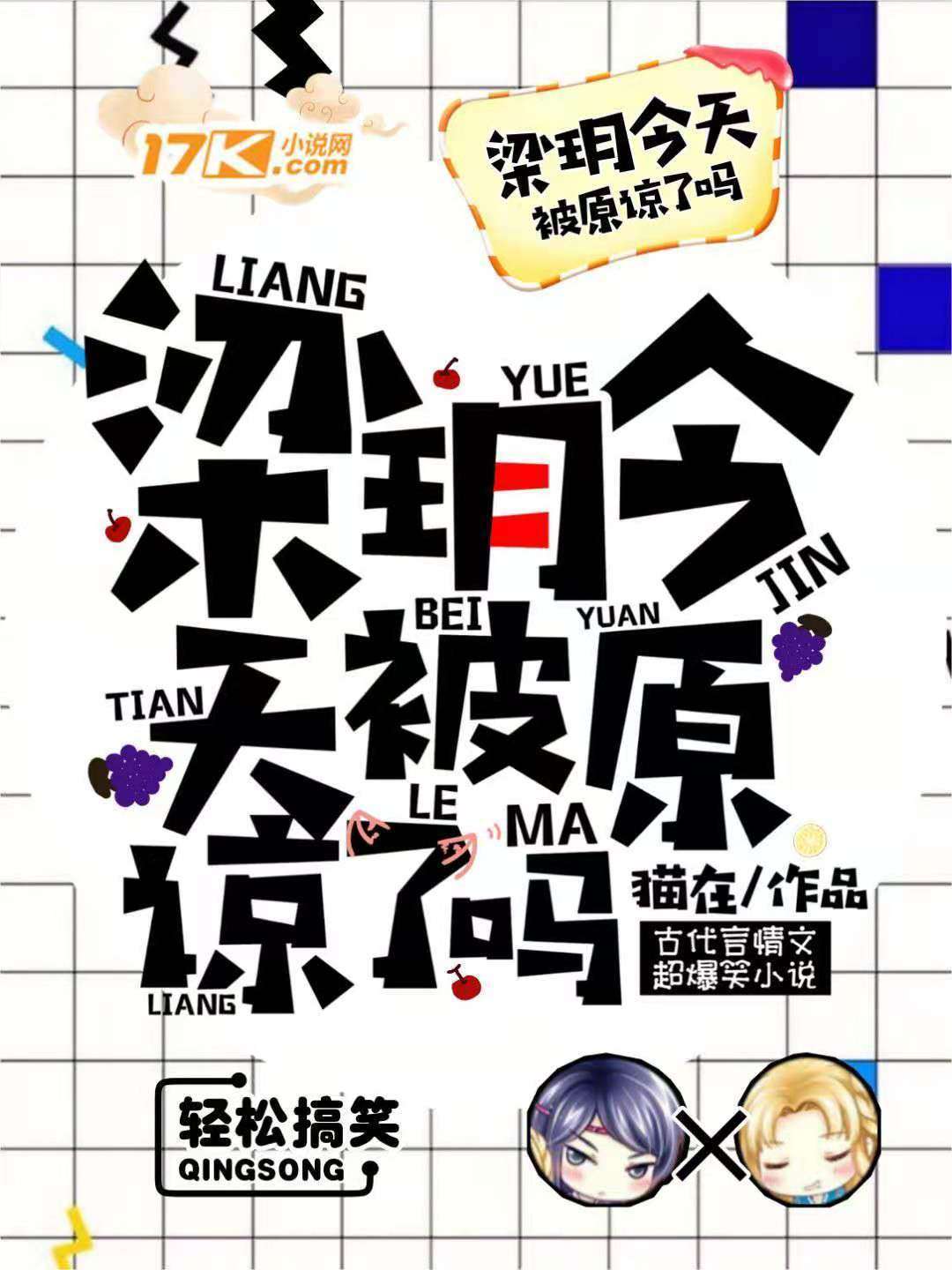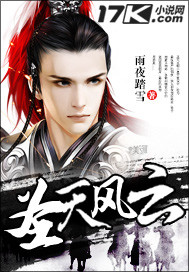夜色渐浓,如墨浸染。不知何时天空竟飘起了鹅毛细雨,她拢了拢被褥,动作轻微的侧过身,大抵是扯到了伤口,她不由吃疼的闷哼了一声。
黑白分明的眼睛掠过这寂静如厮的屋子,最后定格在紧闭的门上。按理说那变态该来了啊!怎么半天没点动静?难不成不来了?
眉梢一挑,罢了罢了,不来更好,这样她就能安心睡觉了,思及此,她打了个哈欠,便闭上了眼睛。但不知为何,原本的困意竟消失殆尽了,心中更是莫名有些烦躁。
这变态还来了不来了?真是的,不来了,还折磨她。她坐起身来,眉头紧皱,烦躁不安的揉了揉头发,心中万般诽腹。
忽然之间,她听到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紧接着越来越清晰,不知为何心中竟有了丝丝的悦色,忙不迭的躺下,狡黠万分的瞧了眼影射在门上的影子,她嘴角微微一勾,闭上了眼睛。
他依是带着那副罗刹面具,轻轻地推开房门,瞧了眼床榻上的人儿,转身便关上了门。
站在床榻前,他的清眸拢了一层别样之色,望着她面色苍白、安安静静的躺在床榻上的模样,不知为何他竟有些怀念她聒噪的时候了。
怀念吗?敛了敛眉……不……他只是不想这把还未出鞘的剑折了罢了。思及此,他眼底的温柔之色尽敛,徒留清冷微凉。
她虽是闭上眼睛的,但却能感受到他就站在床榻边,听着半天没动静,她心中疑惑,不由眯眼瞅了瞅,只见他就跟个木棍似的杵在床榻前。
这变态想干嘛?
这里正疑惑呢!他一摆衣袍坐到了床榻上,掀开被褥,便将她抱到了怀中,似怕弄痛她一般,他的手异常的温柔。
掀开被褥的刹那,她尚且有一丝冷意,可下一秒便入了他的怀中,这一次她闻了出来,他身上那股淡淡的清香便是薄荷的味道,微凉的大手透过薄薄的亵衣传到了她温热的肌肤上,合着那股清香竟像传到了心尖上,让她不住的微颤。
就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心想一定是这变态的手太凉了,而她一向怕冷,所以才会萌生出了那种奇怪的感觉。对,一定是这样。
思及此,她的心底又恢复了一片清冷无虞。
察觉到她的身子有颤意,他眉头一皱,便加快了上药的速度。
上完药,给她盖好被褥后,他不余一丝留恋的转身欲走。
见他要走了,她睁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嘴角微微一勾,轻轻地掀开被褥,动作轻缓的爬起身来,一个跃身便跟猴子似的挂在了她的身上。
“师傅大人。”她禁不住笑意的甜声唤道。
他的身子微微一震,下意识的顿住了脚步,垂眸瞧了眼勾在脖颈上的小手。
“下来。”他不咸不淡的声音,听不出一点波动,然而没人知道他心底的温浅笑意。
“不下。”她眉梢一挑,面上皆是玩味。手更是不甘示弱的收紧了几分,犹如藤蔓一般不依不饶的缠着他的脖颈。
闻言,他的眼底掠过一抹阴影,猛然抓住她的小手,她漆黑的瞳孔微微收缩,下意识的尖叫了一声,这个变态想干嘛?正想着她的身子便飞旋了起来,片刻,她已经被他打横抱抱在了怀中。
她惊魂未定的抬眸望着他,下意识的咽了咽口水,刚刚她以为他要将她甩出去了。
“怕了?”望着她跟葡萄似的眼眸,他嘴角含笑,却声音清冷如厮,甚至透着一股淡漠疏离。
废话,她能不怕吗?她心中默默翻了个白眼,面上却是笑意盈盈,比花娇。
“徒儿还是比较惜命的。”
言外之意,我当然怕了。话落,勾着他脖颈的手不由收紧了几分,似乎便是在应证她的话一般。
“贪生怕死。”他不屑一顾的嗤道,眼底却浸染了笑意。
“徒儿这叫爱惜生命。”她于情于理的反嘴。
“下去。”他再次冷声警告,仿似她在不下去,他就要教训她的感觉,然而抱着她的手却未松开,更是下意识的怕她摔下去,而悄悄地收紧了几分。
此时此刻,他真是将口嫌体正直这个词演绎的淋漓尽致。
她撇了撇嘴,瞪了他一眼:“徒儿有伤,不能着凉。”
听语气便是在责怪他,不懂得体恤她一般。他面无表情的抽了抽嘴角。
灵光一闪的转了转眼珠子,她突然张口就啊了一声。这一声叫的猝不及防,饶是淡漠如水,稳如泰山的他,都不禁被她吓了一跳。
“怎么了?”他关切的问道,只是那声音却冷的能结冰渣了。
“我冷。”她可怜兮兮的耸拉起了小脸,委屈至极的往他怀里缩了缩,就跟调皮的小猫似往他身上拱。
他狐疑的垂眸瞧了她一眼,见她仿似冷的不行的模样,心想这也没多冷啊!难不成是这小狐狸在使什么花招?不过,转念一想,她身上还有伤,穿的尚且单薄,而此刻屋外飘起了小雨,的确是有几分冷意。
于是眉宇微微一松,却将她抱的更紧了,然而他却没发现她眼底的泛滥的狡黠,一个转身便将她放回了榻上。
见他转身又想走,她抿了抿唇:“师傅大人,徒儿还是很冷。”
侧眸回看,只见她眉头一皱,嘴巴扁得跟鸭子似的,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他闭眼一瞬,颇为头疼的揉了揉太阳穴,无奈的转过身。又扯了几床被褥盖在她的身上。
她的额间滑过三条黑线,嘴角万分无语的抽着,这变态简直就春风不解风情啊!她这暗示都那么明显了,竟然还能如柳下惠一般,坐怀不乱?
“师傅大人,天冷,不如一起睡啊!”她笑眯眯的眨了眨眼睛。她这可是直接开门见山了。
绕是他在笨,也懂了她的意思,于是眼底不动声色的掠过一抹阴翳,这小狐狸又在打什么歪主意?
“本尊对豆芽不感兴趣。”他面无表情的打量了她一眼,着实的嫌弃。
唔!她是豆芽菜?有没有搞错,他眼睛长脑门上吗?明明她要胸有胸,要屁股有屁股好吗?虽然不是那么明显。
再说这变态想哪里去了,她不过是觉得他帮她报了仇,解了口恶气,所以想感谢他一下的,不过算了,就他这理解,怕不是以为她想献身啊!
“巧了,徒儿对竹竿也不感兴趣。”她笑眯眯的打量了他一眼,毫不示弱的道。
一个男人最怕便说被一个女人说不行,于是他的脸一下子黑得很彻底,这小狐狸的胆子真是越发的大了,思及此正想掏鞭子给她点教训,不过想到她身上的伤,便就作罢了。
“哦?那你对什么感兴趣?”他不怒反笑,但怎么听都觉得很是阴测测的。
虽然他带着面具,看不到他的神情,但那股冷意却让她下意识的拢了拢被褥,皱了皱眉,她怎么突然觉得心头有点凉呢?
“当然是身强力壮的,反正不是你这麻秸秆似的。”她故作思付了一番,而后万般真诚的道。
“那下次我们试一试一夜七次如何?”他阴阳怪气的道,更无端的透着一股高深莫测的诡异。
不好!她心中警铃大作,这变态要是动了那心思那还得了?再则她是要谢他帮她报仇之事的,怎么扯到一夜七次来了?
皱了皱眉,她懊恼的吁了口气:“师傅大人天人之姿,阳刚威猛,别说一夜七次了,就是十次,那也不在话下。”
望着她满面笑意如春风,眉飞色舞、万般绉媚的拍马屁,嘴角竟禁不住的微微勾起,不过这话他听着有点怪呢?什么叫一夜十次不在话下!她当他是种马吗?思及此,他的笑意尽敛,徒留清冷。
“阿谀奉承。”他不屑鄙夷的嗤笑一声 眼眸不由危险一眯。
“嘿嘿,徒儿是实话实说。”她讪笑着眨了眨眼睛。心中却是不由松了一口气,幸好这变态没什么非分之想啊!否则她还真是砧板上的鱼,任人宰割啊!
为了避开这个敏感的问题,她转了转眼珠子道:“对了,这是感谢师傅大人的。”
说着,便撑着身子从枕头底下摸索出了一个绛紫色的荷包,随即便顺势扔给了他。这荷包是她白日里绣的,时间匆忙,她只绣了一些简单的图案。
本来是想等绣好再给他的,可谁叫现在刻不容缓呢?她是真的怕他“狼性大发,一夜七次。”
大狐狸岂会不知小狐狸的心思,淡淡的瞧了她一眼,垂眸看了眼手中的荷包,眉头一皱,眼底满是嫌弃:“丑。”
他毫不留情的直接批评,一点都不委婉。
呸,她暗自啐了一口,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眼光,想她上辈子可是声名远扬的江南织女,一绣抵万金啊!这变态真是猪油蒙了心,有眼不识金镶玉。
心中万般诽腹,面上却是笑意不减,粲然如撕:“徒儿觉得紫色跟师傅大人的气质很配,师傅大人穿紫色一定很养眼。”
嘴上说着好话,心中却是骂骂咧咧。
她的好话,他没一句是听进耳里去的,在他看来她的话,不可信,这小东西的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功夫,真是练得如火纯青啊!
“口是心非。”他凉飕飕的拆穿她。
她愣了一瞬,笑的越发粲然如厮:“徒儿说的话比珍珠还真。”
“哼。”他冷声的睨了她一眼,话落便将荷包扔给了她:“换一个,明晚之前给本尊。”
“不……”她瞪直了眼睛,下意识的要脱口而出,但他的眼神凉凉的看过来时,让她要说的话从喉咙口又活生生的憋了回去。
迫于他变态的手段,她是敢怒不敢言。
“好的。”她默默地舒了口气,随即笑的如厮乖巧。这个死变态,除了折磨她,还手折磨她,简直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