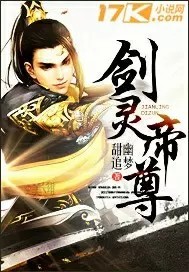有那么一个瞬间,红孤突然感觉自己身不由已,莫能应付自如了,转而又像韩湘子吹笛子,不同 凡响了,他似乎能看到身体里的血液,犹如天河倒泻,一发不可收拾,他的身体简直快要爆炸了似的难受,殊不知,正是内力劲增,势不可挡之时,他的第六感告诉自己,有几双恶狠狠的眼光在某个角落盯着自己,于是他的心神阴冷,恐怖,猛然间,他震天一吼,顿时整个红坡地动山摇,同时四爵布施的苦刻咒的水天屏一下子消失了,四爵遂惊出一身冷汗,片刻歇息,不由的叹道:“好险,好险。”
二爵爷舟陀赶紧护住了怀中双囊中的晚香玉鼬貂、风信紫狐獴,一边手抚一边说:“大乖、二乖,没事的,没事的,小动静、小动静罢了,没事的。”
说着,他左右看看几位弟兄,一回身又瞧瞧身后的众将士,又转回身关切地说:“大哥、三弟、四弟,都还好吧?”
大家都表示并无大碍,只隐隐约约有些干呕,过了一会,便又恢复如初了,大爵爷忻台说:“看洞府的这少年岁数不大,竟有如此能耐,倘若不是我等有洪荒之力,恐怕早已失了魂、丢了魄,不在此谈笑了!”
众人一一点头称是。
三爵爷乐眉说:“水天屏幕中,那个少年应该就是红坡之主,而那石柱被绑架之人,便是昏君葛朗黑聋。”
四爵爷池华一晃天骄猎戟,直指五彩元洞的方向,气冲霄汉地说:“他们就在那里!大哥、二哥、三哥,你们稍作休息,待小弟前去,先收服了他们二人,咋们兄弟便可回营交令是了。”
说完,他刚要提天骄猎戟离去,大爵爷忻台叫住了他,说:“四弟,且慢!”
池华一听大哥叫他,他勒住马的缰绳,夹马旋头,说:“大哥,您还有什么吩咐?”
说着,忻台催马来到他的近前,先是一笑,谨慎地说:“四弟,休要鲁莽,刚才你我兄弟,已经 亲眼目睹,此少年绝非等闲,况尊者一再叮嘱,这么多年以来,都未敢冒犯红坡半寸之地,我想必有他的道理。”
池华一笑,混不吝地说:“怎么?大哥,怕我对付不了那个少年?还是大哥被刚才那一吼吓怕了不成吗?”
说话间,舟陀、乐眉也来到近前,劝池华说:“四弟,大哥说的对,他这也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之前我们有遇到过苦刻咒的时候没有?显然是没有的,这说明,我们面对的是个极强大的魔法师,而且你也晓得,这苦刻咒有个弊端,就是功力的此消彼长,你此一去,万一有个闪失,你让大哥我们怎么在尊者面前说,回苏耶后又怎样给司祖交代?这些后果,四弟不能不考虑啊,我们不能头脑一热,拍马就上阵,这不是个好强逞能的小事,这是战争,战争是谋而后定的大事。”
池华听了顿感惭愧,蓦地,他想起了司祖的话,“倘若遇了事,你们四人可以商量着来,确保万一。”
池华想到这里,便又笑了起来,说:“我听几位哥哥的。”说完,他们重新寻个平原,圈圈画画,又定下了计策。
大火过后,红坡夷为平地,大片林子被烧毁,大批精灵惨死火中,余剩便是残枝断木,满地灰烬,焦头烂额,血肉狼藉。可想而知,一路走去,一股扑鼻的刺激气味,混杂各种乌七八糟的烧焦味极其难闻。闻之,腥臭不可言说。于是,优昙大爵爷安排千人敢死队的一头领,暂时维持红坡外围的井然秩序,然后四人念了咒儿,隐身遁形,径直奔向了五彩元洞。
转眼间,四个爵爷便在洞府前头现了原形。
这时,四爵抬眼上瞧,只见天然石府洞口上书写四个琉金大字:五彩元洞。笔走蜿蜒,栩栩生辉,生灵福地,好生气派。
四爵爷可没雅兴看字,他环顾左右,看有没在外落单的精灵口舌,打探个细情,正寻思不得已时,从远处一瘸一拐地走来一只其貌不扬的幼年花箭猪,它的一只后腿断了,像是被什么重东西压断的。
它又痛又怒,哼哼唧唧地朝洞府走来,池华手持天骄猎戟一晃,一个小小魔法便把花箭猪的嘴给带上了罩,防他惊吓叫唤,与此同时,它被完全困在了一个铁笼子里,脱不得身,越是妄想挣脱,越是摇头摆尾,撞击铁笼,可是无济于事。
其他三个爵爷一看,嘿嘿一笑,四人便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去,花箭猪见有人向自己走来,刚开始有些慌乱。
过了一会,它顿时明白了一切,便不再像刚才那样拼命撞来撞去了,而是翻着黑白不明,朦朦胧胧昏暗无光的猪眼瞅着他们四人,当池华蹲下身,朝花箭猪一笑,说:“花箭猪,我们都是好人,并无恶意,你只要帮我们给你们的大王捎口信,让他把里面擒的那个大胖子还给我们,你给你们大王说随便提条件,你能办到吗?”说完,池华用天骄猎戟在花箭猪后腿受伤的地方轻轻画了一圈圈,倾刻间,它的伤腿痊愈了,花箭猪目神昏视又斜棱了他一眼,连点头答应。
紧接着那花箭猪嘴上戴的罩瞬间不见了踪影,而且铁笼子也消失了,那花箭猪惊喜万分,啥也没说,一溜烟地从他们身边走开,进入了五彩元洞。
过了很长时间,刚才那个花箭猪又风风火火地跑了回来,哼哼唧唧地说道:“我们大王说了,我们没有条件,让你们赶紧离开这里,说……”
乐眉说:“说什么,莫要苏吞吞吐吐,误了大事。”
花箭猪情深意重得说:“我们护者说要不是因为你们辜负红坡,红坡也不至于沦落到如此地步,没有追究你们,便是便宜了你们。念在刚才这位好人帮我医治腿部的骨折,我们花箭猪家族也是知恩图报的家族,刚才我帮你们求护者了,帮你们说话了,但是他把我大骂了出来,所以……长官们莫要怪罪我便是了。”
火爆子脾气的池华一听,顿时就蹦起了大老高,怒不可遏地说:“好个不识抬举的护者,他有什么了不起的,要这样说,今日他就是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你回去告诉他,就说若不答应,今日爷爷就火烧了他这五彩元洞,我看他能把我怎样?”
话音刚落,池华恍惚觉得从洞府**出一道孤魂一般的寒光,直逼池华,说时迟那时快,池华上步闪身,快如闪电一般,躲过了那一道寒光的致命一击。
这时花箭猪连知趣地躲到一边去了,人微言轻,它可不想做什么重于泰山的事,或有吃里扒外的嫌疑,它只是一个小小花箭猪。
众人不住挺身观看,深更半夜,看不真切,但见不远处有一无头女娃,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洞府前头,正怒目而视盯着池华,字正腔圆地说:“刚才就是你说要火烧了五彩元洞吗?”
在黑暗之中,这一如娇似妖,柔中带煞的声音乍一听似莺雀出谷,凤鸣鸢啼,清亮却又柔和;再一听去,却又如那风起云涌,惊涛骇浪,猛烈而又震撼;仔细一听,只觉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令人心惊胆寒捉摸不定,真是个夜色明目,流声悦耳的年华!
大爵爷忻台虽是个稳重的人,却也着实吃了一惊,厉声喝道:“什么人?”
话音一落,只听见一个女人银铃般“咯咯”的笑着,这笑声一会儿忽东,一会儿忽西,一会儿忽南,一会儿忽北,令人弄不清楚声音的发源方位。
四爵赶紧背靠背预备一人把住一个方位,防备对手背后偷袭。
三爵爷乐眉说:“我记得很多年前,在泰亚上学那会儿,我听安徒提教授曾在雷雨课上讲过这样一个魔法,叫柳仙斗雷音。”
据说,世上有一种灵蛇,能自动长出蛇头,极有灵性,行动诡谲,常人不知所踪。灵蛇最怕雷雨,分辩不出雷音方位,避之不及。
因为它每听到一次雷响,便会迟一年成仙,苦恼至极。
后来它灵机一动,计上心来。灵蛇拜见了闪电婆,向她说起这事,拜托她帮忙想个办法。
闪电婆是个热心肠、风风火火的人,她听了以后,深表同情,说,下次在雷公打雷之前,我先打个蛇形的闪电,意思说要打雷了,给你留出空闲时间做好准备,这样你就不会听到响雷了。
古人言:日积月累,自然纯熟。那灵蛇听觉,却变得异常迟钝,不能接受空气传导来的声波,久而久之,听觉系统便退化了,只有内耳,失去了外耳、中耳。
这时,二爵爷舟陀一笑,不屑一顾地说:“三弟,什么柳仙斗雷音,我们几个大男人合伙去斗一个娃子,还是女娃儿,若传出去会笑话咋们的,说咋们欺负一个女顽童。不如这样,我让我的玉鼬貂、紫狐獴去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咋们腾出手去对付那个不世少年。哦,大哥,我突然想起一个事,你觉得那少年眼熟吗?我看他的眼光极像牧竖王子。”
忻台打断了他,说道:“西伯不管了,一会再说!先把这个娃子对付了,否则我们寸步难行。”
说着,舟陀一伸手,把玉鼬貂、紫狐獴从怀囊中掏了出来,说:“大乖,二乖,你们的听觉、嗅觉是超乎一切的,我需要你们把刚才那个声音找出来,把他给我擒住了,但不能致人一死,知道吗?”
两个灵物点了点头,舟陀满意地一笑,说:“去吧!”说完,它们三蹦两窜不见了踪迹。
忻台一回头,问舟陀道:“二弟,你刚才说什么像,像谁?”
舟陀一听,一时没反应过来,愣了一下,说:“哦,我是说,刚才在水天屏幕中,你们发现没有 那少年有些面熟吗?是不是特像一个人,牧竖王子?”他这么一说,大家细细一想,还真是觉得有些地 方相像,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大爵爷忻台暗道:“在苏耶城时,我仿佛听司祖说过,牧竖王子还有个哥哥,叫阿沃厄?蒲松?牧竖,难道是他?假如真是这样,这事说好办也好办,一个杀父仇人在他手上,又岂能善罢甘休。说不好办,葛朗黑聋这鸟人在他的手上,却又不在我们的手上,把柄他攥着,这事就有些难说了,他不给,我们便抢,倘若将来他们弟兄相见,四爵必会留下怨结,徒增烦恼而已,这又怎么办?真是急死我也。”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在不远处,只听见二灵斗的天蛾人,打的那叫难解难分,真是撕心裂肺,怪叫连天。
四爵爷池华见状,早已激情四射,按捺不住,大声说道:“大哥,还等什么呢,我们还不冲进那洞府中,更待何时?擒了那少年,一问便知,他如若不然,先打他个翻覆。”
忻台把眼一瞪并嗔怒道:“休要啰嗦!你可知那少年是谁?据我所知,他十有八九是牧竖王子的亲哥哥蒲松王子,你说我们打还是不打,池华你说?”
看样子,忻台真急眼了,这时,三爵爷乐眉上前劝场,说:“大哥、四弟休要伤了和气,让外人岂不看了笑话,有百害而无一利,对吧,二哥?”
舟陀走到池华近前,轻轻捶了他一拳,说:“四弟,不能跟大哥这样说话,大哥是有他的考虑,
今日我们就是擒住了少年,待日后我们兄弟四人如何在牧竖王子面前交代,毕竟他们是亲兄弟,有些话是不能说明白的。好了,跟大哥说个不是,去。”
说着,舟陀推了一把池华,他来到忻台的面前,低头说道:“大哥,我错了。”
忻台在他的结实的胸膛轻轻打了一下,一笑,坦诚地说道道:“好兄弟,哥哥不该给你坏脾气,莫怨恨哥哥,我必须考虑周全些,因为人生旅途中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免得我们兄弟日后落下祸根,你能理解哥哥的良苦用心吗?”
池华惭愧地说:“是,大哥,我知道了。”
四爵大喜。
三爵爷乐眉说:“大哥,那接下来,我们如何招呼?”
忻台沉吟一下,斩钉截铁地说:“先礼后兵。”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二弟,先唤玉鼬貂、紫狐獴回来,我来和他们对话。”说完,二爵爷舟陀抬手朝天空吹了两个响亮口哨,不一会工夫,两个灵物乖巧地窜回到舟陀怀里,温存慰劳自不必絮繁。
“姑娘,刚才多有冒犯之处,还望姑娘不要与我等一般见识,不知鄙人说话,姑娘能否听得到。”
忻台说完,先施了一礼,停顿一下,无人搭话,接着他开诚布公地说,“我先自报个家门,我们一行兄弟四人,这三位是我的三个兄弟,刚才,有言语不周之处,还望姑娘恕罪。今日我们到此红坡,并无任何要挟红坡之意。或许姑娘有所不知,现如今,天下纷乱,群雄揭杆,大黑城昏君腐败,百姓民不聊生,我等奉牧竖王子之命,擒那贼昏君,以立明主,望姑娘把此意传与护者,把葛朗黑聋押向人民审判的断头台,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中,解黎民之翘首以盼,安得促膝,说彼平生。”
秋夜,一缕凉风袭来,阵阵清爽。
这时,有两个人影,一前一后,从洞府中缓缓走了出来,为首的是一名少年,四爵定睛瞧看并惊喜,不错,正是刚才水天幕中见到的少年,而身后便是那个的冰冷女娃。
忻台暗道:看来刚才的语言起了作用,这第一步算是和平迈出了。
忻台一施礼,拜说:“尊敬的阁下,四爵深夜造访宝地,万望海涵,然多有冒犯之处,全赖护者恕罪。”
接着舟陀,乐眉,池华弗拜。那戴红帽的少年虎着脸,狠歹歹地瞧了四爵一眼,突然冷冷地对忻台说:“你是何人?”
忻台一抬头,只见面前站着一个少年,看那少年身长八尺,紫衣罩地,头裹红巾帽,脚着草莽鞋,面如重枣,唇若丹霞,神龙眼,火狼眉,一戳一站,威风凛凛,不可侵犯。
忻台暗道:好个独立特行的少年!说,“回护者,我等四人本是苏耶人,奈何我家主人被欺,常 闻大黑城的昏君倒行逆施,欲与伐檀行杀孽取珠荒谬之事。义者云:路见不平有人铲,事见不平有人管。我苏耶人便联合伐檀同命子民,助牧竖王子行天命,诛昏君,得清平寰宇,澄颠沛流离。”
忻台在说到“牧竖王子”四个字的时候,他故意提高了嗓音,察言观色,很明显,那少年的身子不禁地晃动了一下,深邃的眸子中夹杂着几分呆滞。
毋庸置疑,他起码听说过牧竖王子。
忻台趁热打铁,意犹未尽地说:“护者,现在贵府邸中,那石柱上被押之人,便是牧竖王子的杀父仇人的弟弟。我曾经听牧竖王子的舅公西伯老师说,牧竖王子的亲生父母,自从十多年前,天宫城国破家亡,被那贼首追杀一别后,至今杳无音讯,生死未卜。苦命的王子,还有个同胞兄弟,却又不幸遗失了很多年……”
情到深处,忻台假装哭泣,却偷眼观瞧,那少年明显有些心伤触动,目光呆滞,黯然神伤。
这时,三爵爷乐眉不失时机的说:“护者,你知道牧竖王子多么想念他这个亲哥哥吗?说了护者也不会相信?他已经中了贼人的咒了,三年了,三年了,他隔一段时间便发作一次,可是王子没有一次说过痛。我记得有一回,听西伯老师说,牧竖王子一直都很坚强,每当那咒儿发作,疼的他满地翻滚,但是王子嘴上却不停地喊着,哥哥,哥哥,我知道你还在人世,哥哥,哥哥,我知道你还在人世。”正在这时,那少年似忍不住,冷不丁地怒说:“为甚不给他除咒?”
与此同时,忻台怕有闪失,赶紧接过话来,深情地说:“护者息怒,护者有所不知,我家主人便是牧竖王子的老师。三年前,是我家的主人帮着王子一天一天养护身子,奈何去除不了根本,也是此个原因,我家主人特别嘱咐我们兄弟四人对牧竖王子的身体要留心观察,并且寻找破解婆罗林下的解药,只图将来。”
红孤说:“你们起来吧,这里黑灯瞎火的,随我到洞府来。”说完,他一扭头径自回了洞府,那女娃随在身后也转身走了。
此时此刻,四爵彼此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简直像在梦魇中一般,不能动弹,又忽地惊醒。倾刻之间,一场水火不容的战争就这样冰消雪融,烟消云散了。
一会儿,战争是一种不问青红皂白的“烈火”,烧他个片甲不留。
一会儿,战争又是一种不可明状的“旋风”,瞬息万变停势头,正所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事已至此,福祸罢了!想到此,爵爷们便无所忌惮了。
他们又沉吟了片刻,一个个大步流星地向五彩元洞走去。
话不絮繁。这次红坡战以红孤的请爵棠下共一叙,双绝四爵会一杰宣告结束。所谓双绝,便是红 孤的否極零儿、吾师剑(巨石化魂成剑)。
而一杰便是魔杰纳兰照明。
照明从半壁坡出来,一路绝尘,便上了红坡。
他拿出七宝风声木,按图索骥,不费吹灰之力,便找见了五彩元洞。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