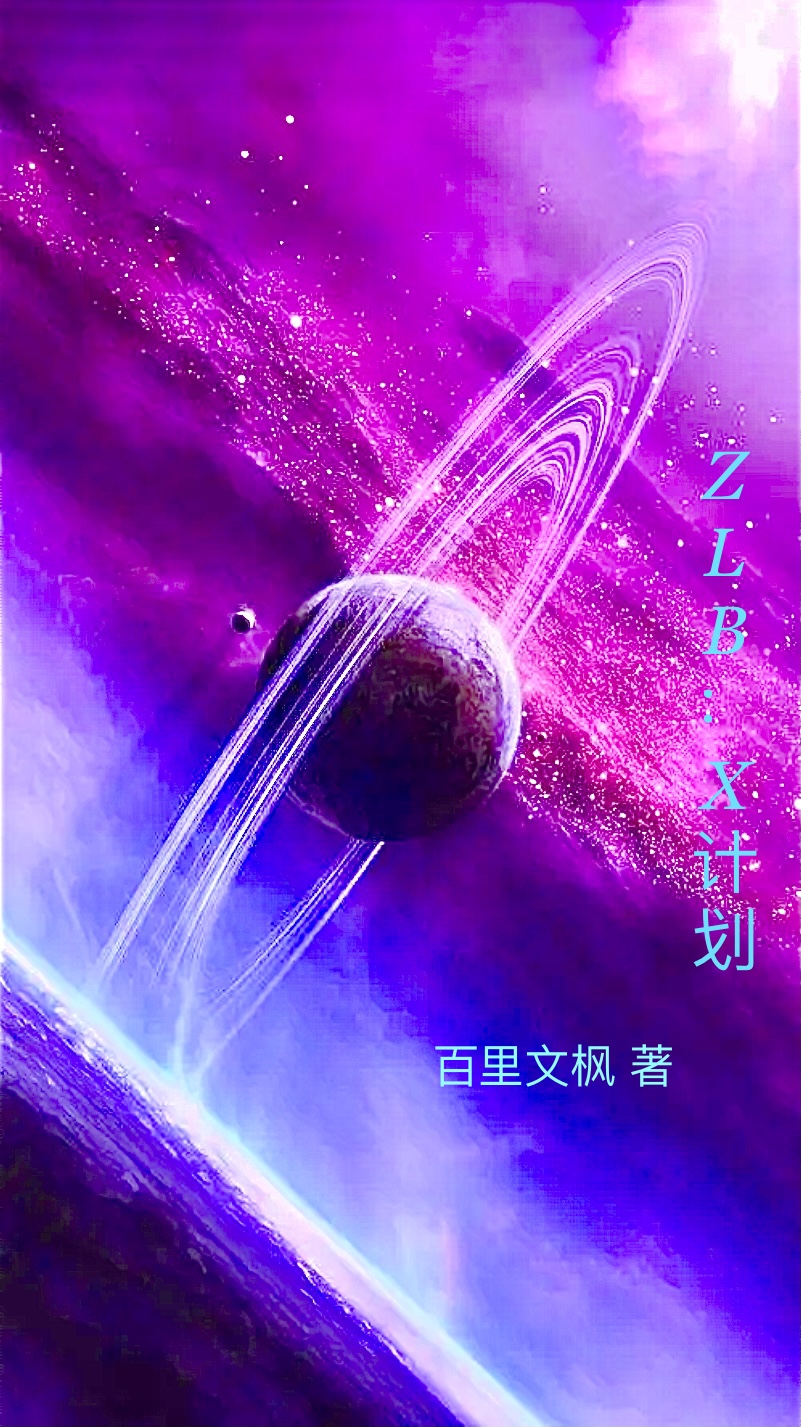“局里的手续都已经给你办好了,出院以后就可以上岗。”
“老爷子那边,你们问过了?”
“嗯,他很支持。”
简单聊了一些,确定白争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樊梨花才带着阿蛮离去,两人有后,宋青树才畏畏缩缩的走进门来,白争喝了一口方才小妮子倒上的水,“怎么想的?”
宋有理同志叹了口气,“那老头儿一过来就说让我负责,你让我怎么办?”
白争一下子从床上弹起来,“你把王滇红那什么了?”
“没有!我一正直的人民警察,公安大学的高材生,?新时代的三好青年,我能干那种事儿?”宋青树激烈的反驳。
“到底是怎么个状况?”
“我哪知道是怎么个状况,早上出去买了两根油条,回来就跟那哑巴碰上了,一照面儿就冲我指手画脚。那是什么地方?我还没弄明白呢,就给局里一懂手语的小姑娘看着了,往外一散,老子的一世英名,算了,甭提了就。”
敢情就连当事人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白争自然也听不出个一二三来,反着问,“你这是打算跟王滇红撇清了?”
“撇清就说的严重了。”宋青树的情绪缓和下来,“我爷瞧我们一家子都不顺眼,不然怎么总想着把我往前线摁,这回倒是破例听进去了,头前还说带回来看看,转头听到是白族的,直接撂狠话了。”
他昨晚给家里打过电话,把这档子事儿认真看待,但是老爹老爷子没一个点头的。凭空在千里之外冒出来一个准儿媳,家里也没正经审视过,在不知道品相的同时,又对自家儿子报以深深的担忧,就如正直的宋老爷子所说,中都的祸害完了,跑边疆去祸害同胞,一万个不行。
白争沉默了一会儿,认真道:“我觉着你还是打个电话过去,问问王滇红那头,到底是怎么回事。”
“问个屁,晌午回了个电话,让局长批得狗血淋头,你就是见不得革命同胞活得长久。再说那老头儿昨天就走了,杨胖子跟我透过风,蹲在门口儿跟个石头一样只进不出,问也是白搭。”
“我的意思是你直接问王哑巴,你打到咱们邬棚镇派出所,白连山在呢,让他去叫人。”
宋青树拧着眉头,“那我就跟他阿巴阿巴?”
“放心,乡里乡亲的几十年了,有人能帮他说话。”
纠结良久,最终摸出了手机。
陈幺接线,等了约莫有十五分钟那头的人员才到位,期间宋青树三番两次的试图用勤俭持家,节省话费的理由挂断电话,让白争的一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给绝了念头。
“喂?在呢,你说,我在这头给你翻译。”白连山接过话筒。
“那个,你帮我问问,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儿,我,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毕竟也是所里出来的,该帮忙也会帮忙的。”
王哑巴只是有口难言,但是听力不差,当即一阵比划,白连山有些为难,“叔,这让我怎么说,您......好好好,宋哥,我就照原话翻译了啊。”
“嗯。”
“你勾了我家闺女,这会儿是要吃干抹净提裤子走人?!”话筒里的声调儿猛然提高,不光是原话,连情绪都模仿出来了。
宋青树扬了扬头,有些尴尬,“别说得那么难听,我跟滇红什么事儿也没做。”
“什么事儿也没做?你还想干什么事儿?把我家姑娘迷得魂儿都找不见,这个责任你不负?不负我赶明儿还去!你能躲一时,还能躲个一世?”白连山几乎没有任何修饰,这就是王哑巴要的效果。
从宋青树的角度上来说,男女之间没有发生床上关系,就不算有关系,但是王哑巴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连白争都无法苟同的想法,他自然是更加无法认同,眼下这种情况在他的眼里已经是顶天儿的严重了,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
“我不是躲,我跟滇红现在就只能算是朋友关系,压根儿就没发展到那一步,跳度有点儿大,我这一点儿准备都没有。”
“你这意思是说你打一开始就没想要过我闺女?那你早前是吃了什么狗屎动了歪脑筋?撩拨完就算过了干瘾了?”
“妹子,你别哭,别哭,你有什么话,你就说,你说。”白连山语调一改,话筒那头传来清晰的抽泣声,应该是王滇红。
作为女方,以前要面对父亲的施压,往后要面临乡亲们的笑话,承受的苦楚可想而知,但是她从来没有在宋青树或者白争面前提起过,每次看到她,脸上挂着的都是柔和的笑容。但是今天,坚固的心理防线在宋青树的辩驳下彻底崩塌。
“宋哥,我,我......我没事儿。”好不容易止住眼泪,却又不知道如何诉说心里的委屈,半天就憋出这么一句话。
宋青树舔了舔嘴唇,倘若是直接倒苦水,他还真不吃那一套,王滇红这句话,正中他的软肋。
“叔,不能打,不能打!”电话那头再次嘈杂起来。
白争跟着有些紧张,王哑巴对自家闺女向来宝贝,从不见打骂,这回算是动了真怒了。其实这事儿要怪还真的怪宋青树,花花性子占七分,无知占三分。白族男女之间的恋爱几千年来都是轰轰烈烈的,两方有意,即使是一见钟情,那也是非他不嫁,非她不娶。在这种大环境的熏陶下,白族子女中不乏对待感情十分偏执的,就比如眼下的王滇红。在她的观念中,自己并不是被宋青树的花言巧语给迷惑,而是通过那些花言巧语,结识了一个自己一直在等的如意郎君。
宋青树到这会儿还带着三分懵,完全没有搞明白这次事件为什么一点儿的先兆都没有,一下子就赶到脸上了?
“滇红,你是怎么想的?”
“我......”王滇红声音微微颤抖。
“你要是觉得,我还凑活,我就娶你。”宋青树的表情十分严肃,严肃得如同他决定和白争一起离开繁华的中都远赴滇南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