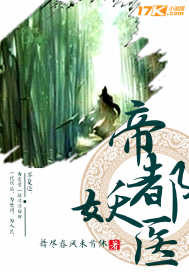却说杨雁翎在千钧一发之际,以射日神箭逼开焱雀,救了白妤一命。但受神箭迸发的气浪冲撞,仍旧让她受了不轻的伤。
杨雁翎见身后徒儿面色苍白,摇摇欲坠,心上实是担忧。但敌人当前,也不敢分心去扶,只紧紧握着手中神兵护在她身前凝神应对。
果然,焱雀愣神之后,方一抹嘴角血迹,眼中突显凶光,又“蓬”地一下弹起,挥动匕首疾向杨雁翎扎来。刀锋寒芒闪烁,凶狠万状。
杨雁翎微微一惊,旋也冷哼一声,抖开架势,将铁杆兵带起一片狂风,迎头就打。
但焱雀仗着身形迅捷,这一下竟不退避,反就将身一纵,轻轻跳上铁杆兵,旋急迈两步,手中短刀刷地直奔敌人咽喉。
杨雁翎见状,眼神一凛,暗道一声:“好个利害的丫头!”慌忙把脑袋后仰,在毫厘之差间避开了那夺命的刀锋,同时双手用劲,把棒头向上挑去,要将对手摔下身后来。
焱雀倒也干脆,见得一击不中,紧接着脚下顿虚,忙借力在铁杆上用力一点,顷刻间整个人已旋转着飞上半空。
但见她腾起丈余,却又卷土重来,把小腿一弯,将膝尖对着杨雁翎脑袋猛然击下。
杨雁翎眉头大皱,暗道自家与这女子无冤无仇,怎的对方如此不留情面,一出手就是连环的狠辣杀着?
连忙也抬起右腿抵着焱雀膝盖,手中倏忽一抓,截住了她接踵而至的握着弯刀的腕口。
焱雀见自家凌厉招法不奏效,反而被敌人捉住,不由吃了一惊。连忙挥动左掌又向杨雁翎面门拍来。
但杨雁翎早有防备,心念一动,铁杆神兵立收。同时左手瞬息探上,仍旧把她一掌抓停。不待她甩出左腿,抢先用力向下一拽,将其“砰”的一声重重摔在地上。
焱雀不及反应,早被敌人扑身而上,将两个小腿曲着压平她二条大腿,紧接着手上被猛力一推,那柄雀嘴匕首锋利的刃口已紧紧贴上了自家喉咙。冰冷的寒意立时传遍全身,惊得她魂飞魄散,面色苍白,忍不住流泪,闭目等死。
可是待了片刻,却不觉尖刀割破喉管的痛楚。
焱雀微微疑惑,急忙睁眼。就看到杨雁翎正冷着双眸盯来。惊疑之间,忽见他冷哼一声,竟松手放开自家身子站了起来。
焱雀得脱束缚,有些不大相信,连忙爬起来迅速后退几丈。
但杨雁翎竟不再理睬,自顾自转过身把白妤轻轻扶住,道:“你怎么样,没事罢?”
白妤听得微微摇了摇头:“我……没事儿,师父。”又转头,微微紧张地看着焱雀。
焱雀见得面色显是大不好看,却不由自主地朝他背影深深地看了两眼,忙就一个猛子扎入半空,头也不回地向北疾飞而去。
白妤才松了口气:“方才……是我急不择言,对不住……”
杨雁翎摇摇头,温和一笑:“不必往心里去,我们先寻个地方给你疗伤歇息罢。”
白妤点了点头,便随他一同转身。却又瞥见那躺在地上的公子,微微迟疑道:“那他呢?”
杨雁翎道:“此人作恶多端,自有老天收拾。莫管他了。”
白妤闻言,轻轻“嗯”了一声。
杨雁翎见得徒儿终于顺从,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就将臂膊扶着她两肩微微一托,一块儿纵身跃上半空来。
正要御动法器飞离,忽的却听的脚下水面有声音道:“恩人留步!”
二人闻声看去,只见小舟上男女二人正站在船头大声招呼,便轻轻落下船蓬,道:“何事?”
渔夫见得,急忙拉渔妇一块拱手拜了拜,道:“小人夫妇今日外出打渔,无故遭金人追杀迫害,若非二位恩人,只怕早已没命了。小人无以为报,但欲请二位恩人到家中歇息二日,聊表谢意。”
杨雁翎闻言,向白妤微微颔首,就转头向渔夫道:“多谢,麻烦您了。”
渔家夫妇大喜,请下蓬上二人,连忙棹桨摇橹,把渔船直奔南岸。有半个多时辰,早到了渔村码头。
杨雁翎见渔夫跳下船,把缆绳紧紧缚在木桩上,就扶了白妤先下来。
二人站在岸旁,放眼一望,黄河的雄奇伟岸,波澜壮阔顷刻尽收眼底。
只见河面蜿蜒崎岖,宽广无边,望不到彼岸。河上不见远帆,阒无人迹,只见水天相连,无尽邈远。
目之所及,但看河水饱满汹涌,苍苍茫茫,混混黄黄。
因其厚重,流动之间不翻浪花,只有连绵漩涡汹涌;因其宽宏,奔腾之时悄无声息,却响彻中华千年韵律。正是派出昆仑五色流,一支黄浊贯中州!
又见脚下草青葳蕤,眼前水黄肆意,河上轻雾朦胧,天际霞红艳艳,实是浪漫缠绵,让人沉醉叹息,不知归路。足可令鸢飞戾天者息心,经纶事务者忘返。
不多时,那双夫妇收拾了渔网,又把打到的鱼儿用绳兜拾好,便招呼着二人同去家中。须臾,四人已到村尾那一间破旧的土坯茅草屋前。
杨雁翎见白妤面色比之先前更加苍白无血,浑身亦微微冰凉,心上着慌,忙向渔夫道:“兄弟,我这徒儿身子不妥,借你们床榻与她歇息一阵可否?”
渔夫正拉开门,闻言道:“恩公不必与小人客气,快些进去罢。”
杨雁翎点点头:“多谢!”连忙扶着白妤入屋,把她轻轻放在床上躺下。
及号脉时,发现白妤脉搏有些凌乱虚浮,便一提灵力,把手指轻轻压在她掌心。自家精气即刻如河中流水,源源不断输送入她身体之中。
有半个时辰,杨雁翎已是面色微微苍白,身上也稍感疲乏。但看白妤呼吸平稳,沉沉入睡,不由得松了口气。
傍晚渐至,晚秋的夜风始凉。
渔家的夫妇也已把饭菜做好,端在门外桌上,叫道:“恩公,吃饭了。”
杨雁翎正把脸埋在膝盖间小憩,闻得答应一声,就轻轻推了推白妤胳膊:“起来么?我们去吃饭。”
白妤才睁开眼,朦朦胧胧地点点头。
二人出了门,正见渔妇点了炉火过来,道:“天冷了,过来烤一烤。”
杨雁翎点了点头,扶着白妤坐下。四人便围坐一块儿用餐。
渔家的饮食,自然多是取自河中。那微微破烂的木桌上菜肴并不大多,但却也不乏精致。一碟糖醋黄河鲤,一小碗河虾,几条煎鱼,几根大葱。红的鲜红,黄的金黄,绿的油绿,火候恰到好处,足可见主人用心。
席间几人也互通了姓名,二人才得知渔夫叫赵大柱,渔妇叫秀秀。他两个都是十八九岁年纪,才成亲不过半年,秀秀肚里亦刚刚怀上孩子。且前月老母因年事已高,得个喜丧,如今家里就剩了这一对小夫妻。
饭毕,天已黑了。众人商议一下,就决定把草屋让给白妤和秀秀住,杨雁翎则和赵大柱睡在屋旁柴棚里。
那棚子紧贴着茅草屋,三面漏风,只有个顶棚,甚是简陋。不过好在地上堆了许多干草垛,倒也挺暖和舒适,足够歇息之用了。
到得半夜,赵大柱忽然道:“杨兄弟,我有些内急,要上趟茅房。”说罢爬起身来,捂了捂衣服,就迈步向屋旁小树林中去。
杨雁翎闻言道声好,闭了眼静静安睡。
这般过了有小半个时辰,才朦朦胧胧听得又脚步声慢慢回来,窸窸窣窣地钻入干草堆中,就不再见任何动静。
杨雁翎睡得正浓,迷迷糊糊地以为是赵大柱归,也不甚在意。
直到寅时鸡叫,他方才清醒了些。但转头一看,就见身旁草窝里空荡荡的却没有赵大柱的影子,只有一件衣服,隐隐约约还传出些血腥味儿。
杨雁翎急忙取了衣服来,用手一摸,但觉其上粘湿,腥气浓郁,确是大滩的血迹不假。忍不住吃了一惊,连忙一骨碌爬起身子就去叩茅草屋门,叫道:“秀秀姑娘,开开门。你家大柱出事儿了!”
白妤闻得连忙起身,但看身旁秀秀沉眠香甜,就先蹑手蹑脚下了床来,打开门道:“师父,出了什么事?”
杨雁翎扬了扬手中衣服,道:“赵大柱这夜中去上了趟茅房,就不见回来。我方才醒来,只看到这条血衣,不知是怎么回事。”
白妤一听也有些惊疑,道:“秀秀姑娘方才怀孕,你先别告诉她这件事儿,以防她惊吓动了气。我就把她叫起来问问。”
见得杨雁翎点点头,连忙转身回屋去。
却方到床榻之前,眼前一幕只将她惊得目瞪口呆。
原来,那原本沉睡着秀秀的火炕之上,此刻竟也是空荡荡的毫无人影!
杨雁翎在门口,见自家徒儿方至睡榻,便转身面色苍白地跑出来,急忙问道:“怎么了?”
白妤惊魂未定,闻言指着房中结结巴巴:“秀……秀秀姑娘也不见啦,方才我起来还看见她睡着的!”
杨雁翎闻言大惊,与白妤面面相觑。
二人虽是修者,不惧鬼神,但今夜所发生之事,却也是处处透露着诡异。便不敢再进屋里去,只一同到柴草棚里坐着打盹儿,等天亮再作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