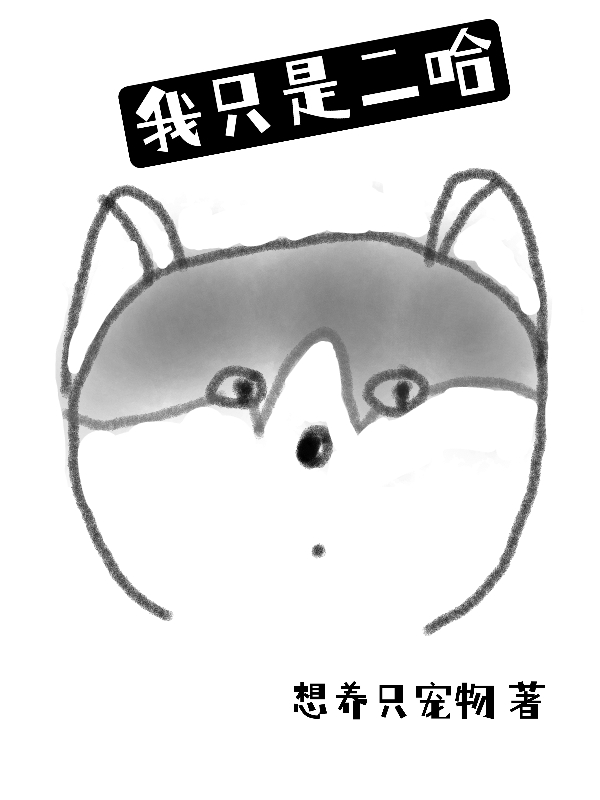是日,魏文琰以宣纸书着魏宴修和魏宴思,而后递到他二人跟前。修儿果真如他所说一般,不怒反喜,乌黑的眸子微眯着,嘴角也噙着淡淡的笑。
却是思思不觉欣喜,脑袋都趴到了桌子上,小嘴撅着道:“思思和哥哥为何要改名换姓?”
一想到思思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性子,独孤慕语终究是没有搭理她,只用了几碟蜜饯果子就把她打发去一旁了。
魏文琰看着心里却堵得慌,直叹气道:“慕语,思思一个女儿家,这般贪食。日后更是不中留,不定哪日便被一叠果子给骗去了。”
听罢他席话,独孤慕语才入口的豌豆黄一时间竟也不敢咽下。她如此窘迫魏文琰全然不觉,紧接着在她的面前摆满零嘴,还贴心递上热茶道:“快多吃些才有气力。”
口中的豌豆黄一早化在口中黏做一团,‘气力’二字惊得她一口气上不来,一时间被呛得是七荤八素。
坐在她身侧的修儿只淡淡地看了她一眼,又埋头凝着手中的书卷,倒是思思一阵小跑而来。到底女儿才最贴心,她才感叹完修儿便淡淡地说道:“食不言寝不语,母亲自找罪受罢了。到底父王的不是,平白的惹母亲说话做什么。”
修儿说时依旧垂着眸翻阅手中的书简,与方才的淡漠言语全然化作一体。这便罢了,魏文琰竟也不替她说话,独孤慕语深感到自己的地位每况日下。
独孤思做什么都是漫不经心的,才关切地问了她几句,紧接着又从里到外地折腾。这会子手里正拎着一张与她齐高的宣纸跑来,远远地唤着道:“娘亲,父王竟藏了旁的女子的画像。”
转眼看着思思口中的罪魁祸首却气定神闲地吓着茶,全然不再意的模样。思思气呼呼地把画推他面前,圆溜溜的眼瞟着他道:“父王朝三暮四,您分明有了娘亲,这画上的人又是谁!父王有了别人!”
“休要胡说。”即便不用看那画中是谁人,她对他也是十足的信任。
思思十分不服气地把那画堆到她跟前道:“娘亲一看便知,太子哥哥家就有许多的娘娘,父王不定哪日也要讨新媳妇。”
思思这小脑袋里究竟装些什么东西?她还未来得及探究,修儿只探头粗浅看了一眼便道:“思思你又在瞎说什么,这画中人分明是母亲。再说,母亲如此凶悍,父王便是有是个胆子也不敢纳妾。”
万恶之源的魏文琰终于不再沉默,“思思啊,你擅动父王的东西便罢了,竟将亲娘认作她人。你说,父王怎么罚你才好?”
那画中绘着个睡眼惺忪的女子,一袭单薄的中衣衬得那人似扶风弱柳一般,仿佛一个晃神便会烟消云散。独孤慕语定睛看了好些会也才认出那是自己,她都如此如何怪得思思了。
魏文琰卷起那副画,神情有些许哀伤:“这是你十三岁那年身受重伤,也是时隔数年后你我再次相见。”
“我竟会有如此孱弱的姿态?”独孤慕语难以相信地问道。
“十三,五岁,那便大思思七岁。”思思掰着手指头数了一番后扬起头望着魏文琰道:“娘亲为何会受伤?伤得可重?如今可都好了?”
至于思思为何不问她而是问魏文琰,答案显而易见,魏文琰于思思而言是父亲也是师长,在思思心中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她只是一个糊涂虫,两袖清风不理世事。
“如今好了也没好。”魏文琰淡淡地答道,忽而对上她的眼,攥着她的手也紧了几分,凸起的茧子不住地打磨着她的守背。
“刻骨铭心,你的所有都有我替你记得,我感同身受。”魏文琰说罢便印上她的前额,深邃的眼一眨不眨地看着她。
“嘭”的一声响,魏宴修舍了手中的书简重重地拍到桌上,神情十分轻蔑地看着他二人道:“父王,幼子幼女均在此,您便与母亲这般耳鬓厮磨卿卿我我,成何体统。”
魏文琰低笑道:“在府里体统不体统的你父王我说了算了,修儿你别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父王休要跟儿子猜哑谜,儿子不懂!”他将最后两字咬得格外重,这也恰恰表明了他知道魏文琰是何意,迷糊着的独孤慕语终于是找回了半分思绪。
他看向各怀鬼胎的两父子问道:“你父子二人可是有事瞒着我?”
魏文琰旋启唇道:“夫人圣明,只是本王不便说与你知。修儿,你说是吧!”末了他又看向修儿,眼底意味深沉不可知。
修儿只淡淡地看了他一眼,便埋头布了棋局,一手白子一手黑子地轮换着。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独孤慕语看了看魏文琰又看看魏宴修叹了叹气。
“整日呆在府里怕要闷坏了吧,不若出去走走?”魏文琰看着正在神游太虚的独孤慕语问道,最先应声的却是思思。
只出去二字便令得思思手舞足蹈地应着:“好啊!好啊!”
思思性高彩烈的声音使得她恍然大悟道:“瞧我整日无所事事的脑袋都迟钝了,一直念着和皇后娘娘坐坐竟忘了。那便今日吧,带上修儿和思思一道。”
“也好,那夫人便只带修儿和思思吗?”魏文琰说时十分期待的模样,却又指望她能看出他心中的希冀。
“对,还有千雪。”
魏文琰停顿了半刻点头重重地应了声:“好。”
如今在府里魏文琰总是寸步不离地守着她,独孤慕语已听出他话里之意,只是女人间的体己话他在旁多有不便。为免他伤心她便说道:“我与皇后娘娘坐坐便回府,就有劳王爷备好美酒佳肴在此等候了。”
“嗯,只管去就是了。”魏文琰朗声答道,转身便坐到修儿身旁打量着他布下的棋局赞赏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本王的儿子果然不差。慕语梳妆还要一会儿,不若你我下一局?”
魏宴修闷声应着便拣好了棋盘上的棋子,旋即将白子推到他的面前。
独孤慕语梳妆妥当从内室走出便看到了这样的一幕,一大一小皆一手撑肘,眉头紧蹙着,日光将稚嫩和冷峻的轮廓雕刻出温情的模样。思思却趴在魏文琰的脚边睡着,恬静的模样像极了慵懒的猫。
千雪轻手轻脚地上前,她才伸出手要抱走思思魏文琰却拦住了她,只做出噤声的手势。独孤慕语会意便招呼了修儿过来,他恋恋不舍地看了几眼棋盘这才起身走来。
“这样恋恋不舍的,可是将要赢了?”独孤慕语抚平他微皱的衣摆,又正了正他的发冠,只是这样他浑然天成的俊俏容貌便足够惹人侧目。
修儿苦恼地摇摇头道:“并非,儿子正居下风,与父王博弈略微吃力。”
“你年岁尚小,尚有大把光景,你父王总是要输的。”她轻轻的一声便使得钻研棋局的魏文琰回过神来,深邃的眸正似笑非笑地看着她,直叫人毛骨悚然。
独孤慕语自知不妥,未免他反悔她急忙拉着修儿逃了出去,修儿就好似一个木偶娃娃一样任她随意拉扯摆弄。上了轿后她才又嘱咐了几句,无非是谨言慎行诸如此类的。
“母亲不必担心,儿子见过太子,我与他甚是投机。”
“修儿,不论你二人再怎么投机,你都要时刻谨记君臣有别。太子是储君,你是穆亲王之子,很快你便会承了穆亲王的爵位,那时你更要一心辅佐太子。”
修儿连连摇头道:“可是儿子不想做王爷,儿子只想跟着母亲平淡度日。”
独孤慕语没有回答他,因为他的苦恼似乎是自己和魏文琰加诸的,是他二人自私地要逃离这些纷争,只好将幼子推上前。
看着她苦恼,年幼的人瞬间做了决定:“母亲不必忧心,儿子会尽好本分的,只要是母亲想要的,儿子都会做。”
他愈发地体贴懂事,她的愧疚就更多一分,同是不善言语的母子二人,她能做的只有紧紧地牵着他。
落了轿后又是一道道漫长的壶道,她牵着修儿走在里侧,深秋的风穿过寂寥的宫墙,更添凄凉。修儿紧着脚步跟着她,忽然停住了脚,“他真可怜。”
萧瑟的风刮着,她听不大清楚,便问了句,“修儿,怎么了?”
他只摇摇头便拽着她示意她继续走着,才到凤鸣宫外便遇上了前来的龙撵,她急忙拉着修儿跪下行礼。这时龙撵上的人缓缓走来,一双龙纹皂靴在她眼前站定。
“起来吧。”低沉的声音自头上传来,她小心翼翼地拉着修儿起身,头由始至终都未抬起过。
“抬起头来!”他又往前走了一步,浓烈的麝香扑鼻而来,低沉的声音染上了不可抗拒的威严。
“陛下龙颜臣妇不敢窥探。”独孤慕语依旧抵着头,攥着修儿的手微微沁出了冷汗,不得不承认,帝王者确有逼人心神的魄力。
只见他连连笑道:“哈哈哈,语儿啊语儿,即便经年累月,你便是你,从未变过。”
他如此亲昵的唤着她的闺名,魏文琰都不曾这样唤过她,他怎么能!即便他是皇上,她毕竟是穆亲王妃,是他的弟妻。独孤慕语惊愕之余更觉羞愤,再看眼前的明黄衣摆只觉得格外刺眼。
“你果然是什么都不记得了,这样的你如同白纸一张,一如当初。”他似乎在自言自语,声音却足够她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