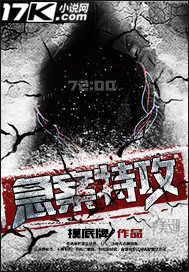“你……你这么快回国了……怎么进来也不说声?”
“还住着十年前的老房子啊,看来你穷得没小偷上门撬锁了,钥匙十年没换哪,我也留着一把呢。”印鹃言辞还是那么尖酸刻薄,她像主人那样招呼说,“请坐。”
“我们单位就快要分新房了,你的钥匙很快就没用了。”沈沧蓝定下心来,决定婉转地撵走她,“印鹃,你还回来干什么呢?当初你选择了你的新生活,我也没拦你,或者干脆说,拦也拦不住。现在呢,我也快要有自己的幸福了,你偏拣这个时候回来,你这不是成心给我添乱吗?咱俩虽然已经分手,可还是要互相尊重隐私的呀,你上次怎么能这么说人家……”
“怎么样,”印鹃就好像没听到他的话,自顾自地说,“你回来之前我把家里打扫了一遍,你呀,你知道我为什么忍受不了你,首先一条就是你邋遢……”
沈沧蓝这才发现家里确实是被布置一新了,他随即想到那死尸身上的黑色方盒仍在家里!如果是别人不一定能找到,但印鹃对这个家的结构和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要找到它绝对不是件难事!
沈沧蓝慌乱无助地四下翻箱倒柜,印鹃跟屁虫似的在后面絮絮叨叨地追问:“干嘛呢?你有什么东西藏着掖着不敢让我知道是吧?怕我收拾家的时候扔了?是你和小狐狸的情书?还是……”
“别吵!”沈沧蓝一反过去的低声下气,他与眼前的女人没有了利害关系,也不怕得罪她,但印鹃突然伸出手,映入沈沧蓝眼帘的竟然是那个黑色的盒子!它打开了,里面空空如也。
“你是在找这个吗?”
沈沧蓝见印鹃突然变得严肃,不由怔了怔,结结巴巴地说:“没……没呢……”
“这里面的东西呢?”
“你……你怎么知道这里面有东西?”沈沧蓝在动用所有的脑细胞疯狂地回忆,里面的东西呢?
印鹃的眼中闪过一丝窘迫:“我的意思是问,这里面应该有什么东西吧?我以前没见过这个盒子,是咱俩分手以后买的吧?里面装着你和小狐狸的定情信物?”
沈沧蓝为了转移她的视线,故作义愤填膺状:“请你别再用侮辱性的词汇称呼她!分手?咱俩那是分手吗?那是你抛弃了我们父子俩!”
印鹃毫无愧疚地笑:“我看你不是过得挺好的吗?”
沈沧蓝刚要反唇相讥,电话在这个时候响了。他见这个号码是霍紫悠的,心里一阵狂喜,又不像当着印鹃的面打电话,以免她嘴又不干净。他跑出卧室,接通后刚要解释,霍紫悠却急切地抢先一步说:“沧蓝,我今天上午去开会,回来听代课老师说心焰在上课的时候突然烧得厉害,浑身燥热,已经送到新平安医院了,我正赶过去呢,你也快来好吗?”
猛然听到儿子出了事,沈沧蓝登时明白了:原来那盒子里的东西被心焰拿去了!自己真是糊涂!真不该当着他的面藏那东西,孩子毕竟好奇心重啊!他曾经偷偷打开过那盒子,里面是一块透明的冰块,迎面散发出迫人的奇寒,就像一下子到了南极,如果把手伸进去触摸,必然会瞬间被冻僵。可奇怪的是那冰块中隐隐闪耀着一丝朦胧的火红色,从外观上看就像一段腊红肠,或者一条红色蜈蚣,尽管色彩淡然得难以觉察,可却有一股太阳般炽热的神秘热流从寒冰的缝隙中微微溢出,这种冰火交融的神奇感觉无可名状,让本来就想像力丰富的他猜到这冰不是普通的冰块,而里面包裹着的更不知是什么可怕的东西,而这两者截然相反的气质又恰巧使得它们的温度达到了动态的平衡。
他当时就感到这东西大有来头,不是古董就是什么高科技产品,由此推断,那个因为行动鬼祟而被他撞死的物品持有者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人,心焰只处于好奇心拿走了这未知是福是祸的东西,肯定是要出大事的。
想到这里,沈沧蓝抄起车钥匙就匆匆冲出门。印鹃以极快的速度揪住了他的手,不依不饶地追问道:“那东西在儿子手里吗?”
沈沧蓝发怒了:“你到底是关心儿子还是那东西?那东西关你什么事?”
印鹃毫无表情,一字不变地重复道:“那东西在儿子手里吗?”
沈沧蓝这才觉察出不对劲,印鹃的面孔似乎因过于激动的情绪而变得格外扭曲,看上去就像是一团橡皮泥外面裹着塑料袋一样。他蓦然感到极大的惊惧,想要挣脱开来,却觉得胳膊疼得厉害,步子难以移动分毫。他猛然意识到,眼前的这个人很可能并不是印鹃……
千钧一发之际,一辆熟悉的长丰猎豹伴着刺耳的警笛声疾速驶到眼前,还是那一老一少两名警官。姓王的老警察一下车就说:“沈先生,纪春南先生被人谋杀了,他的尸体在黄羊渠那个地点被发现。死亡时间是在我们刚刚离开不到半小时,死状很惨烈,就像被什么动物撕扯了一样……”
沈沧蓝忙不迭地打断:“王警官,李警官!救救我,这个女人她疯了!”
两名刑警这才发现正死死抓住沈沧蓝不放的印鹃,年轻的警察小李厉声喝止:“你是什么人?快放手!”说罢就快步走上来劝阻,由于印鹃打扮得很普通,小李并不认为她会做出什么暴力的举动。
但就在那一霎那,印鹃痉挛到极限的脸猛地像花瓣一样轻盈地绽放开来,小李吓得一声惊叫,旋即居然把枪口对准自己,好在他手上一抖,砰地一声打穿了肩膀。沈沧蓝看得瞠目结舌,只觉得喉咙像被无形的手扼住,吓得动弹不得。
被风一吹,小李肩头裸露出的骨头就像被利刃刮过,疼得撕心裂肺,几近晕厥。但他仍然很专业地趁自己神志尚未模糊闪电般再次抬起手枪,一面瞄准一面用癫狂的嚎叫来发泄痛苦。但扳机还没有来得及碰,印鹃左手扬起,小李再度神色模糊,又举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这一枪打得脑浆四溅,枪落在地上,染得腥红可怖。
沈沧蓝已经知道那不仅不是自己的前妻,而且还是一个能控制他人思想的巫婆,她要得到那个东西,肯定会去医院伤害儿子。脑海中心焰无助的样子令他瞬间产生了极大的勇气,双手接住落地的手枪,反手便对准印鹃扣动扳机。
印鹃本来只想打落手枪,绝没料到连老鼠也害怕的沈沧蓝敢于向自己开枪,一时没防备,子弹已经穿过了她的脸颊,把牙齿打落数个,口水混合着鲜血四下喷溅,人也倒在地上。
老王警官连忙示意沈沧蓝上车,同时要去拖拉小李的尸体,刚打开车门,两人的虎口便一阵剧痛,小李的躯体弹弓一样被猛地扯了回去,印鹃大概以为那是沈沧蓝,结果发现搞错了,便发出激烈的怒吼,并扯断小李的躯干。
老王临危不乱,沉着地发动车,沈沧蓝拱进去,全身发抖。车刚开动,后视镜中的印鹃便以人类难以企及的神速追了上来。
王警官冷笑一声,陡然间踩了急刹车,顿时惊天动地一声爆响,车的后窗溅满了厚厚一层正冒着气泡的恶心黄液。印鹃的身体腾空而起,远远地坠落到七八米之外,落地前又被一辆高速行驶的福田大货迎面接住,然后继续被三四辆车分别“踢球”,当即四分五裂,而货车也由此翻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