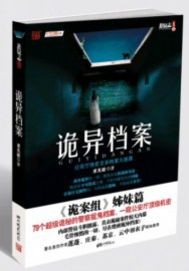武林军低下头,像是在向老师念检查的学生,一字一顿地说:“苗哥,事到如今我也不敢隐瞒了。我老家在西部,重工业城市普川。初中高中都在武校,不是吹牛,不止一个老师说我是练武的大好材料,单说动手,能打过我的同学没几个,只不过我的基础文化课太差,毕业后因为分数低,连三本也上不了,就出远门做点小买卖。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经商头脑,折腾了一年多才回家,也没挣什么钱。回家那天,我看到我妈妈脸上肿了一块,嘴巴也发紫了。我一看这不对头,就追问是怎么回事,我妈坚决不说,我爸也直叹气。他俩就是这样,一辈子说要做好人,他俩觉得只要自己老实厚道,别人就不会欺负。所以特别珍惜名誉,还自以为名声挺好,岂不知在邻居和其他外人眼里,他俩都是可怜可笑的懦夫、胆小鬼、窝囊废。我小时候听到人家对我们家里的评价后告诉父母,他俩不但掩耳盗铃不相信,还总打我。我的骨子里和他俩竟然都不同,从小到大,绝对不是逆来顺受的性格,我不甘心也成为这样一个为了名誉就放弃了做人尊严的所谓好人,也许做老好人会很安全,但活得太悲哀了。关键时刻我必须强硬,别让人小看,不然时间一长,别人就会认为欺负你是理所当然,你要是反抗就会被视为大逆不道。我毕竟是习武之人,要是任人宰割,我哪还有脸继续呼吸下一口气?
“于是我向邻居打听后才知道,原来附近一栋楼上一个年轻女人来收水电费,我妈就因为发现数目不对询问她,她就火了,要知道我妈妈对我很严厉,但对外一直笑脸,就算和人理论也是小心翼翼,不知道这样善良可怜的老人怎么会惹得那女人大怒,不但掴了我妈好几巴掌,打得她一脸乌青,还吐了她一口唾沫。我似乎觉得周围的邻居又在指指点点,暗地里嘲笑我爸妈是任人欺凌的可怜虫,还自以为自己得道多助,是人人敬仰的有德之士呢。我虽然性格沉默,但一点儿也不软弱,谁触犯了我的底线,我就让他终身难忘。于是我立马去找那个年轻女人。那女人名叫柳栖凤,怪不得她这么猖狂,原来这马蚤狐狸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傍上了一个有钱的公子哥,那公子哥有一大群流氓朋友天天在一起吃喝玩乐,我这一去,他们不但不悔过,气焰更是嚣张,这群野痞子就一拥而上打我。我哪受得了这个气,一拳一脚都用尽了全力跟他们死拼,本来打伤了他们其中两个,可他们有十多个,很快就把我送进医院了。我爸妈哭得死去活来,这让我更加不安、心痛。等我伤一好,就拿着双节棍去找那个公子哥,他也许经常欺负人,压根就没想到还会被报复,当时落了单,我当场就把他的鼻梁骨砸塌了。谁想到他老爹原来不是一般的有钱人,是普川数得上的大企业——卡*维实业的董事长,找了一大帮子人追我,我这一跑,连累了我爸妈,那帮人把家里砸了个稀巴烂,把保险柜存的那点可怜的积蓄都烧了。我妈哪受得了这个打击,精神开始不清醒了,我爸爸就像突然老了十几岁,很长时间不肯说话。
“我实在受不了了,想去告这帮王八蛋,可是他们竟然还和六扇门串通反咬我一口,把我抓进去毒打了一顿,并告我打伤了公子哥。这一下我不但被动地赔偿了八千块,还要蹲三年大号,我父母的生活更困顿了。卡维的老总还不算完,他买通不少号子里的差役和囚犯,故意刁难我,我知道要报仇必须忍耐,对于差役,我就忍气吞声,任凭他们侮辱也要笑脸相迎,而对于囚犯,我毫不客气地将他们打得奄奄一息,毕竟在号子里里没有枪没有刀,一切变得很平等,再会装逼也没用,靠拳头才能说话。很快,号子里和我接触过的狱友都比较忌惮我了,有些大哥级别的牢头狱霸还都争着拉拢我,说等出去后要聘请我当他们的打手。上头都觉得我有威信,反而提我当管理员。很快,由于我比较会处理关系,解决了不少纷争,立了功,不到两年就减刑出来了。我难咽这口气,出狱后就拿着刀子直接去卡*维实业。谁料到卡*维实业在我入狱期间出了什么经济上的大问题,破产了,不但老板落魄街头,柳栖凤也另攀高枝了。这个时候,我虽然觉得恶人终有恶报,却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下一步该找谁报复了。与此同时我也没承想自己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名气,虽然没人知道我的名字,可我被人起了个外号叫‘双节棍’,社会上都在盛传我是个心狠手辣的黑道老大,势力大得把卡*维实业都干倒了,不少慕名而来的流氓都尾随我,赶都赶不走。我去找了几次几次以前打过我的那个公子哥和他的流氓朋友,但他们都像怕瘟神一样躲着我,我这才知道他们虽然势力大,却怕我这个没本钱的疯子报复。我又重新树立了信心,打算横行街头一辈子。就这样过了五六年,我的锐气却随着年龄慢慢减弱了,而且在普川地面上呆久了,当差的也开始注意我,让我感到很不安全,毕竟我不是那种黑道上有实力有头脑的人,只有这一对拳头,凭拳头吃饭太惹眼了。我也怕当地六扇门担心我说出他们和卡*维勾结陷害我的事情而对付我,就选择离开普川,从小混混开始做起,所以几经周折落脚烟州,就认识苗哥了……”
“我真服了,你上辈子是不是个说评书的?”苗放听得很出神,吞了口唾沫,不禁追问:“那……那你说了这么多,这跟刚才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
“你还记得去年八月份那个任务吗?咱们因为这件事分开到外地躲了半年。所以你们对我现在怕高的行为很惊讶,其实当年在外地我已经这样了,只不过你们都躲到农村去了,所以不知道上楼会有什么危险。我过去并不怕高,两三米的高度我根本不当个事儿,或者干脆说,我怕的并不是高度,而是……”
苗放回忆起去年八月份,白金东从南方的大亨手里拿了一部分数量惊人的黑*钱到烟州,以借高利贷和投资房地产、娱乐行业的行为清洗,从中获取提成。当时有个市委路秘书长的儿子路新豪准备自己做买卖,从银行贷了一笔款子,结果越做越赔,银行追着要,迫不得已,路新豪瞒着父亲向白金东借了一千万高利贷。白金东从八十年代末解散团伙并以一人蹲大狱顶罪后南下南方,直到三年前才卷土重来,总共也没有多少钱,这一千万基本上就是他大部分家底。完全看在路秘书长的面子上,相信其父铁定不会坐视儿子不理,关键时刻一定会拉儿子一把。谁也猜不到路新豪骗了两头,加上路秘书长那些破事进行交易东窗事发,一下子判了个十五年,路新豪从公子哥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白金东气急败坏地去找他,他却躲了出去。苗放和刘玉河打探到路秘书长在烟州市一处尚未被发现没收的秘密房产,里面包养了一个年轻女人,而路新豪竟然也经常来,原来那个女人瞒着路秘书长,做了他父子二人共同享受。这女人长的很漂亮,路新豪无处可走只能来这里,他们就打算守株待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