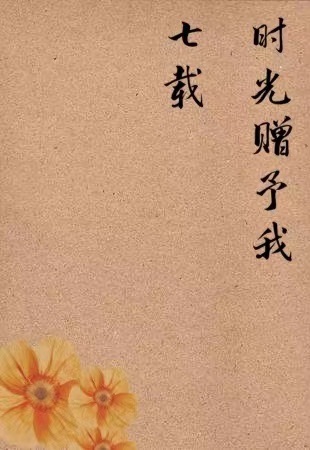阿海悄无声息的端着一盘吃食从正房经过。
盘子里是一盅荷花什锦炖并一份南瓜松仁拉糕,这些都是少爷平时爱吃的,老爷曾经在家的时候也很喜欢,因此家里面常备着材料,本来是要放到今晚家宴上做主菜的,可是这个元旦注定没办法和和美美的过。
老爷和少爷虽然长相不像,少爷更像太太些,但父子俩的脾气如出一辙,都是三角石头,倔,脾气硬,不大晓得变通。
这脾气若是当个普普通通的大宅少爷也就罢了,可是少爷要去做魔术师,进彩门,那就是个大缺点。
太太不让少爷从事家传本事,里面绝没有强横掌控之意,只有一片慈母之心。
可俩人这脾气,太太想让少爷回心转意,除了关住他,其实也没什么法子。
明明已经气的脸色雪白,但是太太依旧记得吩咐他给少爷送最好的吃食。
阿海悄悄往正房里探了一眼,太太正坐在椅子上怔怔出神,不知道是不是又在想老爷,再次叹了口气,阿海脸上的褶皱都堆在了一起。
阿海回来的时候,杜和已经将书信写好了,封在了信封里,端端正正的拿着一本闲书再看,一副打发时间的样子。
阿海敲了敲门,得到许可后,伴随着一阵冷风进到了小厅里。
杜家就杜和一根独苗,因此原本的三间东厢房就打通两间,给杜和做了小厅和一个小书房。阿海的盘子一放,杜和的鼻子就抽了一下,登时坐了起来,惊讶的看着阿海:“海叔,这是?”
阿海慈祥的笑了笑,将盖子揭开,把热水盅里温着的炖盅拿了出来,顿时,一阵沁人的鲜香就溢满了房间。
杜和轻呼一声,大马金刀的坐在了桌前,满是惊喜的拾筷挟了一筷子花胶,囫囵着吞进口中,烫的直吸气,还招呼着说:“海叔一起吃,花胶炖的怪好的,这几年还蛮想这口的。”
杜和一激动,乡音都蹦出来了。
阿海笑呵呵的陪坐着,看着杜和一通迅速的进食,有些疼惜。
他在杜家二十五年,先跟着老爷,后来又跟着太太,打理家门上下,是看着少爷长大的,老爷常年在外,少爷对他的感情其实也有些长辈的意思,他虽然不说,可是又哪能真个把少爷就当个少爷看了?
少爷不到十七岁就远离家门了,那个时候还有些娇惯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虽然不到,但是也是从来没吃过苦的。
异国他乡四年,居然连口热饭都吃的这么开心……
阿海心下感慨,看杜和吃得开心,一时就忍住了劝杜和遵从母亲的想法,转而轻飘飘的说了句:“少爷,这什锦炖还是太太亲自做的咯,说是你回来一定喜欢呐。”
虽然嘴上不让儿子回来,但是哪个当姆妈的不想孩子,太太心里头也是盼望少爷回来的。
杜和动作顿了顿,将脸埋在碗里,吃的稀里哗啦,最后居然硬生生将两碗吃食都填进肚中,还打了个饱嗝。
阿海哈哈大笑,赞道:“少爷可不是小鬼头了,是个有肚量的奶油小生了!”
老苏州现在夸男人就爱夸奶油小生,这是新兴的词儿,专说男人长得俊的。
杜和有些脸红,总感觉奶油小生有些脂粉气,憋着脸硬邦邦的说:“海叔,我可不是小生,国外的那些淑女们都叫我绅士咧。”
“好好好,少爷就是个绅士,以后还是先生,娶了婆姨以后,还要当阿爹呐!”阿海说的满面红光,似乎都看到了少爷成家立业的景象。
自古青年最怕的就是这遭,杜和有些腼腆,还带着点恼怒,最后吭哧吭哧的,还是“嗯”了一声。
阿海心满意足的端着盘子走了,给杜父写的信也被阿海妥帖的放到了怀里,传去南洋。
杜和相信父亲听了自己的解释会支持自己,心里头略微宽松些,坐在温暖的床上看了会儿月亮,就安心的睡下了。
杜和不知道的是,自己的书信很快就放到了母亲的面前,杜母看着信封,连想都不用想里面写的是什么。
将那封信放到了香炉里,很快,一股火苗冒出,变成一缕青烟。
阿海在门外候着,只听到杜母有些沙哑的声音传来:“明日起将家里的医书都送到阿和房里,不够就出去托人购买,开春的时候,就送他去博习医院。”
阿海应了一声,悄然退下。
杜母的屋子里电灯很快就熄灭,一盏油灯却随之点燃,亮到了天明。
第二日开始,杜和就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杜母未曾露面,但阿海却跟在了他的左右,寸步不离,就看着杜和研习医书。
如此几日后,阿海态度依旧,杜和倒是不答应了。
“海叔,您没有事做么?”
杜和扶了扶自己的脑袋,再一次问阿海。
阿海站在杜和右侧,闻言立刻就答:“太太吩咐我协助少爷苦读,别的差使就延后掉,少爷要是心疼我,就快快学成,进入博习医院罢。”
类似的问题杜和不知道问了几十个,阿海都是拿这句话来回应,别说阿海自己腻味,杜和已经快被折磨疯了。
那些医书他不是看不懂,但是他更想看的是家里面藏的《西洋魔术考》和《彩门九法详解》这类魔术研究类的书,而不是冷冰冰的解剖图和一堆一堆的药理公式。
有些人天生会唱歌,有些人脑子灵敏擅长算学,他就天生就喜欢魔术,这都是明摆着的道理,却不知为什么人人都想强迫他人做不喜欢的事,非要让他学个医术。
杜和叹了口气,放下书说:“我要去见姆妈。”
阿海这回不立时回答了,想了想才出门,还吩咐了两个小仆人来看着门。
杜和算了算,那封信去了南洋,此时应该会有回信了,不过姆妈肯定不会让他看,此时他就是打算自己去看看父亲的回音。
他相信,他那么充满诚意的跟父亲坦诚心事,父亲一定会同意他的。
毕竟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是乐意杜和学习魔术的。
杜和头没动,手上一面小镜子一晃,就看到那俩小仆人正在门外站着,他缓缓地起身,踱步到了书房边上。
警惕的小毛头顿时就看向他。
杜和拿了个黑胶唱片,晃了晃,就又回了书房,还砰的一下关上了书房的门。
两个小毛头正急,很快,书房里面就传来一阵音乐声,还夹杂着少爷朗读的声音。
俩人对视一眼,都松了口气。
少爷会魔术,云里来雾里去的,大家都怕少爷弄个什么法术,就把自己给变没了。
人还在就好。
此时的书房里,早就空空荡荡,杜和以一枚发针穿过窗棂,悄悄的翻了出去,又小心的将窗户关好,一路上绕着房屋,从廊道边缘,钻进了姆妈的正屋里。
一路上虽然有人经过,杜和都险之又险的避过了。
这几年他魔术虽然没有名师带,但杜和为了锻炼体能,一直修习西方锻体术,还把家族里面的锻炼方法回忆了一个七七八八,没想到是在自家派上了用场。
杜和心里苦笑,母亲平时这时候应该在外院处理杂事,整好他知道母亲会把父亲来信放在主卧里,所以一打量,就熟门熟路的摸去了卧室。
杜和也是第一回做梁上君子的小人行径,有些紧张是免不了的,进了里屋心里一松,就靠在了姆妈的小佛龛旁边。
他是个半洋半中教育出来的,对头顶三尺敬意不深,此时体力消耗一大,更是不注意,也没什么形象的拿胳膊一撑,靠的结结实实。
刚一靠过去杜和就觉得不好,果然,这一回头,动作一大,龛上的青铜香炉晃了晃,一头就栽了下去,“咣当”一声,里面的香灰撒了一地。
杜和先是惊慌,接着余光划过,瞬间呼吸一紧,在香灰里拨了拨,拿出来一小片纸屑来。
杜和不知道的是,自己的书信很快就放到了母亲的面前,杜母看着信封,连想都不用想里面写的是什么。
将那封信放到了香炉里,很快,一股火苗冒出,变成一缕青烟。
阿海在门外候着,只听到杜母有些沙哑的声音传来:“明日起将家里的医书都送到阿和房里,不够就出去托人购买,开春的时候,就送他去博习医院。”
阿海应了一声,悄然退下。
杜母的屋子里电灯很快就熄灭,一盏油灯却随之点燃,亮到了天明。
第二日开始,杜和就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杜母未曾露面,但阿海却跟在了他的左右,寸步不离,就看着杜和研习医书。
如此几日后,阿海态度依旧,杜和倒是不答应了。
“海叔,您没有事做么?”
杜和扶了扶自己的脑袋,再一次问阿海。
阿海站在杜和右侧,闻言立刻就答:“太太吩咐我协助少爷苦读,别的差使就延后掉,少爷要是心疼我,就快快学成,进入博习医院罢。”
类似的问题杜和不知道问了几十个,阿海都是拿这句话来回应,别说阿海自己腻味,杜和已经快被折磨疯了。
那些医书他不是看不懂,但是他更想看的是家里面藏的《西洋魔术考》和《彩门九法详解》这类魔术研究类的书,而不是冷冰冰的解剖图和一堆一堆的药理公式。
有些人天生会唱歌,有些人脑子灵敏擅长算学,他就天生就喜欢魔术,这都是明摆着的道理,却不知为什么人人都想强迫他人做不喜欢的事,非要让他学个医术。
杜和叹了口气,放下书说:“我要去见姆妈。”
阿海这回不立时回答了,想了想才出门,还吩咐了两个小仆人来看着门。
杜和算了算,那封信去了南洋,此时应该会有回信了,不过姆妈肯定不会让他看,此时他就是打算自己去看看父亲的回音。
他相信,他那么充满诚意的跟父亲坦诚心事,父亲一定会同意他的。
毕竟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是乐意杜和学习魔术的。
杜和头没动,手上一面小镜子一晃,就看到那俩小仆人正在门外站着,他缓缓地起身,踱步到了书房边上。
警惕的小毛头顿时就看向他。
杜和拿了个黑胶唱片,晃了晃,就又回了书房,还砰的一下关上了书房的门。
两个小毛头正急,很快,书房里面就传来一阵音乐声,还夹杂着少爷朗读的声音。
俩人对视一眼,都松了口气。
少爷会魔术,云里来雾里去的,大家都怕少爷弄个什么法术,就把自己给变没了。
人还在就好。
此时的书房里,早就空空荡荡,杜和以一枚发针穿过窗棂,悄悄的翻了出去,又小心的将窗户关好,一路上绕着房屋,从廊道边缘,钻进了姆妈的正屋里。
一路上虽然有人经过,杜和都险之又险的避过了。
这几年他魔术虽然没有名师带,但杜和为了锻炼体能,一直修习西方锻体术,还把家族里面的锻炼方法回忆了一个七七八八,没想到是在自家派上了用场。
杜和心里苦笑,母亲平时这时候应该在外院处理杂事,整好他知道母亲会把父亲来信放在主卧里,所以一打量,就熟门熟路的摸去了卧室。
杜和也是第一回做梁上君子的小人行径,有些紧张是免不了的,进了里屋心里一松,就靠在了姆妈的小佛龛旁边。
他是个半洋半中教育出来的,对头顶三尺敬意不深,此时体力消耗一大,更是不注意,也没什么形象的拿胳膊一撑,靠的结结实实。
刚一靠过去杜和就觉得不好,果然,这一回头,动作一大,龛上的青铜香炉晃了晃,一头就栽了下去,“咣当”一声,里面的香灰撒了一地。
杜和先是惊慌,接着余光划过,瞬间呼吸一紧,在香灰里拨了拨,拿出来一小片纸屑来。
杜和不见了。
阿海通知了太太之后,俩人到了杜和的东厢一看,早就人去楼空,留声机里依旧播放着杜和读书的声音,但是案子上的书已经被随意的扯了两页,做了个小机关,让留声机不停运转。
杜母简直怒不可遏,以为杜和是溜出去看街上柳门的戏班表演。
最近几天元旦日,苏州大小戏班都出动了,甚至平时让人看不上的团春的也出来说点段子,混几个银元留着过年,按照杜和的性子,一定坐不住的。
杜母很快镇定下来,吩咐几个家、仆人上街寻找,务必将少爷妥帖带回来。
阿海领命带人去了,杜母捂着心口,压抑着自己心里不好的想法,缓缓踱回主屋,本来想床上歪一会儿缓缓神,却刚一进屋,就闻到了一股子香味儿。
杜母虽然供奉佛龛,却也只是早晚一炷香,平时不会多动,这股子香味儿开始还让她有些疑惑,很快,她就看到了佛龛上还没擦干净的灰痕。
杜母猛然瞪大了眼睛,嘴巴张大,难以置信的打开了香炉。
几个呼吸后,所有的仆人都听到了主屋里速来平稳庄重的太太在几乎尖叫的喊人:“来人!”
杜和果然没在街上,所有做花活儿的地方都找遍了,也顾不得颜面的问了街坊,没有人注意到杜和,杜母的想法在晚上变成了现实,杜和走了。
杜和身无长物,出来的时候他只来得及换了身衣裳,此时正抱着膀子缩在一处冷冷清清的船坞里头,等着船家开船。
行李都在耳房里,也没人敢给他,他怀着一肚子的委屈和不甘,就那么光着两手从家里面跑了出来。
二十一岁离家出走,杜和此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今天。
他一向是父母眼中的好孩子,听话懂事孝顺是街坊们对杜和的一致看法,可以说除了性格有些执拗,杜和其实是很多个姨母们的理想女婿。
然而杜和今天就大胆了一次,就这一次,直接就捅破了天,把祸事一下就闯了个底掉。
在典当行当了自己的手表,换了两个小头银元,杜和明知道是亏了,可也只能忍着。
典当行的人惯会看人情,急着出手的价格能有原来三成就顶天了。
虽然两个小头银元也足够一个单身汉活过一个月,可是下一个月,杜和如果没有找到转机,就会面临着可怕的后果。
船费不贵,才一角钱,合着不到三十个铜元,还不够杜和一盘糕的价钱。
可是当船家给他找钱的时候,他才真正有些紧张了,为了船家毫不掩饰艳羡的眼神,也为了自己的前途。
那一袋子细碎铜元,就是他以后所能依仗的所有,如果连这些都没了,杜和可能会在这个冬天里无声无息的消失在一条没结冰的河里。
很快,一声号子,船家撑槁一动,小船就窜出去十几米远。
“小少爷这是去哪儿?”船家声音颇为多言的问了一句。
“投亲。”杜和掂量着船家的眼神,谨慎的说。
“哦,”船家撑了一下槁,“不知道去投谁?小的虽然不是个东西,但是犬子也是跟着黄先生做事的,就是锦镛先生,兴许能认识?”